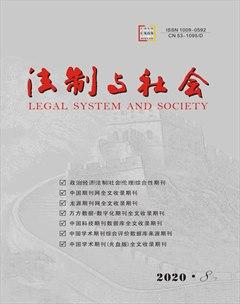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关键词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国际海底 全人类利益 共享
作者简介:金泽兴,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8.265
一、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的由来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与海床洋底、外层空间与南极地区密切相关的。三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在现有的技术手段基础之上人类活动所能到达的最后领域。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最初作为一种理念,出现在1963年第十八届联大决议中即:《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空工作之法律原则宣言》。该宣言提出了9项原则,包括外空的探测和使用应为全人类谋福祉和利益;禁止国家将其据为己有等。随后,在1967年签署的《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即《外空条约》中,上述原则得到了确认,然而,“在法律制度上,外空条约没有提出特别的方式,只是强调活动的目的应为所有国家谋福利,其核心是强调所有国家应当在平等、不受任何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1]它只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的不完善的雏形。1979年通过的《月球协定》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从海洋法中引入,正式确立了月球及其资源为全体人类的共同财产。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在一个有168个缔约国的公约即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确定下来,是有重大意义的。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出现在海洋法中,与国际海底区域的丰富资源分不开的。在深海底部蕴含着丰富的锰结核,它包括猛、铜、钴、镍等金属。据统计,仅在太平洋的洋底就有大约5000亿到10000亿吨左右的锰结核资源。由于储量巨大、价格低廉,加之在上世纪50年代,在海底采矿的技术得到验证。从60年代起,许多国家纷纷注意到海底资源所蕴含的巨大利益,提出了将国际海底国际化的建议。1956年,美国政府在海洋研究和技术上的支出约为2500万美元。到了1968年,尽管越南战争造成了美国的财政紧缩,但在海洋研究和技术上的投入仍超过了4.48亿美元[2]。在这一时期,军事技术特别是潜艇以及潛艇的导弹技术的发展也引起了许多国家注意。为了避免海底再度成为战场,也为了防止拥有海底采矿技术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对海底资源的霸占,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要对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洋底的资源进行管制,使之服务于全人类的利益。1967年8月,马耳他驻联合国代表帕多(Avid Pardo)在22届联大议程中提出:建议将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床、洋底及其资源视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同时他提议起草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包括如下4项原则:(1)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床及洋底不得被任何国家据为己有;(2)对上述区域的开发应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一致;(3)对上述区域的经济开发和利用应以保证人类利益为目标,产生的经济利益应主要用于促进贫穷国家的发展;(4)上述区域应被永久的专为和平目的而保留。1970年12月17日,联大二十五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底床与下层土壤之原则宣言》,对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海床、洋底及资源进行了确认,确认其为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1982年,海床洋底资源的法律地位第一次以公约的形式得到确认。
这一原则的确立毋庸置疑的受到了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政治利益的影响,妥协的后果使得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适用范围变小,但它正式确立了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洋底和底土的法律地位,也得到了联大及其他机构的重申、确认,它仍然是国际法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在外空法中,也免不了因利益妥协而造成的方案折衷,它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二、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与内涵
(一)关于“人类”这一概念的指涉
第一,“人类(mankind)”与“人(man)”是不同的。“人类”是一个集体概念,而“人”则指的是个人、个体。个人的权利是指个人因其成员身份即作为人类的一部分而有权享有的权利,人类的权利则与一个集合实体有关。因此应当将人类作为一个集合即单一主体,人类共同继承是人类作为一个单一主体继承的,而非个人或者是代表个人集合的国家继承的。
第二,正如上文所述,不论是9项原则,还是帕多在二十二届联大中的提案那样,这一财产应当是全人类共同所有,并不能据为己有。任何国家、国际组织或个人等国际法主体对这一财产的任何违反国际法原则和规定、违背服务于全体人类利益和用于和平目的的行为都事实上被视为对这一共同财产的侵犯。
第三,“人类”这一概念并不止局限于当代,而应当是当下及以后的所有人类。因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其宗旨是服务于全人类的利益,并不只是服务当代人类,而应当是世代传承,是一个有着可持续性的概念。
(二)关于“继承财产”指的是占有权、使用权还是所有权的问题
有的学者将海洋中的“财产”视为国际公共财产,这意味着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看作是国际社会中的成员国及其居民对财产的共同所有权;有的学者则认为“遗产”有两层含义:可继承的实际占有物与类似“宪政自由遗产”所包含的抽象原则,这实际上是把“继承财产”看作是一种占有权。笔者认为,就拿“区域”来说,全体人类对我们继承的这一财产仅仅只有使用权。尽管国际海底区域的金属矿物储量丰富,但它始终有用尽的那一天。为保证当代以及我们的后代都能享受地球的这一资源为人类带来的巨大利益,就不能让这一“继承财产”被国家据为己有,因为将其定性为“占有”或者“所有”就势必会导致“滥用”以及大国之间为国际海底资源而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夺,这违背了帕多在提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理念——那就是服务于全人类和用于和平目的。帕多在提出这一构想时并没有主张其所有权,他只是摒弃了旧有的公海理论,提出了新的关于国际海底的国际法原则。
(三)关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与无主物、共有物以及公有物的区别
第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同于“无主物(res nullius)”,早期的一些国际法学者将海底视作无主物,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先占而取得。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主要是由于对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绵和珊瑚的海床在较早时候提出的排他性主张,以及在海底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释义,“无主物”指的是:“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的事务或一种不属于任何人的动产。”[3]早期国际法学者的排他性主张指的是邻近国家海岸的地区,并不是指深海底部,这些地区早已被大陆架制度所确立。再者,海底铺设电缆和管道只能说明是对公海海底的利用或使用,或者说是对“公海自由原则”的利用,铺设电缆和管道并不能构成对海底排他性主张的理由。实际上,关于海底是“无主地”的说法现在已经被抛弃。
第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与共有物不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制、法制史中对“共有”这一概念的解释和理解有所不同,以我国的民法制度为例,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与“共有物”的区别主要有二:其一,前者的主体是单一主体即全体人类,将其视为一个集合概念;而后者是多主体的;其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是无法被处分或分割的,这不符合现实。笔者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超越了国际社会是由传统主权国家构成的观念。
第三,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同于“公有物(res communes)”。“公有物”指的是:“所有人共有的事物;任何人不能拥有或占有的东西,例如光、空气和海洋。”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与公有物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它们都排除了任何个人对它们的占有和主张排他性的主权,任何人有的只是对公有物的使用权。同时,二者也有一定的区别,公有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难以用任何计量单位来衡量公有物的数量。海底的自然资源尽管储量巨大,但它仍然是可以衡量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据估计一立方英里的海水中含有大约1.25亿吨氯化钠、650万吨镁、3.8万吨锶、280吨碘、14吨砷、1吨银、0.02吨黄金和14吨铀。更重要的是,海底的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综上,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主张占有、分割的国际法学者都是从主权国家出发的。事实上,主权国家这一概念是抽象的,它将全体人类划分为有着不同归属的人的集合。在涉及关乎全体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平目标以及将这种利益和和平永久传承下去时,主权国家观念需要让位于全体人类這一概念。毕竟先有人类,而后才有主权国家。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是应服务于全体人类利益的。海底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金实力和高尖端的开采技术,这就使得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对海底资源的开采和使用上处于优势地位。国际海底管理制度的确立就是要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核心目标清晰化,那就是不仅要求全体人类的共有,而且要成为事实上的共享。
三、 结论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同于“无主物”和“共有物”,与“公有物”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尽相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应首先服务于世世代代的全人类的利益且专用于和平目的;其次,任何国家或个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其据为己有;最后,要真正实现事实上的公平与共享。对国际海底而言,尽管国际海底管理制度面临着较多困难,但统一管理排除了机构之外的单独开发,防止拥有先进技术手段和资金雄厚的海洋大国对海底的霸占与瓜分。平行开发制度使得各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成为一种国际责任。更重要的是它保证了国际海底资源用于和平目的,避免海底成为军备禁赛的新场所。正如帕多在1968年美国国际法协会联席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国际海底管理制度对公平地维护和协调大国与小国之间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言,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这是避免在世界上所有的大洋底部进行军备竞赛的唯一方法。”[4]庆幸的是,如今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主持以及各国的共同积极参与之下,国际海底区域开发规章草案正在制定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特别是2016年以来,开发规章草案更加强调和细化关于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人类共同继承原则促进了海洋环境的保护。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魏伊丝所说的那样,“比起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而言,在更长期的时间关联和更广大的地理范围上,应当将焦点放在保护我们的自然、文化环境的地球质量之上。”[5]
参考文献:
[1]薛捍琴.共同资源的法律制度比较研究[J].中国国际法年刊,1986:139-158.
[2]Arvid Pardo, Who Will Control the Seabed? Foreign Affairs, Vol.47, No.1, 1968:129,153-158.
[3]Bryan A. Garner (editor in chief), 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Standard Edition), Toronto, Thomas West, 2004:4076,4089.
[4]Ambassador Arvid Pardo, Whose is the Bed of the Sea? Proceedings of the ASIL Annual Meeting, Vol.62, 1968:214-229.
[5][美]爱蒂丝·布朗·魏伊丝著.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M].汪劲,于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