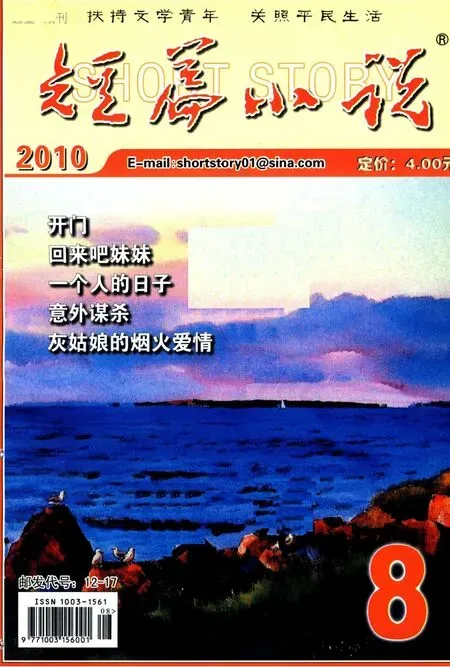1974年的猪
◎张淑清

我八岁那年,大连知青小郭被分配在我家住。生产队倒是有青年点,可已经叫前几批知青给住满了,生产队还得接出几间,房没盖好前,新来的就得住农户。队长马三是我爹的表哥,那天中午他手里捏着一根细篾,一边剔着黑黄牙齿上的菜叶子,一边往我家逛荡。身后跟着穿得很干净的小郭。马三一进门,就看到我娘弯着腰朝锅里搓饸饹馇子,黄澄澄的饸饹馇子,像屋檐下结的冰溜子,遇到暖日头挂不住,一嘟噜一嘟噜落进沸腾的汤锅里。馇子和酸菜浮着暗黄色的光泽,加上几只红辣椒,颜色鲜亮,香气扑鼻。马三不由咽了一下口水,旁边有些拘谨的小郭,也不约而同地咕嘟咕嘟吞了几口唾沫。
“就这家了,小郭。你安心住着,有事吱声。”马三队长说完,顺脚蹬掉了鞋盘腿坐到炕上,那样儿就像他是家里的主人。我娘扎撒着沾满面子的双手跟进屋,不明就里,问,“大哥,这是演的哪出戏?”
马三摆摆手,“你一个女人家家的,别管了,我跟明子都说妥了,小郭是新来的知青,眼下暂时没处落脚,反正你家西屋闲着也长草。到时候给你们记工分就是。”
明子是我爹的小名。那晌,我爹陪着马三和小郭,敞了怀,松了裤带,三个男人狠狠地造了几大海碗饸饹馇子。等他们吃完,我和娘只能喝些汤水混个半饱。饭后,爹就吩咐我,以后管小郭叫郭叔。
郭叔住进我家,我是欢喜的,来人都是客,何况是个说着好听口音的城里小伙。日子照旧穷得生疼,娘还是尽力往咸菜里多放几滴油,把苞米粥馇得更浓稠些。小郭叔倒不挑食,跟我们一样把苞米粥喝得山响,还常夸我娘馇的粥特香。
再穷,娘是要养一头猪的。娘说了,庄户人家,到了年底不杀一头年猪叫人笑话。饥荒年月,泔水都见不到几粒饭渣,干草粉碎的萆糊,是猪的主粮。那阵我读一年级了,放学后就去拔草喂猪,如果赶上连雨天,郭叔不上工,他也随我一起拔草。郭叔是城市长大的人,这使他对乡下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这会子,亲眼目睹一头猪的生长,简直是乐不可支。
我家的猪栏是石头砌的,结实牢固,郭叔来的时候,小黑猪已经三个月了,不爱吃食,一个劲地嚎。郭叔没事就进圈里,与黑猪磨磨唧唧说上一段话。乡下的日子枯燥得令人窒息,生产队劳动强度也大。郭叔是高中生,细皮嫩肉的,冷丁和土地打交道,被老日头暴晒,脸晒秃噜皮,手掌磨出一个又一个血泡。累得吃不下饭,爹关照过娘,好好弄两菜,别屈了城里来的郭子。
郭叔闲下来就愿呆在猪圈前,同黑猪说悄悄话。黑猪呢,似乎懂得他的心思,常常是静静地聆听,偶尔配合郭叔哼哼几下。黑猪不知怎么就病了,也查不出啥病,毛也不光滑,爹找队里的张兽医诊断过了,说有虫子,打打虫子就好了。买打虫药需要五角钱,爹一头虚汗,摸遍了所有中山装的兜,也没捯饬出一分钱。
郭叔递给张兽医一元钱,说,不用找了,你记着就行。
爹红着脸,搓着大巴掌,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郭叔伸手给小黑挠痒痒,笑吟吟地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小黑猪被挠得舒服了,伸直了腿儿咣叽一声倒下,还哼哼唧唧地表达着舒坦。日子长了,小黑猪对郭叔也亲热,只要他站在猪圈前,小黑猪听到他的脚步声,就蹭地爬起来,将前蹄子趴在矮墙上,啾啾啾地叫。郭叔抚弄着它的脊背,人和猪无声地交流着,郭叔的眼睛就红了。
郭叔是想家了,想家的郭叔,趁着有月亮的晚上,坐在猪圈前的一块青石板上,吹笛子。他有一只短笛,别在腰里,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休息时,一个人坐在僻静处悠悠地吹几曲。
我知道邻家二姐梅花喜欢郭叔,五月柳絮飘飞的季节,他们在一块插秧,下田总是并排走,羊肠子似的土路上,时常飘着两个人开心的笑声。
梅花的爹——我大伯却不让劲儿,他觉得郭叔是下乡知青,迟早是要返城的,梅花姐小学没读完,跟人差距太大,长得俊有什么用?人家回城能带上她么?我大伯横竖拦着梅花,不许她同郭叔走得太近。梅花不听,白天干活时,偷摸给郭叔一个约定,夜里就在我家门口猪圈前的梨树下见面。
我爹是明白人,对梅花和郭叔的事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季节,月亮特别圆,像一只大玉盘子,听着郭叔的笛音,悠扬婉转,倒真是叫人觉着美妙,又掺了些许的忧伤。爹在炕上,磕一下烟袋锅,火星儿飘散,爹嘿嘿笑了,娘手上的针线活儿突然加快了速度。
有时,郭叔和梅花约会还要带上我。梅花姐掏出一只麦芽糖,塞给我,去,帮姐盯着点儿,有人来,就喊我。
麦芽糖,甜丝丝的,我有点生气,郭叔又不是你的专利品,看在麦芽糖的份上,我没反抗。躲在距离他们不远的路口,用舌尖轻轻舔着麦芽糖,竖起耳朵听动静。
小黑猪也凑热闹,不住地挣命叫唤,在圈里转悠,不安省。这半大子正长身架,吃的又孬,半夜里也闹食。
小黑猪是公的,没劁,娘有她的打算。当初,从集上用独轮车拉回小黑猪时,娘的眼光就放出很远,她跟爹说,咱队里就张兽医养了只炮卵子,大伙用还需交钱,咱也养一头呗。爹说,养种猪得先过马三那关,不然,他给小鞋穿咋整?
娘捻了一下线陀,线陀受了惊吓,转得飞快。娘有她的主意,她见天瞅着家里大黄鸡的屁股,单独为大黄鸡开小灶,抓一把苞米粒喂它,或者是一捧谷子。这么着,大黄就像知道主人心思似的,日头刚露头,就钻进鸡窝生蛋。一个月后,娘傍黑挎着一只竹篮,篮子上遮着她平素扎的蓝色围巾,抄小路折进了马三家。
那晚回到家,娘脸上喜滋滋的,一篮子鸡蛋让小黑猪的身份得到了默许。
长到六七个月时,小黑猪虽瘦,但那股骚劲儿却是遮拦不住了,整日在圈里上蹿下跳,娘扒拉一下它的下身,脸热乎乎的,知道小公猪要媳妇了。它疯狂地朝娘,朝郭叔,朝每一个来圈前看它的人,发出呼唤,发出抗议。此时的小青年黑猪,毛色锃亮,在郭叔与我割来的各种野菜滋补下,它发育良好,肌肉发达,腰身健硕,一双眼睛充满了月亮般的光芒。
青年黑猪的反应,令娘措手不及,它反抗的方式是绝食,娘熬的苞米糊糊也引不起它的食欲,我和郭叔割的青草,它仅是闻了闻,摇摇脑壳,继续呜哇乱叫,好像全世界都欠着它。
怎么办?爹在饭口上,使劲呷了一口酒,还能咋弄,找母猪配对啊!那节骨眼上,要秋收了,大家都忙。队长马三终日嘴上含着铁哨,唧唧响,一天到晚就不得歇息。马车牛车呼啦啦地来去往生产队场院运送苞米穗子,大豆棵儿,稻捆子,哪有空关注青年黑猪发情的事儿。
马三忙,爹也忙,这个地球上的人都在各自忙。唯有小郭在黄昏后的笛声显出些悠闲来,月色朦胧的晚上,他对着一树山梨吹出一支支缠绵的曲子,那曲子如泣如诉,把村庄的夜晚揉成了一汪波澜不惊的池水。许多人枕着这池净水睡去,梦里全是秋季里黄澄澄的粮食。
一阵阵夜风袭来,携带着栀子花的芬芳,在鼾声四起的村庄里漫漶。梅花瞅着爹娘都睡熟了,悄没声地爬起身,循着那只魔笛的丝线,蹑手蹑脚地来跟小郭叔相会。我还没睡,照例走到院外,准备以我的值守去换取又一块麦芽糖。这个晚上,梅花姐却有些反常,她冲我挥挥手,说不用你放哨了你去睡吧。随后挽着小郭叔朝房后的小山坡走去。他们消失在暗影里的轻笑声,就像夜鸟的鸣啼。
青年黑猪在这个夜晚也选择了反叛和逃亡。它闹腾了无数次,也没有人理睬,索性开始自己想办法。瞄准食槽和前方半人高的圈墙,它后退到睡窝的位置,来了个助跑,一个强劲的冲刺,终于挣脱了禁锢火热身体的藩篱。它拱开院门,乐颠颠地奔走在洒满月光的村街上,栀子花的香味对它没有半点吸引力,它嗅觉灵敏,能于浓烈的夜气中剥离出另一种腺体散发的气味,径直奔向村西五婶家的猪圈。那里,五婶家的小母猪正春心荡漾。
第二年开春,五婶家的小母猪得了八只猪羔子,让他们甚是惊异,因为他们从没给母猪配过种。而我娘更不知道,青年黑猪的第一次努力播种,神鬼不知,她也没收到半分回报。
这个夜晚注定不平静。睡了半个时辰的我大伯,被一泡尿憋醒,起身解手时发现梅花不见了踪影,心下便有一团怒火迅速燃起。数月以来,梅花跟那个知青小郭暗地里黏糊的事情,他已有耳闻,只是还一直没能抓住把柄。这阵子没影了,想放骚?想造反?我大伯牙咬得咯噔噔响。他去院子里攥起把铁锨,沿着屯子的土路,朝我家摸了过来,他认为我爹,他这个堂弟,瞒着他和城里来的知青小郭穿一条裤腿子,合伙欺负他们父女。大伯一路咒骂着,将我爹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底朝天,发誓逮着我爹,咔嚓一声,用铁锨劈两半,一半喂猪,一半扔到坟地!
院子里响起大伯狼嚎一般的呼喊,他像一列愤怒的火车直扑过来,让我爹交出他的闺女,交出小郭。刚刚睡熟的我,耳膜被大伯的咒骂震得生疼,惊悸中,听见我爹我娘都起身了。娘有些慌,说老大这是要干嘛,找你拼命来啦?爹也有几分哆嗦,让她赶紧去马三家搬救兵。娘拉开后屋门的门栓,趁着夜色跌跌撞撞地走了。爹瞅瞅我,担心门外的火车逮着那对小野鸳鸯,能要了他们的命,就对我说,你知道他们上哪了?快去告诉他们一声。我点点头,也顺着后屋门跑了出去。
我跑上屋后山坡,四周黢黑,蛇动虫鸣,却早忘了害怕。我不知道小郭叔和梅花姐藏在哪丛树棵子后面,只能一面寻觅着一面低声呼喊。转过一块大岩石,听到近处有小郭叔含混的应答,同时还听到梅花姐黏黏糊糊的哼唧声,我奔过去,看见两个人忙不迭地整理身上的衣裳,梅花姐两个膀子都露在外边,真不要脸。
我说你们快跑吧,我大伯拿着铁锨来劈你们了!梅花姐就跟个受惊的兔子似的,我上我二姨家去!顺着山路就往后坡跑走了。
小郭叔还愣在原地,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此时他笨得像猪,还不如我。我说,你上青年点躲着去吧。他如梦初醒,冲我点点头,也跑走了。
原以为大伯一定会把俺家闹个翻江倒海,最起码会把俺爹揍上个鼻青脸肿,没曾想等我回到家,见人家两个正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闷头抽烟,没事人一样。事后,我才了解了我爹怎样灵机一动,化干戈为玉帛。
面对外面的嚎叫,我爹也不敢轻易造次,只把屋门开了个半扇。我爹说,哥,咋着,你这是要来劈我啊?
大伯说,劈你咋了?快把那两个兔崽子给我交出来,不交出来我就是要劈你!我爹说,这话怪了,你哪只眼看见我把他们藏起来了?孩子大了不由娘,谁管得了哇,要不你进屋来搜搜?大伯没动,仍然叫骂。
我爹突然想起了个事,足以捏住大伯的疼处,提了提底气,猛然吼了声,告诉你!高老四早都想告你了!你还耳后不知天鼓响呢。
大伯瞬时愣怔,没一会儿,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蹲在地上。
高老四常年在外做瓦匠活,给人家盖房垒墙干得欢,没曾想一场大雨把自家的院墙给冲倒了。高老四的女人生得颇丰腴,人送外号大白瓜,尤其一对白生生的奶子,比小孩头都大,比供饽饽都暄,整日在胸前衣服里鼓荡,晃得男人们眼睛疼。大伯身板健硕,长脸上线条硬朗,年轻时就招姑娘们喜欢,中年后也让老娘们眼热。
一个午后,大白瓜截住大伯,想让他帮着去南甸子取些黄土,把塌了的院墙垒上。都是乡里乡亲,大伯哪好拒绝,拴上驴车就跟大白瓜去了南甸子黄泥坑。
这事儿后来怎么被我爹给撞见,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那天我爹霉运冲头,目睹我大伯像啃猪蹄似的,趴在大白瓜身上啃着她的奶子。我爹嘴还牢实,并未把这事往出说,但那两个尝到了甜头的货,此后却不想收手,又被人发现去钻过苞米大田。声音渐渐传到高老四耳朵里,他把大白瓜揍得嗷嗷嚎哭,还扬言要告我大伯调戏妇女。
队长马三被搅扰了好梦,一路不满地嘟哝着,跟着我娘来到家门口,见两个人啥事没有,只是你一根我一根地抽着烟,顿时跳脚骂:什么鳖犊玩意儿,大半夜地把我找来,看你们拉呱放圈儿屁?你们也太不把豆包当干粮了!骂完兀自返身走了。
后来大伯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我只清楚地记得,那晚我爹不得不贡献出一盒他平时不舍得抽的烟,那香烟的名字叫大生产。烟草的香味,像一粒红色胎记,牢牢生长在我的灵魂深处。
事情就此不声不响地给按下去了,再没听过大伯要劈死谁的叫嚣。但接下来的日子,小郭叔和梅花姐却似乎不像往日那么黏腻,他们偷偷约会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小郭叔开始在一些书本上用功,外面传来些消息,据说他家里挺有门路,有机会让他上工农兵大学。院墙外青石板上的笛子声戛然而止,梅花姐跟丢了魂儿似的,有事没事地来我家转悠了几回,又红着眼圈离开了。她说,人家在读书,不希望被人打扰。
小郭叔像是变了个人,整日面无表情,嘴里絮絮叨叨,像被什么阴魂给魇着了。我在心里揣度,难道真应了我大伯的话,小郭叔迟早是要返城的,不可能呆在这穷乡僻壤里。那样,可真就坑了梅花姐了,她把光膀子都露给了人家,这个臭不要脸的,往后可怎么活呢。
家里的黑猪整天腻腻歪歪,哼叫着蓬勃的欲望,养着老母猪的人家,也都到了母猪闹圈的时节,队里的另一头跑卵子供应不上,便自然找到我家。想想我娘确实英明,一筐红皮鸡蛋堵住了马三队长的嘴,虽说有个别人在背后议论,也终究起不了什么风浪,我家的黑猪担当起大任,开始给家里挣钱了。
我娘不让我看黑猪和母猪配对的场景,倒是那些老娘们小媳妇,有些没羞没臊,边看黑猪爬架子,边大呼小叫地开着彼此的玩笑。有人说,妈呀,老王家的,看你看得这个仔细,当心看进眼里拔不出来啦。对方反唇相讥,哎呦嗬,还说俺,都说你家俺妹夫才欢实,没把炕板石顶塌了,把你顶炕洞里边去啊。一群人就放肆地笑起来,声浪拱得房檐都跟着颤动。
两岁的黑猪正是健旺,娘把它也伺候得好,每次配完种都给它骨粉、泡黄豆和生鸡蛋补养。青年黑猪精神抖擞,不仅把本屯的母猪都播了种,连附近屯子的人也闻风而来。他们折一根柳条,一路跟在母猪后边,不必把柳条抽在母猪身上,这些春情荡漾的母猪,闻着味儿就吧嗒吧嗒找来了。不过,黑猪偶尔也挑剔抗命,不愿去爬架子,用母猪尿抹到它鼻子上也不好使。或许在它眼里,也能看出个丑俊来,或是对面的母猪有什么疾病,被它给嗅闻出来,哼哼唧唧怎么也不肯亲近。
黑猪每次爬完架子,娘都能从对方手里接过三块钱,这对那时的农户来说,真算是一笔令人眼热的收入。马三队长的嘴好堵,还有很多张嘴和很多双眼睛却堵不住,那些妒忌和恨,就如漂浮在空中的粉尘,堆积着,弥散着,恨不能化作一团烈火,把我家的黑猪给烧成灰烬。
有人怂恿张兽医,说队里本来有一只种猪就够了,你是专业的,也合法,凭啥让别人再养一头啊?张兽医倒巴不得干独家买卖,但有些事不是他说了算,马三当队长当了十几年了,在上边在村里都颇有威望,他点过头的事情,哪个好去掰扯?何况他自己养的那头公猪,也是年龄大了,有些不争气,骨架子挺大,就是骚劲儿不足,虽说也发情,但骑到母猪脊背上,经常草草了事,没一会就骨碌下来。配种效果不好,别人自然也不找他了,结果让我家的公猪占尽了风头。
张兽医也旁敲侧击过我爹,他不止一次向我爹发难,你家的猪检疫过么?扎过疫苗么?猪的杂病多,你可不能祸害了别人。我爹哪里懂这些,只能唯唯诺诺,从张兽医手里买来各种药喂给黑猪。那些药都死贵,我爹知道对方是加了狠价的。
小郭叔本来都归到青年点去了,但为着复习不被吵闹,又在晚间回到我家西屋来住。他时常熬到半夜,他对我娘说,嫂子,你家的电字儿都算我的,你放心。我娘待小郭叔一直挺好,她觉得这小伙子有情有义,是个叫人信任的人。娘也不想占人的便宜,她说,青年点的伙食吃着总不比家里的上口,以后你晚饭还是来家吃吧。小郭叔笑了,点点头。
入冬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发生个事,我是第二天才听爹娘说起的。半夜里,爹听见圈里的猪挣命一样嚎叫,他起炕出门一看,竟是小郭叔拿着条棒子,在抽打那只他曾尽心照料过的黑猪。我爹都蒙了,说小郭,你这是闹哪样?小郭扔下棒子,样子挺羞愧,嗫嚅着,这猪,这猪,太吵人了。说完回屋收拾了书本,匆匆离开我家,临走还对我爹娘说了句,对不起。
爹有些气愤,跟娘议论,这小子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咋就能为猪叫了几声,就去打咱的猪呢,咱没亏待过他呀。娘倒挺宽容,劝爹,大概是被吵烦了吧,谁还没点脾气呢。
靠近年根的时候,小郭叔最后一次来我们家,他是来跟我们告别的。那晚,素常从不喝酒的小郭叔,跟我爹推杯换盏起来,直把一张白脸喝成了红布。小郭叔说,我也不是翻脸不认人的主,挺大个人还跟猪去治气,本来,我上学的指标很有把握的,可谁曾想,还是被人家后台更硬的人给顶了。
爹娘明白了他那晚为何发脾气,宽慰他,没事啊,人就是这样,一条道被堵了,另一条道就出来了。小郭说是啊,这不,让那顶我的混蛋看看,老子提前招工回城了,比他走得还早!那晚小郭喝得有些张狂,一改他平时文雅的模样,甚至一些粗话也蹦了出来。
酒酣耳热之时,我爹还是多嘴了,问了个敏感问题:小郭,你这一走,就不能回来了吧?
“不能回了,我可算爬出这个坑了。不过我跟你说大哥,你们家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以后我能行了,一定会来看你们。”小郭叔颇兴奋地说。
我爹说,那倒没啥,来的都是客,俺们待谁都一样。那啥,那梅花,你想咋整?
空气似乎一下凝固了。小郭叔又喝了口酒,清清喉咙,“梅花,呃,梅花,其实我们也没啥,真的。我跟你们发誓,我、我没碰过她。”
我娘突然站起,开始收拾桌子,手底有些控制不住,把碗碟撞得乒乓响。“别喝了,喝啥喝啊,好好的人,喝点猫尿四五六不懂了……”
我家的黑猪丢了。
我家的功臣,造钱机器,精力健旺的黑猪,突然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就在小郭叔跟我们告别的第二天晚上,无声无息的,黑猪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娘发疯了一样四处找,甚至都找到二十里外的屯子去。爹则丢了魂一样抽闷烟,娘责骂他他也不吭气儿,只在猪圈周围反复查看,好像他能找到蛛丝马迹破了案似的。
事情很快传遍了全村,邻居们纷纷前来,有的是真诚表示关切,有的则是来看热闹,甚至都流露出喜形于色。他们三三俩俩袖着手,来我家猪圈前,欣赏西洋镜似的,一波来,一波走。张兽医也来过,说那头种猪真不赖,丢了真可惜了。我娘私下说,他那是黄鼠狼哭鸡,假慈悲呢。
黑猪的丢失给了娘一个结结实实的打击,过年都没过好,正月里的一日,她坐在炕上大哭了一场,让我和爹都噤若寒蝉。哭过了,娘说,从今往后,咱再不养种猪了,这事儿遭人眼红,遭人恨,划不来。来年,咱养两头克郎猪,杀了吃肉!
乡间的舌头飞短流长,总会有人时不时提起黑猪的失踪。有的说,这猪就是叫贼给偷走了,每到年根,总有些不要脸的毛贼去偷别人的猪,杀了卖钱;有的私下暗示我娘,说就是张兽医使的坏,他是嫉妒我家才把那黑猪弄走的;还有人说,这事吧,就是小郭他们干的,这帮知青,扛不住嘴馋,弄去吃肉了,以前不就有谁谁家的鸡呀鹅的丢了么?要不是熟人,也弄不走那猪啊。
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说,都能牵动我爹娘涌起一阵子难过。有一次梦里我还梦见了黑猪,只见它蹒跚着从院门外进来,像一个悠闲归家的农夫,甚至还对我说了句什么,把我给吓醒了。醒来我想,这黑猪也不亏呢,不管是死是活,它已经子嗣遍天下了。
转过年的秋天,梅花姐出嫁了,找了邻村的一个石匠。临出门子之前,梅花姐跑到我家西屋,一个人趴在炕上好顿哭。我娘借此告诫我说,你记住蛾子,不管以后咋着,咱一定不去攀谁的高枝儿,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强。我梗着脖子说,我以后不嫁人!
多年以后,我早已嫁人,孩子都挺高了,时常开车回乡下探望爹娘。日子已经今非昔比,连猪肉都懒得吃了,当然,爹娘家的年猪总还是要养。
端起酒杯,我爹时常唠叨的一件事,仍是关于1974年那头黑猪的话题。我爹能回顾起有关那只猪的所有细节,从哪个集上抓来的,怎么喂养的,都给它打过什么针吃过什么药……末了总是总结说,真可惜了那头猪了,要能再养几年,都能给咱家翻新房子了呢。我娘有时不爱听,埋怨道,一喝点酒,就念叨这些,老母猪想起万年糠。都啥时候的事了。
大概三年前,有一次回乡,见爹娘像憋着什么事情,又不怎么想对我说。我便追问,爹终于吐口了,说原来下乡在咱村的那拨知青来过了,有的还带着第二代第三代,乌乌泱泱一大帮。
这些人现在都行了,做商人的,做领导的,出国回来的,啥都有。他们在原先青年点的房子前照相、唱歌,完了还好顿哭。
我忙问,那小郭叔也来了呗?
爹说,就他没来。他现在是一家什么上市公司的老总,忙得很,见天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他还特意录了一段像,问候我跟你娘。
我心忖,全在心了,谁不忙啊,一种托词罢了。
爹接下来一段话让我惊异:“咱那头黑猪,确实是叫那帮知青给弄走偷吃了,小郭不是要走嘛,他们得弄个欢送会,其实也就是嘴馋抗不了,找个由头。
这次来,他们还专程派两个代表,找上咱家门,给送来两千块钱,说是补偿。咳,这些人呀,也难怪,当初还都是些毛头小子。我不要,他们说啥也得给,那就接着吧……”
我感觉自己热血上涌,把头涨得生疼。想恼怒,想骂人,但什么也说不出来。独自走出屋门,我努力想回顾起小郭叔的那张脸,不过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他的那张曾经俊秀的面孔,已然湮没在村子周遭朦胧的景色中。
那一天,南河屯下了一场细雨。杏花在微雨斜风的沐浴下,碎了一地的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