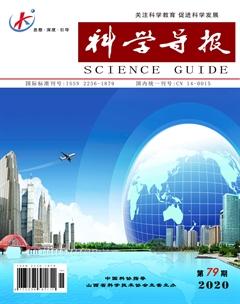汤显祖与龚自珍情思内涵的多向辨析
李佳璇
“情”是汤显祖和龚自珍著作中引人注目的字眼,也是他们文学创作以及美学观念的灵魂。汤显祖和龚自珍的情思多有相似之处,呈现出前后承继的面貌,并且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转变。然而,学者大多将二者的情思分别与三袁的“性灵”说或李贽的童心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不曾对汤显祖和龚自珍二人进行对比探讨。本文将尝试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展现汤显祖与龚自珍情思的发展脉络,从不同阶段对比分析二人情思内涵的异同,探讨社会环境对其二人情思的影响。
一、情思的生成——“外部”与“内部”
汤显祖和龚自珍情思生成的动因不仅与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个体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在“外部”与“内部”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
(一)“外部”的影响
汤显祖身处明末,龚自珍身处晚清,均处于历史大转折、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二人情思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级的扩大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力量,同时产生了一大批代表他们思想意识的思想家,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同时,也带动了俗文学的迅猛发展,小说和戏曲的演出日趋繁荣。在晚清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厦终于日薄西山,清王朝在内部遭遇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同时还面临着西方的领土、资本、文化入侵,从经济命脉和国体人心上打乱了王朝的正常运转。这一时期,西方先进的思想传入中国,经世致用与西学东渐的社会思潮兴起。社会的转型、新思想的传播为汤显祖和龚自珍情思的生成提供契机。
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促使汤显祖和龚自珍希望通过肯定个体情感的合理性、追求无拘束的情感抒发,对统治集团的思想控制进行反抗,并借此表达他们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追求。明代后期,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统治集团维护统治的工具。故而,汤显祖的“至情”观中的“情”强调的是人的七情六欲。而晚清时期,社会内忧外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统治者大兴文字狱,造成社会恐怖。因而,龚自珍“尊情”说中的“情”带有一种大胆的革命色彩,表达的是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需求。
(二)“内部”的生长
除却外部环境的影响,个体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情感体验对二人情思的生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汤显祖早期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内心深处不认可“无欲”说,认为人心不能无欲,将王阳明对“良知”的倡导幻化于“情”。早在《贵生书院说》中,汤显祖的情思便初露端倪。他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所谓“贵生”,即认为生命具有一种值得珍视、宝贵的价值,可以带来情感愉悦的“美”。由此可见,“情欲”早就扎根于汤显祖的心中。而对龚自珍来说,其内心深处早已积淀着对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他在诗中说:“少年哀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其中的“少年哀乐”指的便是龚自珍有一颗能够感应天地万物喜怒哀乐的同情之心,他比别人能够感受人间的痛苦和快乐;“无端”二字也说明了这种心理感受无法用社会环境的影响所解释。
同時,汤显祖曾在遂昌任了五年县官,广泛而深入地接触了群众,对“情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于“良民”和“豪强”的交往过程中,他将“情欲”进行了分类,认为“情欲”有正常合理的“善情”,也有不正常不合理的“恶情”。然而,与汤显祖不同,龚自珍先后任职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官,终日于官场周旋,脱离百姓较远,所以他情思中的“自我”的色彩更加浓重。
二、情感的抒发——“至情”和“尊情”
对个体情感的抒发是汤显祖“至情”观与龚自珍“尊情”说的共同特点,要求抒发真情、张扬个性,成为二人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情感的本质
情感是汤显祖和龚自珍进行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但二人情感的本质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汤显祖所抒发之情的本质是“情欲”,这是其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他在《牡丹亭题记》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牡丹亭》中的“情”不是单纯指向爱情,而是指“性欲”。情欲贯穿了《牡丹亭》的始终,为杜柳二人情爱之内核,具有出生入死的内在超越品质。
与汤显祖不同,龚自珍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是“童心”,这是其情感产生之根本。龚自珍认为“我”是世界的创造者,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为其童心的体现。他在《壬癸之际观胎观第一》中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解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论纪。” 这里的“我”反映了龚自珍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在此基础上,龚自珍在诗中赋予万物以强烈的主观色彩。如“西池酒罢龙娇语,东海潮来月怒明”“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 等诗句中,一个“怒”字用得十分传神,成为句中之眼。“月怒明”“怒于潮”,极言月光之明亮与花影之动荡,是龚自珍本人郁怒的内心情态的反映。
(二)现代的色彩
汤显祖和龚自珍对情感的抒发,逐渐成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潜意识,这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带有现代性的进步色彩。
与其情感的本质相对应,汤显祖的进步色彩表现为其对自由正当的人欲的追求。《牡丹亭》中杜丽娘与陈最良之间形成强烈冲突,可看出汤显祖“情”的思想与程朱理学“理”的思想的严重对峙。同时,汤显祖所追求的情欲包含着“现代的性爱”的成分。在中国古代,夫妻之间往往只有婚姻而没有爱情。在这种背景下,性爱更是羞于启齿的。而汤显祖正是将这一层难以言说的性爱用文学的语言加以渲染。
龚自珍的进步色彩则表现为对自由生长的人格的追求。在以儒家伦理为正统思想的晚清社会中,知识分子大多唯唯诺诺,不敢有主体性的认同,只能在异化自我的客体化中沉浮,廉耻尽失。龚自珍致力于改变这一社会风气,在《病梅馆记》中充分表达了其构建自由人格的主张和向往自由生长的美学观念。文章表面是抒发文人画士对梅花的摧残,实际上是揭露专制主义对人的天性的野蛮戕害。
本文认为,二人情思的思想启蒙价值就在于其进一步关注到了社会的文化风气,关注到了社会群体的精神心理状态。在长期的制度、伦理的压制下,人们逐渐丧失了主体意识,失去了生气和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汤显祖和龚自珍认识到仅仅批判制度弊端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于是便主张抒发个人内心情感,唤起人性和情欲,从而构建自由、健全的人格。
三、自我的压抑——“入世”到“出世”
在以儒家为经典的封建社会中,汤显祖和龚自珍都带有儒家“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他们的情思中包含着对社会的“忧患”之情。但是,儒家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中,二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寄托。
(一)“入世”的理想
在二人的一生中,科举仕途占有较大的比重。二人都曾用浪漫的笔墨描绘了自己心中的美好社会。汤显祖在《南柯记》中写到了淳于棼治理下的南柯郡政治清明、和平富裕的景象,闪耀着作者美好的社会思想。龚自珍在《能令公少年行》中同样用瑰丽的笔墨构造了自己的理想世界,透露着作者积极的情感。
在实现“入世”理想的过程中,二人都不约而同地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不同的是,汤显祖的批判稍显含蓄。《牡丹亭》中杜丽娘回到人间后,拒绝了柳梦梅的求婚,提出“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含蓄地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否定和嘲讽。汤显祖追求自由无拘束的人欲,而这种人欲却只有在梦中或变成鬼魂才能得以实现,现实和梦境的巨大反差表现了封建礼教对人的压制。与之对应,龚自珍的批判则更加大胆直接。他在《题梵册》中云:“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直接表明儒学不过是各类流派中的一种,如何能成为正统思想?
然而,无论含蓄,亦或是大胆,他们心中的政治抱负只能停留于笔端,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使二人的美好幻想沦为泡影。
(二)“出世”的无奈
儒家肯定性善,所以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罪恶,未能有较深刻的剖析。因此儒家的道德思想,对生活变动幅度大,且有深刻痛苦经验的人,显得无力。汤显祖和龚自珍二人的科举之路坎坷,受尽官场倾轧。现实社会的巨大打击使二人体会到了强烈的“存在哀感”,在社会中找不到可以归依的精神本体,于是转而探寻佛教,寻求心灵安慰。与儒家思想不同,佛教观察人生是从负面切入,主张“无明”,认为人类生命本身就是没有明的。汤显祖和龚自珍在现实中遭遇的重大失败、忍受的深刻痛苦,迫切地需要佛教的救赎。
在“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下,汤显祖在《南柯记》和《邯郸记》中流露出“梦了”和“情了”的消极出世思想。《南柯记》中淳于棼梦中经历了情爱、富贵、权势、阿谀奉承后沦为阶下之囚,最后大梦初醒,经老僧点破,参透情梦,遁入佛门。梦境的破灭表现了汤显祖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和抛弃。而蚂蚁王国被暴雨冲垮,也隐含着他对现实政治无药可救的认识。《邯郸记》中的卢生在梦中备受颠簸、享尽荣华,忽然梦醒,尽扫功名富贵之心,登上仙境。
龚自珍常以“翻经写字”来排除内心的痛苦,寻求精神寄托,直接影响了龚自珍诗歌创作的题材和思想。《己亥杂诗》中有许多与和尚、居士往来的诗作,如“龙华相见再相谢,借经公的龙泉僧”。然而,龚自珍的“出世”思想与汤显祖不同,他仍然保留着儒家思想的内核,具有积极向上的情感。《己亥杂诗》中有许多关心民生疾苦、表达自身同情的诗作,如“书生挟策成何济?付与维南织女愁”可见,龚自珍保有儒家经世致用、仁者爱人的内核的同时。又如“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龚自珍默向龙泉剑祝祷自己当年的锋芒能够重新回归。“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情感积极乐观,化腐朽为神奇,进一步表现了他内心的儒家思想。
综上所述,汤显祖和龚自珍情思的生成是“外部”和“内部”的双重驱动,本文在对二人情思的对比辨析过程中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由于社会环境的区别和人生经历、内在体验的不同,汤显祖的情思包含着对人生百态的体察,而龚自珍的情思则包含着浓重的“自我”色彩。
二、湯显祖和龚自珍的情思都注重对情感的抒发,但汤显祖情感的本质是“情欲”,而龚自珍情感的本质是“童心”。
三、汤显祖和龚自珍的情思都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的进步色彩,不同的是汤显祖主要追求自由正当的人欲,而龚自珍向往自由生长的人格。
四、汤显祖和龚自珍的情思中都带有“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却有着不同指向的内核。汤显祖后期情感的消极色彩浓重,挣扎后选择皈依佛门,忘却俗世;而龚自珍历经沉浮后仍保有积极向上的情感,体现出“外佛内儒”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