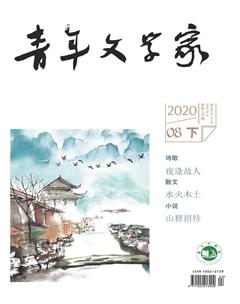互文与诗性抒写
摘 要:张承志在《黑骏马》小说中,以“草原人”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骑马寻妹,接受心灵之问的故事。古调《黑骏马》的苍凉基调也自小说文本中升华出来,浸润了作家的心理历程,承载着作品的精神内核。这部有着交错时间线的中篇小说,以其互文性和充满诗性的抒写,提供了理解张承志和草原的文学性方式。
关键词:黑骏马;互文性与诗性;人物塑造;写作特征
作者简介:孟亚杰(1998.2-),女,汉族,河南商丘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黑骏马》发表于1981年,当时的张承志刚毕业,并被分配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距离他初到内蒙古草原开始插队生活,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对于已经返城的知青张承志来说,在新环境下,过往的生活记忆也会被重构。不同的作家因不同的插队经历而有迥异的体验,从而进行不同角度的知青生活再阐释及建构。不同于部分作家对于“知青运动”的否定态度,张承志认为“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黑骏马》正是基于这一滋养。张承志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用独特的互文构思与诗性抒写,不仅讲述了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和索米娅之间的爱情悲剧,更书写了在新旧观念冲突下草原儿女的抉择和对生命的礼赞,至今依然散发着特殊的魅力。
一、经历互文:古调《黑骏马》与白音宝力格
“一个哥哥骑着一匹美丽绝伦的黑骏马,跋涉着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寻找他的妹妹的故事。”这是古调《黑骏马》的大致内容。
张承志以一首古调中的故事为互文线索,串联起白音宝力格宝力格的前半生经历,让人感叹其匠心独運。“互文性”的基本内涵是:“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1]对于古调来说,这部同名的小说不仅仅是吸收,更是作家张承志在把握了古调苍凉基调的基础上,融入了张本人对草原文化的思考,而后对古调文本的一次升华。作家从小说文本外部,为小说掘得了一口灵感的源泉。
如果说,贯穿于行文间的古调《黑骏马》已是一条明晰的线索,那么分散于各章节开头的歌词引用更如全文的有机脉络,是小说文本内部的隐含逻辑思路。两者可以与白音宝力格宝力格的经历互作参照,不时提示着读者,白音宝力格宝力格的经历将与古调《黑骏马》构成丝丝入扣的互文,白音宝力格的形象就是古朴歌谣中的牧人形象。比如,第二节开头引用的“妹妹远嫁”歌词,也正是在这章中,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得知了索米娅嫁人的消息、决心前往寻她、开始回忆往昔。又如,最后一节开头的引用也正好紧扣了最后一章白音宝力格懂得了索米娅的改变,并最终与往昔告别的内容。
T·S·艾略特曾提出:“没有任何诗人,没有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能够单靠自己获得全部意义。他的意义,人们对他的欣赏就是欣赏他和已故诗人及艺术家的联系。”张承志通过“互文性”吸收了古调的文本,在获得了古歌中的意义及精神内核之后,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从文本外部来看,“互文性”代表着小说与古调文本的彼此牵涉,而自小说文本内部进行观照,则见出白音宝力格宝力格与历史上千万个牧人之间的暗合。
正因这作用于文本内外的“互文性”,使得作家与古调、白音宝力格与古调中的牧人之间的关系真正打通了。在作家的笔下,白音宝力格才能从自身经历出发,真正唱懂苍凉的古调,成为了一个清醒着的人。他发现,古调中的悲剧故事、深沉爱情,都只是一框架和依托,唯有千百年来流转的复杂且神秘的草原灵性,才是古歌真正所要表达的核心要义。这不仅仅是小说文本内部的白音宝力格的发现,更是身处文本之外的作家对于草原灵性、古歌的理解、阐释。
二、情感互文:在交错时间线中的跋涉
骑马寻妹本是现实素材,而古调以歌谣化的语言,将素材转化为文本。作家张承志在歌谣文本的基础上,通过交错呈现时间线等程序,将素材及文本重新编排,并为之扩充、升华,使得小说文本具备了异于古调的美感。
重返柏勒根河畔的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已是一位畜牧厅的科学工作者,他甚至认不出胯下的马正是自己曾朝夕相处多年的钢嘎·哈拉。与牧羊人的对话,让他回想起深埋于心的生活图景。随着回忆的深入,白音宝力格开始了记忆与现实的双重跋涉,其人物形象也开始趋于完整。
张承志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分开讲述往昔与现实,而是交错呈现两者。这样一来,《黑骏马》有了两条时间线,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过去和现在也于交错的叙述中得以呈现。在小说的前六节中,现实与记忆的对应关系较为明显。每一节都有两个白音宝力格宝力格,且两者的形象差别极大。一个是年纪尚轻,品尝过亲情、爱情滋味,后又离故乡而去的白音宝力格;另一个是在现实的跋涉中,感叹曾经有过不当言行的白音宝力格。而当时空的界限被作家打破,主人公便有了穿梭的自由。于是在现实、记忆的来回拉锯中,白音宝力格开始自省。“我们总是在现实的痛击下身心交瘁之际……”这段话,是他的自白,也是他为什么启程寻找索米娅的原因。正是多年之后的遗憾、追悔,不仅促使他踏上现实的路程,欲探故人,也让他沉潜入记忆之海,在追忆中不断认识到自己曾经的过错。
这样一来,经过时间线的“暗示”,过去与现在两条线分别呈现了两个白音宝力格宝力格的形象。与此同时,作品的情绪流及深层结构也随之浮现。
此外,从深层结构来看,时间线还交代了理想与现实、现代与草原的关系。在过去的时间线中,少年白音宝力格宝力格怀揣着梦想,渴望学习现代知识,飞出草原。他对老兽医使用的“旁门左道”有些怀疑,希望接触到“真正的牧业科学”。于是少年选择在去参加为期半年的牧技训练班,又在看到索米娅怀孕后,远走农牧学院。然而,现实却是有别于理想的存在。“白音宝力,你得到了什么呢?……”这段独白,是白音宝力格心声的吐露,也让人看出一个人在理想与梦想之间的挣扎与无奈。
过去的白音宝力格宝力格,与奶奶的想法不同;而重返草原的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则与索米娅等生活在草原的人们想法各异。两条时间线中的态度之别,代表了现代与草原的关系。得知索米娅怀孕后,少年白音宝力格的第一反应是:“怎么?难道那样的坏蛋还配活到明天?”但奶奶却认为女人世世代代便是如此。这里作家将两人的观点并置,从情节来看为下文白音宝力格出走作了铺垫,但从深层意义来看,却是将现代与草原文明的差异摆在台面上。同样的,在现实的时间线中,白音宝力格宝力格与索米娅也有观念上的碰撞。为了安抚其其格,索米娅谎称白音宝力格宝力格是女儿的生父;然而,成年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却认为孩子内心深处的创伤并不会随时间而愈合,并没有帮助索米娅巩固这个善意之谎。让白音宝力格作出这一选择的,是在城里看到的一张照片,上面的女孩無忧无虑地笑着,与眼前这个严肃的小女孩完全不同。草原上的索米娅仅希望女儿有个企盼,而在现代文明浸润已久的白音宝力格却认识到创伤的难愈性,这又见出文明之别。
两条交错的时间线,贯穿了“跋涉”这一过程,让人物游走于现实与记忆之间。时间线不仅完整呈现主人公形象及其情绪流变化,还让现代与草原文明之别得以并置,使得小说结构多了二元对立的层级,不再局限于人与人,而是扩展至文明与文明。原本仅是作家传声筒的人物,成为了文明之间碰撞的承载者,可见作家的运思与笔力。
三、张承志与《黑骏马》
贾植芳先生曾指出作家人格境界与写作的关系,“作家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格发展史的表现和反映形式。”[2]理解小说《黑骏马》的方式,除了关注文本本身,另一种方式便是从作家张承志的经历和人格入手。
《黑骏马》创作于八十年代初期,正值“知青文学”的创作热潮。因此,其创作者也被冠以“知青作家”的称号。然而,张承志却与许多“知青作家”有别。
文革后,由于对所处环境及身份认识的含糊不清,“知青作家”群体有普遍的焦虑感,找不准自己在城市的位置。因此,知青生活便被视为“确定现实位置而不断挖掘、重新审察的对象”[3],成为了待加工和重构的写作素材。正如张承志本人所认为的由底层体验形成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建构着他们的文学审美与判断,再加之重构记忆所倚仗的经历因人而异,“知青小说”便呈现出了多重阐释维度。这其中,既有“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也存在着对这场运动全盘否定的声音。
对于张承志来说,他和其他知青一样,离开了插队之地,但他却开始了心灵的“跋涉”,与草原越发相近。这一趋近的心理距离的书写,正从《黑骏马》等早期作品中开始发端。
“草原文化的粗犷博大,更对张承志文化幻灭后的心灵构成深刻而强大的浸润和影响力。”[4]他将自己汲取到的精神力量,熔铸于白音宝力格的跋涉与蜕变之中。因此,这个生于斯、长于斯,外出接触了现代文明,而又回归的年轻人,其实就是张承志的化身,是作家以“草原人”的视角书写、歌颂和回馈草原的产物。与其他知青文学作品中明显带有外来色彩的人物形象相比,白音宝力格就有了明显的差别。这显然与张承志本人的草原扎根生活和对草原的讴歌息息相关,也得益于张承志扎得更深的乡土之根,对于“第二故乡”有着更为老到和民间式的认识。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张承志通过一系列作品,完成一次次心灵上的蜕变,最终进入“以真正民间的文化、情感和视野来审视生活、认识生活的全新境界。”[5]经历心灵上的煎熬和考验的,不只是小说中的一位位主人公,更是张承志自己。作为作家早期的作品,《黑骏马》已有了不同于知青式的审察视角和观照,是作家尝试以草原人身份,歌颂心爱草原之作。对于张承志的创作史而言,《黑骏马》是其心灵跋涉的一部分,并最终帮助作家走向心灵皈依。
注释:
[1]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J].文学评论,2017(02):114-122.
[2]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25.
[3]樊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431.
[4]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与文化困境[J].文学评论,1999(06):118.
[5]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与文化困境[J].文学评论,1999(06):119.
参考文献:
[1]张承志.《黑骏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3]张承志.《风土与山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J].北京:文学评论,2017(02):114-122.
[6]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25.
[7]樊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431.
[8]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与文化困境[J].北京:文学评论,1999(06):118.
[10]马丽蓉.“在路上”的张承志[J].宁夏: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1999(02):91-95.
摘 要:张承志在《黑骏马》小说中,以“草原人”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骑马寻妹,接受心灵之问的故事。古调《黑骏马》的苍凉基调也自小说文本中升华出来,浸润了作家的心理历程,承载着作品的精神内核。这部有着交错时间线的中篇小说,以其互文性和充满诗性的抒写,提供了理解张承志和草原的文学性方式。
关键词:黑骏马;互文性与诗性;人物塑造;写作特征
作者简介:孟亚杰(1998.2-),女,汉族,河南商丘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黑骏马》发表于1981年,当时的张承志刚毕业,并被分配到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距离他初到内蒙古草原开始插队生活,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对于已经返城的知青张承志来说,在新环境下,过往的生活记忆也会被重构。不同的作家因不同的插队经历而有迥异的体验,从而进行不同角度的知青生活再阐释及建构。不同于部分作家对于“知青运动”的否定态度,张承志认为“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黑骏马》正是基于这一滋养。张承志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用独特的互文构思与诗性抒写,不仅讲述了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和索米娅之间的爱情悲剧,更书写了在新旧观念冲突下草原儿女的抉择和对生命的礼赞,至今依然散发着特殊的魅力。
一、经历互文:古调《黑骏马》与白音宝力格
“一个哥哥骑着一匹美丽绝伦的黑骏马,跋涉着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寻找他的妹妹的故事。”这是古调《黑骏马》的大致内容。
张承志以一首古调中的故事为互文线索,串联起白音宝力格宝力格的前半生经历,让人感叹其匠心独运。“互文性”的基本内涵是:“每一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1]对于古调来说,这部同名的小说不仅仅是吸收,更是作家张承志在把握了古调苍凉基调的基础上,融入了张本人对草原文化的思考,而后對古调文本的一次升华。作家从小说文本外部,为小说掘得了一口灵感的源泉。
如果说,贯穿于行文间的古调《黑骏马》已是一条明晰的线索,那么分散于各章节开头的歌词引用更如全文的有机脉络,是小说文本内部的隐含逻辑思路。两者可以与白音宝力格宝力格的经历互作参照,不时提示着读者,白音宝力格宝力格的经历将与古调《黑骏马》构成丝丝入扣的互文,白音宝力格的形象就是古朴歌谣中的牧人形象。比如,第二节开头引用的“妹妹远嫁”歌词,也正是在这章中,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得知了索米娅嫁人的消息、决心前往寻她、开始回忆往昔。又如,最后一节开头的引用也正好紧扣了最后一章白音宝力格懂得了索米娅的改变,并最终与往昔告别的内容。
T·S·艾略特曾提出:“没有任何诗人,没有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能够单靠自己获得全部意义。他的意义,人们对他的欣赏就是欣赏他和已故诗人及艺术家的联系。”张承志通过“互文性”吸收了古调的文本,在获得了古歌中的意义及精神内核之后,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从文本外部来看,“互文性”代表着小说与古调文本的彼此牵涉,而自小说文本内部进行观照,则见出白音宝力格宝力格与历史上千万个牧人之间的暗合。
正因这作用于文本内外的“互文性”,使得作家与古调、白音宝力格与古调中的牧人之间的关系真正打通了。在作家的笔下,白音宝力格才能从自身经历出发,真正唱懂苍凉的古调,成为了一个清醒着的人。他发现,古调中的悲剧故事、深沉爱情,都只是一框架和依托,唯有千百年来流转的复杂且神秘的草原灵性,才是古歌真正所要表达的核心要义。这不仅仅是小说文本内部的白音宝力格的发现,更是身处文本之外的作家对于草原灵性、古歌的理解、阐释。
二、情感互文:在交错时间线中的跋涉
骑马寻妹本是现实素材,而古调以歌谣化的语言,将素材转化为文本。作家张承志在歌谣文本的基础上,通过交错呈现时间线等程序,将素材及文本重新编排,并为之扩充、升华,使得小说文本具备了异于古调的美感。
重返柏勒根河畔的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已是一位畜牧厅的科学工作者,他甚至认不出胯下的马正是自己曾朝夕相处多年的钢嘎·哈拉。与牧羊人的对话,让他回想起深埋于心的生活图景。随着回忆的深入,白音宝力格开始了记忆与现实的双重跋涉,其人物形象也开始趋于完整。
张承志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分开讲述往昔与现实,而是交错呈现两者。这样一来,《黑骏马》有了两条时间线,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的过去和现在也于交错的叙述中得以呈现。在小说的前六节中,现实与记忆的对应关系较为明显。每一节都有两个白音宝力格宝力格,且两者的形象差别极大。一个是年纪尚轻,品尝过亲情、爱情滋味,后又离故乡而去的白音宝力格;另一个是在现实的跋涉中,感叹曾经有过不当言行的白音宝力格。而当时空的界限被作家打破,主人公便有了穿梭的自由。于是在现实、记忆的来回拉锯中,白音宝力格开始自省。“我们总是在现实的痛击下身心交瘁之际……”这段话,是他的自白,也是他为什么启程寻找索米娅的原因。正是多年之后的遗憾、追悔,不仅促使他踏上现实的路程,欲探故人,也让他沉潜入记忆之海,在追忆中不断认识到自己曾经的过错。
这样一来,经过时间线的“暗示”,过去与现在两条线分别呈现了两个白音宝力格宝力格的形象。与此同时,作品的情绪流及深层结构也随之浮现。
此外,从深层结构来看,时间线还交代了理想与现实、现代与草原的关系。在过去的时间线中,少年白音宝力格宝力格怀揣着梦想,渴望学习现代知识,飞出草原。他对老兽医使用的“旁门左道”有些怀疑,希望接触到“真正的牧业科学”。于是少年选择在去参加为期半年的牧技训练班,又在看到索米娅怀孕后,远走农牧学院。然而,现实却是有别于理想的存在。“白音宝力,你得到了什么呢?……”这段独白,是白音宝力格心声的吐露,也让人看出一个人在理想与梦想之间的挣扎与无奈。
过去的白音宝力格宝力格,与奶奶的想法不同;而重返草原的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则与索米娅等生活在草原的人们想法各异。两条时间线中的态度之别,代表了现代与草原的关系。得知索米娅怀孕后,少年白音宝力格的第一反应是:“怎么?难道那样的坏蛋还配活到明天?”但奶奶却认为女人世世代代便是如此。这里作家将两人的观点并置,从情节来看为下文白音宝力格出走作了铺垫,但从深层意义来看,却是将现代与草原文明的差异摆在台面上。同样的,在现实的时间线中,白音宝力格宝力格与索米娅也有观念上的碰撞。为了安抚其其格,索米娅谎称白音宝力格宝力格是女儿的生父;然而,成年白音宝力格宝力格却认为孩子内心深处的创伤并不会随时间而愈合,并没有帮助索米娅巩固这个善意之谎。让白音宝力格作出这一选择的,是在城里看到的一张照片,上面的女孩无忧无虑地笑着,与眼前这个严肃的小女孩完全不同。草原上的索米娅仅希望女儿有个企盼,而在现代文明浸润已久的白音宝力格却认识到创伤的难愈性,这又见出文明之别。
两条交错的时间线,贯穿了“跋涉”这一过程,让人物游走于现实与记忆之间。时间线不仅完整呈现主人公形象及其情绪流变化,还让现代与草原文明之别得以并置,使得小说结构多了二元对立的层级,不再局限于人与人,而是扩展至文明与文明。原本仅是作家传声筒的人物,成为了文明之间碰撞的承载者,可见作家的运思与笔力。
三、张承志与《黑骏马》
贾植芳先生曾指出作家人格境界与写作的关系,“作家的生活史和创作史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格发展史的表现和反映形式。”[2]理解小说《黑骏马》的方式,除了关注文本本身,另一种方式便是从作家张承志的经历和人格入手。
《黑骏马》创作于八十年代初期,正值“知青文学”的创作热潮。因此,其创作者也被冠以“知青作家”的称号。然而,张承志却与许多“知青作家”有别。
文革后,由于对所处环境及身份认识的含糊不清,“知青作家”群体有普遍的焦虑感,找不准自己在城市的位置。因此,知青生活便被视为“确定现实位置而不断挖掘、重新审察的对象”[3],成为了待加工和重构的写作素材。正如张承志本人所认为的由底层体验形成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建构着他们的文学审美与判断,再加之重构记忆所倚仗的经历因人而异,“知青小说”便呈现出了多重阐释维度。这其中,既有“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也存在着对这场运动全盘否定的声音。
对于张承志来说,他和其他知青一样,离开了插队之地,但他却开始了心灵的“跋涉”,与草原越发相近。这一趋近的心理距离的书写,正从《黑骏马》等早期作品中开始发端。
“草原文化的粗犷博大,更对张承志文化幻灭后的心灵构成深刻而强大的浸润和影响力。”[4]他将自己汲取到的精神力量,熔铸于白音宝力格的跋涉与蜕变之中。因此,这个生于斯、长于斯,外出接触了现代文明,而又回归的年轻人,其实就是张承志的化身,是作家以“草原人”的视角书写、歌颂和回馈草原的产物。与其他知青文学作品中明显带有外来色彩的人物形象相比,白音宝力格就有了明显的差别。这显然与张承志本人的草原扎根生活和对草原的讴歌息息相关,也得益于张承志扎得更深的乡土之根,对于“第二故乡”有着更为老到和民间式的认识。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张承志通过一系列作品,完成一次次心灵上的蜕变,最终进入“以真正民间的文化、情感和视野来审视生活、认识生活的全新境界。”[5]经历心灵上的煎熬和考验的,不只是小说中的一位位主人公,更是张承志自己。作为作家早期的作品,《黑骏马》已有了不同于知青式的审察视角和观照,是作家尝试以草原人身份,歌颂心爱草原之作。对于张承志的创作史而言,《黑骏马》是其心灵跋涉的一部分,并最终帮助作家走向心灵皈依。
注释:
[1]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J].文学评论,2017(02):114-122.
[2]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25.
[3]樊星.《中國现当代文学史(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431.
[4]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与文化困境[J].文学评论,1999(06):118.
[5]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与文化困境[J].文学评论,1999(06):119.
参考文献:
[1]张承志.《黑骏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3]张承志.《风土与山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王爱松.互文性与中国当代小说[J].北京:文学评论,2017(02):114-122.
[6]贾植芳.《贾植芳文集(理论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25.
[7]樊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431.
[8]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与文化困境[J].北京:文学评论,1999(06):118.
[10]马丽蓉.“在路上”的张承志[J].宁夏: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1999(02):91-95.
——读《黑骏马》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