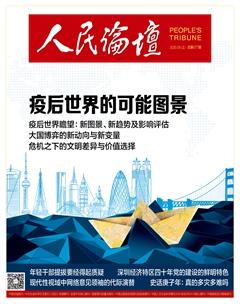现代性视域中网络意见领袖的代际演替
张森

【关键词】网络意见领袖 现代性 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站在2020年这一特殊时间点上,回望网络意见领域的过往十年,能够明显感受到其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首先,在主体身份上,2010年前后,网络意见领袖以资深媒体人、专家学者、大公司高管和部分文娱明星为主;近年来,网络意见领袖则转向以李佳琦、李子柒为代表的“网络红人”(简称“网红”)为主。此外,活跃在知乎、果壳等问答社区的一些知识型意见领袖影响力日增。其次,在活跃平台上,2010年前后,网络意见领袖集中活跃在各大微博及少数博客平台;近年来,网络意见领袖实现了网络平台的整体迁移,其主要态势是从微博、博客等传统平台转向抖音、小红书等新兴直播、短视频平台。最后,在影响的领域上,2010年前后,网络意见领袖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以公共事务为主,他们也因此以“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的整体面貌为公众所熟知。近年来,网络意见领袖活跃的领域则转向私人生活,包括美妆、美食等生活领域以及对日常现象进行科学解释等。由此可以判断,过往十年间我国的网络意见领袖已经完成了一次代际演替,即从先前以公知型意见领袖为主发展到目前以网红型、知识型意见领袖为主。
有观点将这一变化归结为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公知型意见领袖在“净网”等一系列网络监管行动下的衰落;二是直播、短视频等新兴传播方式的兴起催生了“网红”群体的出现,迅速填补了前者留下的空缺。正是这一“打”一“拉”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了当下网络意见领袖的格局。这一逻辑看似合理,但经不起推敲。一方面,即便有政策因素的影响,但对于公知型意见领袖式微而言仅属外因,同时也并不必然导致其被后来崛起的网红型、知识型意见领袖所替代。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持有一种“意见领袖本位”的立场,即认为只要有意见领袖出现,自然就会有追随者。事实上,意见领袖的出现是其本人与追随者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意见领袖作为行动者获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本,然而追随者对意见领袖认可与否,才是决定后者地位能否确立的关键性因素。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网络意见领袖的传播行为必然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框定和制约。因此,想要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网络意见领袖的代际演替,应将其置于过往十年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解读。
“个体化”趋势的出现
过往十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加速蔓延和扩散。按照西方的经验,随着现代性的深度卷入,整个社会将进入“个体化”阶段。所谓“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指社会的行动和思考是以个人为基础,而不是传统的组织、家庭等结构性因素。在个体化社会,如德国学者贝克(U.Beck)所言:“在人类历史上,个人第一次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同时“个人成为基本社会结构”。
现在就断言中国已进入个体化社会显然为时尚早,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显露出个体化的趋势,特别是在互联網领域,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网络活跃群体的代际更替——“80后”“90后”成为网络上的主要行动者和发声者。相对于前辈,他们较少受到传统和结构的束缚,以实现个人理想和人生价值为目标,更注重个体的感受。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网络意见领域。
个体化推动社会“平视”视角的形成,公众的关注重心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
传统上,人们习惯于“你说我做”,服从规则,崇尚权威。随着现代性的渗透、个体化的深入,人们开始“做自己”,逐步赋予个体更多的能动性。相比于十年前,当前网络意见领袖最大的特点无疑是其“平民化”特征。2012年发布的国内第一份《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意见领袖都是掌握相当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社会精英,草根网民、普通网民微乎其微。这是互联网经历了“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必然结果。互联网对于社会传播业态的最大改变,是将传统的以机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改变为今天的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性传播,具有天然的反中心取向。但与此同时,互联网信息的海量性和碎片化等特征,又增加了从中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和成本。信息筛选和事实研判的需要,必然产生新一轮的中心建构,社会精英很容易凭借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获得中心位置。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Merton)曾将意见领袖区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能够在多个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多型意见领袖和只在某一专门领域拥有较多话语权的单型意见领袖。以此观之,公知型意见领袖多为多型意见领袖,他们正是凭借追随者对其的“仰视”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拥有话语权。但随着民众整体上降低了对权威的盲从、社会“平视”视角的形成,社会精英逐渐退出舞台中央,取而代之的是后起的平民意见领袖。后者虽然也有众多追随者,但只能在某一特定的领域保有影响力,显然属于单型意见领袖。追随者对意见领袖的态度也不再仅仅是从前的仰慕和追随,更多的是认同和喜爱。
网络意见领袖代际演替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其影响的领域由公共事务转向私人生活,这同样是个体化推动的结果。个体化强调人们脱离了传统的阶级纽带和家庭扶持等结构性约束,逐渐开始转向对其个人命运的关注。较之以往,个体化社会中的人们更关注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沿着这个思路,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从事美妆行业的李佳琦和薇娅、专注于美食研究的李子柒等人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毫无疑问,不论是美妆还是美食,对于个体而言,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能够提升其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领域,活跃于该领域的意见领袖自然能够引发更多的关注。可以预见,时尚生活、娱乐消遣领域的“吸粉”态势还将持续下去。
在个体化社会,个人成为社会的能动塑造者。照此逻辑,个人也自然是问题的主要解决者和责任的承担者。个体化在增加个人自由度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共同组成的体系——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这一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整个社会对于专业性的要求空前增加。
个体化造成社会成员强烈的“认同渴望”
现代性所蕴含的脱域(disembeding)机制意味着“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这造成在现代情境下,人们很难对自我身份以及行为的社会物质环境的持续稳定怀有信心,“本体安全感”的获得也就更加艰难。
个体化社会成员的当务之急是社会认同建构问题。传统上,人们的社会认同是被“预先设定”的,不需要个人去建构。然而随着现代性的深入,特别是在个体化阶段,“每个人不得不在各种选项间作出选择,包括自己想要认同的群体和亚文化。事实上,人们也要去选择或改变自己的社会认同”。
近年来,消费主义在中国兴起,人们的讨论多集中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费能力增强,甚至归咎于“李佳琦们”的推波助澜。事实上,经济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解决的只是需要问题,而消费社会来临的背后则是欲望在推动。法国学者福柯(M.Foucault)曾经将消费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认为人们通过消费实现社会区分,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事实上,在消费主义的驱动之下,人们的每一次购买行为绝不仅仅着重于商品本身,而是能动性地指向这种行动背后的文化意涵。一些亚文化群体的消费行为恰恰是其内部进行交流、构建认同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实现对主流文化的群体性对抗。比如一些粉丝的消费行为背后有着“生产”的意涵,即帮助构建粉丝群落。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Bauman)所说,购物本质上是一种驱除心魔(inner demons)的仪式,它可以帮助人们对抗让人神伤的不确定性和令人苦闷的不安全感。
个体化社会的“集体心理寻唤”
看过李子柒作品的人,都会被她所演绎的田园牧歌生活所打动,这正反映了现代人对他们头脑中所想象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法国学者丹纳(H.Taine)曾指出,“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这说明文化作品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按照文化心理学的观点,特定的社会造就了个体生命间相似的意识形态结构,由此产生一种集体性心理缺失与心理寻唤,能够有效回应这种心理缺失与心理寻唤的作品将会被更多人所选择。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快”,李子柒作品中所塑造的慢生活、烟火气,恰好迎合了现代人所期待的理想图景,因此在社会公众间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面对近年来直播、短视频行业的强势兴起,很多人将之归结为4G技术的成熟,使得以往制约网络视频行业的主要瓶颈随之破解。但这只解释了这些新兴传播形式普及的可能性,并不能解释它广受欢迎的事实。按照美国学者凯瑞(J.Carey)的观点,对技术的分析不能脱离于文化。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心智”协同的产物,是人类解决问题,让事物得以运行或让事物运行得更加有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就是文化。在现代社会,正因为人们以个体的形式面对各种风险,在坚持个人自主性的同时,“知道与自己面临相同问题的其他人怎样处理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电视上的谈话类节目给观众提供的正是其他人的处事方式,它曾经的流行正是“了解他人的生活”的心理在起作用。互联网出现后,先是微信朋友圈的風靡,而后是直播、短视频等传播形态的广受欢迎,背后都遵循了同样的逻辑。
总而言之,过往十年发生在国内网络意见领域的意见领袖代际演替是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加速扩散和蔓延所引发的个体化进程出现的自然结果。中国社会正在显露的个体化趋势一方面改变着社会底层结构,另一方面也推动着社会心理的整体转型。从人类社会的总体经验看,现代性的扩散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值得深思和警惕。
一是私人领域的兴起对公共领域的“反向侵蚀”问题。一直以来,人类社会都沿着增加个人的自主性,最大限度争取个人自由的路径在发展,即力图将个人从社会结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在个体化趋势的推动之下,人们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受到抑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日趋模糊。这反映在传播领域,私人问题日益取代公共事务,在公共领域中被呈现和讨论。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大量有关私人生活的节目出现,如“真人秀”节目的泛滥;另一方面,一些本属公共议题的讨论也有“私人化”的倾向。而现代社会治理,同样离不开公共空间的营造和公共权力的介入。如何重新营造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重构公共空间、重建公共认同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是“娱乐至死”可能卷土重来。上世纪80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以波兹曼(N.Postma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深深担忧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波兹曼将过去以印刷媒介为中心的时代称为“阐释时代”,将当时以电视媒介为中心的时代称为“娱乐业时代”。他指出,文字是严肃的,它代表着理解和信息的传递,而电视的表达形式因为图像的介入掺杂了美学和心理学的学问,往往是娱乐性的、碎片化的、排斥思考与逻辑的,(在其中)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这促使我们对今天直播、短视频行业的兴起保持足够的警醒。在当今视频行业藉由资本力量推动而强势兴起的大背景下,如何让大众避免再次沉迷于视频这种娱乐化的媒介接触,以致重新陷入“娱乐至死”的窘境,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强文化范式视域下社会治理的文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BSH02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马杰伟、张潇潇:《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喻国明:《互联网是高维媒介:一种社会传播构造的全新范式——关于现阶段传媒发展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辨正》,《编辑学刊》,2015年第4期。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张文杰、何博闻译:《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④[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编/银冰瑶 美编/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