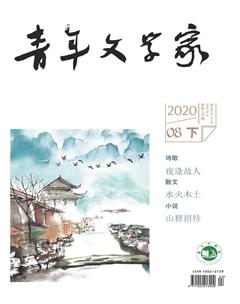中西“礼仪之争”与文化交流中的矛盾处理
摘 要:礼仪之争是中西交流史上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往往被认为是中西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历史影响,主要责任人,中西各有说法,从哲学、文学、社会学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本文则主要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参考萨义德和周宁的理论,再次分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从这些原因入手,为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现时代的跨文化交际的事业,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关键词:礼仪之争;跨文化交际;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袁佳怡(1995.4-),女,汉,山西太原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2
一、礼仪之争事件始末
“礼仪之争”发生于清康熙皇帝在位年间,是一场关于中国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拜和基督教相互之间包容共生问题的争论。争论的起源在于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西方传教士,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基督教的传播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康熙皇帝不满罗马教廷的专断而全面禁教。这次争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在中西方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对此问题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明代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以耶稣会为多,他们这一行动的宗教背景,在于欧洲范围内天主教的复兴。一些新的修会成立了,他们充满着强烈的使命感,要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海外去。耶稣会的教士在沙勿略的带领下,在许多东方古老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宗教问题上的妥协。不只是在中国,也出现在耶稣会到达的其他许多国家之中。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中国生活的融入和适应,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动机之上的。利玛窦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经籍之中的许多说法,与西方基督教的观念的区别只在于名不同,但实际上的内核是一致的。因此利玛窦积极学习中国经典,力图做到中西双方之间的互相理解,是一种根据中国本土进行改造之后的本土化的宗教传播策略。具体包括承认中国人民的祭孔和祭祖不违反基督教的一神论原则,因为“他们只感谢天与地但并不向天和地要求天堂的福乐。”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人的排斥心理,也以此说服了罗马教廷中国自身的习俗可以和基督教的信仰实现共存。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的统治阶级对思想上的渗透非常警惕,所以选择从器物入手引发其对于伦理道德的兴趣,为了融入中国士大夫阶层,他主动改变装束,努力学习儒家经典,最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士大夫的戒心。不可否认他的行为确实在传教初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中国统治者的认同,这一点从康熙四十六年所下达的禁教敕令中也可以看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从表面来看,中西文化这次相互交流的惨淡收场,原因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欧洲的教会自身之间的斗争,影响了在华传教士的行为,导致了中国统治者对于传教活动的警觉,从而禁止传教,甚至埋下了对西方的不信任情绪的根由。而对西方世界来说,采用这样的传教策略,也是为了扎根中国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性的策略,一旦西方教廷认为自己的势力已经强大,为了维护自身宗教的纯洁性,教廷势必会提出不同意见。毕竟儒生祭孔等行为,如果想要证明其不是宗教异端的话,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二、礼仪之争的原因和影响
从表面上来看礼仪之争的爆发在于传教士之间争论和分歧的扩大,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一次激烈交锋。中国怎样认识西方,而西方是如何看待中国,二者之间认知和观念的巨大差异才是背后真正的症结所在。
利玛窦去世之后,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主要领头人变为了龙华民,他带头反对利玛窦的主张和策略,认为中国的祭孔和祭祖是偶像崇拜,这与基督教的信仰根基是存在严重冲突的。但矛盾的真正爆发还在于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到来,他们与耶稣会的争论,真正引发了“礼仪之争”。二者在中国争执不休,而罗马教廷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免不了偏听偏信。而在教廷仍摇摆不定时,教廷在华代理人颁布禁令,禁止基督教徒祭孔祭祖,从而触怒了康熙皇帝,言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就“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关于此事的思考,安希孟曾经把此事定义为是基督教内部不同教会之间为了争夺地盘而进行的利益斗争,而非所谓冠冕堂皇的神学分歧。因为教会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因此发言权是归于罗马教会的,所以主要责任归于康熙皇帝,这是不客观的。李秋零先生认为,根源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这大致是没有问题的,而中西文化的差异为何会引发惨烈的斗争,则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
礼仪之争的后果是惨烈的,虽然在欧洲阴差阳错导致了汉学的兴盛,但却导致了中国社会对于西方的冷淡,中国人民对西方人的敌意。和禁教一起到来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全面沉寂。闭关锁国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中国与世界的隔绝无疑更加大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推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虽然不能把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全部归结到基督教这一场礼仪之争之中,但礼仪之争作为一个侧面,所反映出的问题远远多过它本身。
从萨义德在《东方学》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对于西方人来说,在明清之际,虽纵观文献资料对中国多有溢美之词,但实际上西方人的东方,是想象中的东方,是其根据自身的需要所构建的。“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 他们来到古老的中国大陆,出于对神奇东方的好奇之外,更多的是想要把基督教的真理传扬出来,这样的心态在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是在看待中国的时候采取了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虽然,对于西方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方始终处于“他者”的地位,作为乌托邦寄托着西方的想象。但如果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时时刻刻以自身为尺度去对其他文化做出价值判断,则必然会导致对对方的不理解。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经籍当中,一直强调,我们是“中央之国”,是最为强盛、繁荣和智慧的民族,自诩为自出东方之国度,而对四方之邻则有“西夷”“北戎”“南蛮”这样的蔑称。面对外来的使臣,也从不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其进行交际,这样自大的民族心理导致无法容忍其他民族对自身文化提出的任何質疑。
除此之外,正如周寧在《天朝遥远》中指出的,对于东方而言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异己世界的象征,是西方社会集体梦幻投射自身焦虑与渴望,紧张与不满的“他者”。它可能作为乌托邦化的“他者”被美化地构筑,也可能作为意识形态的“他者”被丑化地构筑,无所谓知识,更无所谓真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几乎是作为第一批来到东方的西方人,传教士的脑海里没有对中国的正确认识,但是他们却都存在着对中国的某种“期待视野”,这些期待来自种种游记、小说、书信,往往是不足取信的只言片语,但是,正如埃科指出的:我们周游、探索世界的同时,总是携带着不少“背景书籍”,它们并非是体力意义上的携带,而是说,我们周游世界之前,就有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它们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即使在十分奇特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知道我们将发现什么,因为先前读过的书以及告诉了我们。这些“背景书籍”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无视旅行者实际所见所闻,而将每件事物用它自己的语言加以介绍和解释。所以他们很难真正认识东方。而在其身后指挥其行动的罗马教廷,对中国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同样的,东方从不屑于与西方进行交流,对自身之外的世界茫然无措。以上,在我看来,是礼仪之争产生的最深刻的原因。
三、礼仪之争留下的思考
跨文化的交流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封闭自身的做法只能带来自身的不幸。但是如果在跨文化的交流当中不能采取合适的方式方法,则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一点,从清朝中西的礼仪之争当中已经非常显然了。
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克服的,首先就是万事从自己出发的心理,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的行为,就非常容易造成双方之间的误会和不理解。世界上有很多独立生长和发展的民族,这些民族也往往会创造出自身的绚烂文化,而文化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学习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则不会取得良好的交流结果。既不能正确认识自身,也无法正确认识他人。一味地自大自得,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在自我沉醉中被世界抛弃。
文化软实力是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际则是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得到深刻思考的课题。我国以“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一个新的起点,拉开了对外交流的新篇章。但是,我们知道,因为现代世界的秩序是由西方世界制定的,因此在进行文化的评价、研究、传播甚至交流的时候也多会采取西方的视角,采用西方的话语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永远都只是西方世界的“他者”,需要被归化和拯救的他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康熙帝在当时的做法,是具有合理性的,毕竟任何外来的文化若是想要在中国立足,则必然要进行适应性的改变,傲慢地要他国全盘接受基督教的想法,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不能因为之后的闭关锁国就对其做法全部加以否定。这是礼仪之争中一个好的方面。但同样,交流之中的冲突难以避免,而冲突发生之后如何应对,怎样解决则值得思考。如果为了避免冲突而放弃交流,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会产生怎样的苦果。
参考文献:
[1]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3]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4]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5]安希孟.清初"礼仪之争"中的文化沟通[A].基督教文化学刊 (第7辑) [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6]纪建勋.“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中西学统的关系[J].世界历史,2019(01):112-121+159.
[7]李秋零.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学再反思——兼与安希孟先生商榷[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04):113-118.
[8]任婷婷.天主教改革与“利玛窦规矩”的兴衰[J].世界历史,2017(01):42-54+157-158.
[9]幸念.中西礼仪之争对当今社会跨文化交流的启示[J].群文天地,2011(2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