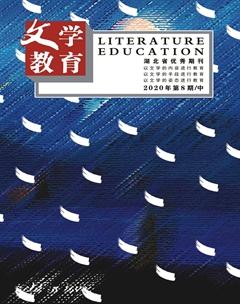我在童年养过的虫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虽然没有布娃娃和小汽车的陪伴,但却因为拥有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萌宠而分外有趣。细数我养的宠物,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
对于虫,估计大多数人并没有好印象,有人甚至会感到有些恶心。然而,山里面有趣的虫可多啦。有神奇可爱的蚕,有憨态可掬的芝麻虫,有身形矫健的蛐蛐儿,有牙尖爪利的天牛,有翠绿锃亮的丁丁虫,有头大颈细的土狗儿,有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说起来这么多,但我真正养过的也只有蚕、芝麻虫和蛐蛐儿了。
蚕籽是哥哥从中心小学弄回来的,密密麻麻地粘在一张皱巴巴卫生纸上,棕黄色,小小的一粒粒,乍看起来和油菜籽差不多。哥哥告诉我,只要细心呵护,不出几天就会孵化出蚕宝宝来。
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包在棉花里面,塞在胳肢窝下面孵小鸡般地用体温给蚕籽取暖,每隔一小段时间,便会好奇地拿出来察看一番。然而,四五天过去了,蚕籽却纹丝不动,只是颜色一天比一天加深。
某日,又忍不住打开了棉花包,一看之下不由大吃一惊,出现在棉花上的居然是几条黑黑瘦瘦的小虫子!我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是说蚕宝宝吗?怎么是如此丑陋的小小毛毛虫?一点儿也不像我心目中的“宝宝”那么呆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蚕的幼虫。之后,养蚕的过程中,我慢慢见证了蚕的蜕皮,变胖,变白,吐丝,结茧。
当时奶奶尚且健在,由她向幼小的我传授养蚕经验。奶奶说,蚕是极娇嫩极神圣而又极有灵性的小动物,喂养的过程中一定要细心谨慎,切忌粗心大意。譬如,忌敲擊门窗,忌在蚕宝宝附近舂捣,养蚕的桑叶忌讳用手采摘,必须用铁剪刀剪。并且,忌剪摘有雾湿和露珠的桑叶。此外,奶奶还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养蚕过程中语言禁忌。比如,蚕不能叫“蚕”,要叫“蚕宝宝”或“蚕姑娘”;蚕爬不能说“爬”,要说“行”;喂蚕不能说“喂”,要说“撒叶子”;蚕长了不能说“长”,要说“高”;蚕不能数数,否则,会减少等等。
关于这些禁忌的由来,我曾刨根问底地追问过奶奶,她却答不上来,只是说老祖宗们世代都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能冒犯。正因为如此,蚕在我幼小的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神秘莫测,神圣不可侵犯。养蚕的经历也成了一段经久不忘的特殊经历。
我们那个时代,山里的孩子不上幼儿园,一直玩到七八岁才正式上学。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每天总有大把的时间可供玩耍。玩耍的项目多种多样,除了上山放牛和下河捉蟹外,有时我也会随父母一起去田间地头捕捉虫子。所有虫子中,我最爱捉的要数芝麻虫、蛐蛐儿和丁丁虫了。
芝麻虫别名豆虫,中原人称之为芝麻虫,我们当地也称大青虫。它们最爱生长在芝麻叶、黄豆叶和红薯叶上面。据说,此虫捉而食之,味极鲜美,营养尤为独特,为苏北人所珍爱,被奉为人间极品,美其名曰“豆丹”。
然而,我小时候捉芝麻虫并不是为饱口腹之欲。就算是现在,我也没有勇气敢尝试那肉乎乎的小东西。童年时期之所以喜欢它,只因为以孩子的眼光看,觉得它形态优美,憨态可掬,属不可多得的玩赏之物。
芝麻虫多是嫩绿色的,也有部分是棕灰色的,但棕灰色的远不及嫩绿色的漂亮。我喜欢养嫩绿带着黑点花纹的那种,有着圆圆的貌似眼睛的装饰,翘着短短的尾巴,被我亲昵地称之为“猪娃儿”。不错,同母亲在猪栏里养猪一样,这些芝麻虫就是我养在盒子里的猪娃儿。
鼎盛时期,我最多同时养过十多头“猪娃儿”。每日不辞辛劳地在田间奔走采撷嫩叶,然后心满意足地看它们在“猪圈”里大快朵颐。它们倒也争气,欢快地蚕食着我投入的叶子,个头眼见着一天天壮大起来。
这样养了一段时间后被母亲发现了。她又吃惊又好笑,从此视我为怪物。时间长了,终于见惯不怪,也就由着我折腾。我愈发养得起劲儿,悉心饲养的同时,只盼着能早点“杀年猪”。
可是,我并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某天不小心打翻了喂养的盒子,十几头“猪娃儿”通通跌落到地上。它们在地上挣扎着,翻滚着,试图做最后的拼搏。只怪它们太笨拙了,还没来得及扭动肥胖的身子,便引得附近鸡群一哄而上。顷刻之间,我的“猪娃儿”全军覆没,统统葬身于鸡腹之中。深受打击后,我再也没有养过芝麻虫。
蛐蛐儿往往从夏初时节开始出现,常栖息于地表上、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最爱夜出活动,是典型的夜行者。因其常在灶膛附近出入,我们当地称之为“灶蚂子”,也有人称之为“灶鸡子”。
自小在田间爬摸滚打,我深谙蛐蛐儿的习性,故总是知道该在何处觅得它们。夏初时节的白菜地便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彼时,白菜只有两寸来高,叶嫩,味美,深受蛐蛐儿喜爱。它们将娇小玲珑的身子隐藏在白菜的嫩叶下面,敞开肚皮直吃得肚儿滚圆。
我静静地蹲在菜畦上,聚精会神地盯着某株小白菜叶子边缘晃动的那对细细的触角,忍不住偷偷咧嘴笑了。过一会儿,那棕褐色的身子终于探出一点,然后又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了,似乎正和我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我轻手轻脚地挪过去,伸出右手猛地一捂,一下子就抓住了那个谨小慎微的家伙。它在我手中拼命挣扎着,似乎不甘心束手就擒。我得意地冷笑一声,将它投入到小罐里,然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蛐蛐儿生性好斗,雄性尤其如此,二者相遇必分个胜负才肯罢休。它们一经被我投入到小罐这个狭小的空间,便相互撕咬起来,一点儿也不友好。见怪了它们的战事,我早已不以为奇,索性让它们过起大杂居的生活——一个小罐同时喂养十来只。自然,小罐之中免不了经常“战火纷飞”。
蛐蛐除了是好斗的武士,还是歌喉优美的音乐家。夏秋的夜晚,每当四野蛙声和其他虫鸣暂时沉寂时,总能听到一阵阵旋律优美柔和的歌声。那歌声在夜晚的草丛中回旋,在夜空中飘荡。清冷,清疏,清静,清凉,与夜色苍茫中的静谧气氛再适合不过了。童年的我,无数个夜晚静静地躺在床上,侧耳倾听那一首首美妙的乐曲,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幻想。
有晚停电,母亲点着蜡烛做饭,父亲打下手,我在灶膛前帮忙添柴。蛐蛐罐被我悄悄放在灶门下面。“唧唧!”一只蛐蛐儿不甘寂寞地忽然唱起来。“唧唧!”“唧唧!”“唧唧!”一罐蛐蛐儿争先恐后地迎合。我家厨房顿时变成了蛐蛐儿演唱厅。
母亲吓一大跳。
“屋里哪来的这么多灶蚂子?”她吃惊地问。
“估计要变天了吧。”父亲东张西望,不明所以。
我偷偷笑,忍不住捧起蛐蛐儿罐在灶台前的蜡烛下查看,不料一失手将罐子打翻了。十多只蛐蛐儿好不容易获得了自由,立即不顾一切地四处逃窜。它们有的跳进了锅里,有的跑到了灶前,有的蹦进了我们的晚餐盘子里……总之,场面十分混乱,母亲吓得花容失色。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父母弄明了原委,也忍不住笑得直捂肚子。好好的一场烛光晚餐,被蛐蛐儿的逃逸事件硬生生地给搅合了。不知那晚逃生成功的蛐蛐儿,是否会记得当时的惊心动魄。
炎炎夏日,我也会从花栎树上捉来丁丁虫玩,丁丁虫实际上是铜绿金龟子,椭圆形,体壳坚硬,表面光滑,背部铜绿色,多有金属光泽。它们嘴巴锋利,有的嘴前还天生一个小铲子,以啮食植物根和块茎为主,因此不便喂养。
捉到丁丁虫后,我喜欢用细线拴在它的后腿上,系牢。这样,只要捏住细线一端,那丁丁虫便会“嗡”得一下飞了出去。由于腿被线绳绑住,它只能不停地绕着转圈,不停转,不停转,直到转得晕头转向才肯找个地方停下来。等体力稍稍恢复,它们又会“嗡”得一下飞出去,然后继续转圈,像个百折不挠的战士。
由于不了解丁丁虫的食性,因此捉住它们把玩一阵后,往往又会放走它们。它们也不客气,等我手一松,便“嗡”得一声,头也不回的飞走了,顺着遥远的童年路,飞向不可知的未来。
还有那星星点点在夜色朦胧的田野上闪烁的萤火虫,那穿着盔甲晃着长长触角令我又爱又怕的天牛,那外形像狗儿擅长打洞的土狗,那被掀翻身子好久爬不起来只能倒退着行走的土鳖虫,那身躯纤细体态轻盈的蜻蜓,那五彩缤纷妖娆美丽的蝴蝶……它们曾引起我很多童年的好奇、欢乐和陶醉。
啊,这神奇的大自然,感谢你无私的赋予。啊,这可爱的昆虫精灵们,感谢你们陪我度过了整个童年。
伊梦,原名王丽,八零后文艺女青年,现居湖北保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