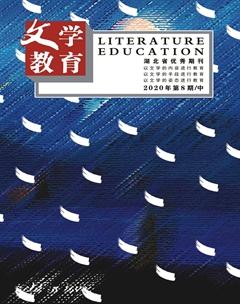晓苏老师的龙洞

一
说真的,对于油菜坡,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还小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九〇年左右,我从大人们口中知道,我们店垭有个叫油菜坡的地方,出了个作家叫晓苏。那时候,正好是油菜花一田一田盛放的时节。我站在田埂上,面朝着暖黄得几乎要流出蜜糖的无边花田,满耳都是成群蜜蜂在丰饶的花海里嗡嗡振翅的声音,想象着一个漫山遍野都飘荡着浓郁花香的山坡上,一个叫晓苏的大作家也这样站在故乡的花田边沉醉,就忽然感觉到一种亲切的光荣与幸福。
在那之前,我仅知道语文课本最下角注释中的几个作家名字,一直觉得作家是多么神圣又多么遥不可及的人物。仿佛天边的明月,他们挂着清冷而圣洁的光芒,只能供地上的人们仰望和赏叹。
就此,油菜坡作为一个具有地理和文学意义上的名词,始终和晓苏这个名字天衣无缝地黏合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他的小说知道了油菜坡、龙洞、老垭镇,并很自然地知道了店垭、保康、襄阳,乃至湖北。作为他的家乡人,我们自然沾光不少,与有荣焉。
可是,说来惭愧。我竟始终弄不清楚油菜坡的具体位置。它就那么风雨不动安如山地横亘在我模糊的想象与猜测中,与我所读到的晓苏老师笔下的油菜坡纵横交错。就像莫言的高密乡、苏童的香椿树街、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晓苏老师笔下的油菜坡是一面镜子,真实地折射出人性的复杂,有一种迷人而残酷的质地。很多时候,我甚至并不刻意去打探它的方向。因为,我始终觉得留这么念想就够了,知道它一定非得站在那里么?留点儿虚幻的想象和憧憬也是不错的。
二
让我改变这一固有想法的,源于晓苏老师屋旁的龙洞。
在我们店垭,龙洞这个名字并不稀奇。很多泉眼,都被老人们带着敬畏与自豪之心冠以龙洞之名。在我印象中,我所知道的叫龙洞的地方都有四五处之多。有几处,我还亲自去探访过。那些地方,往往藏匿在密林深处。啾啾鸟鸣从绿叶深处四下飞溅,藤蔓胡乱纠缠在一起,从外部环境看毫无吸引力。但是,一缕蜿蜒流淌出来的涓涓细流则不动声色地向人昭示:去看看吧,这个龙洞神秘着呢!
是的,只要朝前走,永遠是一股清凉爽洁的气息扑面而来,一个幽深黑暗的石穴像一张神秘的嘴巴,静静地流泻一股凉气扑面的清泉。那水,永远是清冽甘甜的。因为人迹罕至,寻访不易,这些龙洞确实有种拒人于千里的神秘莫测。于是,我一直深信老人们的话:石穴深处,有一条巨龙静静地盘桓千年,只要水不干涸,一直不知疲倦地奔流,说明这个地方就是有灵气的。龙洞,龙洞,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拜访晓苏老师之前的一晚,翻看他的一本作品集,碰巧就翻到了他的《龙洞记》。于是,我跟着他文字的指引,先在书中神游了一番。
真是个有故事的龙洞啊!这个龙洞仿佛是一个老家的图腾,它让老家变得具体可感,热气腾腾。只要龙洞在,关于老家的一切记忆都是鲜活的。一看到它,许多人、许多往事、许多过去的岁月都像电影回放,一幕幕闪现在眼前。晓苏老师动情地写道:“每当想起老家来,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龙洞。而且,龙洞往往是我回忆的重点,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有时候简直超过了那栋房子。”
其实,离开故乡的游子,哪一个心里没有这样一个秘密花园般珍贵的所在呢?只是有时候,我们刻意选择了遗忘。可是,一旦彻底忘却了,那一缕如轻烟、如浓雾似的乡愁,该如何安放,该让它们在哪里飘荡呢?你骗得了别人,可是午夜梦回时,怎么骗自己相信已跟老家没有联系呢?这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情分,是可以随便而轻易地忽略掉的么?
这,真是个问题。
三
上了林间水泥路,我就忽然有了种回老家的新鲜与欢腾。
越来越灼热的阳光透过头顶密匝匝的绿叶,在平坦又忽升忽降的路面上,投下了斑驳不规则的、半透明的树影。于是,阳光的热力被稀释殆尽,只剩下莹莹绕绕的清凉与绿意呼啦啦涌上来,将我们的车子包裹。我顿觉全身每一个之前冒汗的毛孔,此刻都在畅快自由地呼吸。其实,这种感觉在我每次春夏季回老家神龙时也有,凉快之外,更多的是归乡带给游子“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清净与适意。
水泥路走完,再走一段凹凸不平的机耕路,终于到了晓苏老师的老家。
和晓苏老师描述的对上号了——
龙洞离房子十步左右,后面是竹园。泉水是从一块巨石的裂缝里流出来的。巨石有两人多高,长度少说也有七八米,形状极像一条卧龙。泉水是从龙嘴巴流出来的,却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
虽然与晓苏老师笔下的介绍别无二致。但是,却与我印象中家乡那些隐身于山野草莽中的龙洞不一样。
这里的地势较高,站在修缮一新、挂着晓苏老师父亲“苏天铨老家”的匾额下放眼远眺,远山重叠的蜿蜒曲线在远方肆意地延展,色泽由深蓝、浅蓝、深灰、淡灰过渡渐变,直至最终与遥不可及的天色汇合融成没有边界的一片。
这片苍莽绵延的群山,曾经多少次黏住一个少年痴望远方的目光,又有多少次在异乡游子的梦里温柔召唤呢?我没有问,但透过晓苏老师一一指点时,眼中灼灼的神采,我想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比起多年前遍插铁管和皮管的遭遇,现在的龙洞显然经过了彻底精心的修复,仅供旁边这两户人家的生活用水。用各色鹅卵石围砌的弧形水池,很像一个巨大的逗号,似乎暗示着晓苏老师写作的灵感永远汩汩流淌。泉水清澈,下面的细沙和碎石历历可见,旁边的藤蔓低垂,阳光顺势将它们斑驳的影子投在水面上,就像是许多鱼儿聚在一起休憩。
龙洞静水流深的姿态,和许多年前一样吧?它是否知道,楼上书柜里站着的一排排晓苏老师历年来的作品集,都沾着龙洞水的灵气呢?
我很想弯腰鞠一捧泉水洗一把脸,再尝尝它甘美清冽的味道,借此沾一点灵气。犹豫再三,终是没有伸出手去,我怕玷污了这股龙洞水的纯净与圣洁。
四
“这些石头,每一块都粘过我的泪水。”
晓苏老师指着龙洞旁边形状各异的石头,平静地对我们说,没有丝毫开玩笑的口气。
我们当然要好奇地追问原因。
原来,身为大哥,也还是个孩子的他,一度要承担给四个弟弟洗澡的重任。这个任务,是母亲天黑前下达的指令。母命不可违,他是老大,父亲长年在外工作,帮母亲分担家庭任务,是他分内的事情。
天黑前,从龙洞一桶一桶地把水提回去,架火烧热。四个大木盆,一字摆开。倒好水,试好水温,帮他们一个个脱好衣服跳进温热的洗澡水里去。一下水,水花四溅,各种麻烦也纷纷四下溅开:这个喝洗澡水,那个水里撒尿,还有两个泼完水就打成一团。拉开这个,那个又捣乱;教训玩这个,另一个又笑嘻嘻捣蛋。一场澡洗完,当大哥的也渾身湿透。一半是水,一半是汗。受了累,母亲回来的那顿打照样逃不掉。弟弟们会小心保留挨打的“罪证”:揪红的耳朵啦、出血的鼻孔啦、背上的巴掌印子啦……
一大早放完牛回来,已经快上课了。来不及吃早饭,只好举着母亲递过来的锅巴饭团,赤着脚就沿着门前小路往下跑,边跑边吃,边抹眼泪。是委屈,辛酸,还是害怕迟到?说不清楚。
晓苏老师笑着讲述这些,我们边笑边发出感叹:唉,当老大都不容易啊。其实,在那个荒寒贫瘠的年代,当老大则意味着更多的付出,甚至牺牲。好在那个倔强自强的少年咬着牙挺了过来,用大哥的担当与责任,给兄弟们做了值得他们一生仰望的范本。
每逢父亲回家,每个人都会心一惊,暗自历数自己前段时间犯下的过错,再去堂屋接受父亲树条唰唰下的责罚,在心里警醒自己不可再犯。
管教严格的父亲、温良勤俭的母亲,以及他们的相濡以沫互敬互爱,都在言传身教中,给了苏氏兄弟最好的教育。
认识苏氏五兄弟的人,无不在介绍时露出钦羡之意。但了解到这些他们成长背后的故事后,也都会由衷钦佩他们身后这两位平凡而又了不起的老人。
家和万事兴——这是中国人最朴素的治家经验。这饱含着简单智慧的经验一旦由一个家庭推广到一个家族,其影响和辐射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
苏家的文化广场上,每年都会在油菜花竞相绽放的时节准时开一场规模盛大的“清明会”。这一天,不仅仅是族人聚会,家长里短,更是尊老爱幼、家道家风传承的重要节点。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年一度清明会的召开,晓苏老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苗,给了苏家人无限的希望与力量。他用自己的奋斗史和暖人心窝的话语让他们深信:只要有担当、肯吃苦、愿奋斗,有什么坎儿会迈不过去呢?在离苏家老屋不远的文化广场上,我看过他和族人们的照片。那一张张质朴亲切的笑脸背后,是对生活的微笑与自信,是对山河岁月的知足与感恩。
离开苏家老屋的时候,晓苏老师的堂弟苏顺敏先生,这位世纪初南下创业成功、被晓苏老师誉为“大气早成”的商人告诉我:他们即将去赴一场特殊的答谢宴。问及答谢什么,他说,多年来他们自发帮助苏氏家族家境稍稍落后、但又自强不息的人,给予他精神及物质上的帮助。这家人目前已全面脱贫,此次答谢宴即是为感谢晓苏老师这些发起人而设的。
回望油菜坡上这栋新屋,想起屋旁那面农耕文化墙,那些挂满农具的墙上,满是曾经沸腾的朴素日子,不该忘,也不能忘。展出即是一种对岁月、对乡愁的铭记。
龙洞旁边的石头上,是晓苏老师题的字:留住乡愁留住根。在五月初的阳光下,这七个字很明亮、很耀眼。
严榕,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与鸟为邻》等。现居湖北保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