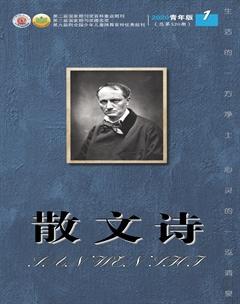问题会一直存在
玉珍

我有个缺点,晚上写作。白天不是做事的好时辰。白天的脑袋旁围绕着巨大的苍蝇,来,离开,来,离开。啊夜晚,夜晚太甜美了,我的屋子极其的寂静,我们的小院子极其的寂静,我们的野猫在树枝下走着,夜晚太甜了,我大大地吃了一口黑暗。
艺术诞生于吃饱了撑的,诞生于误会,诞生于游手好闲,诞生于疯疯癫癫,誕生于异于常人,诞生于普普通通。艺术诞生于出生、死亡、沉默、咒骂,艺术在梦游,梦游时不要吵他。
醒来十秒内去洗个冷水脸,这是对付赖床的好办法,我从小洗冷水脸,喝冷水、井水,厌恶凉白开。在学校,下雪天我起来走出宿舍,风很冷硬,厚冰冻住了洗脸水,揭开它,我将冰拿在手上看着,很美,晶莹剔透,极其地网,有一回我咬了一口,它缺了一块的样子也好看,这一切的问题是冷,冰块们属于美神。
爱造了什么孽要拿来洗礼人的污浊?没办法,它是爱啊。
我怀疑一切,不仅仅怀疑我自己,没有什么能使我十足满意,这一刻不同于下一刻,下一刻不同于明天,每当我写字就是在验证我的怀疑,当我解答时创造了新的问题,我还没有自己的道路。
2002年,也许是2004年,我只记得是傍晚,我放学回来见到了我的牛,在河堤边,美丽的花朵再没盛开过,我的牛走了,走向了死神与案板。
有时你深夜独坐,睡不着,就那么大睁着眼睛,也不想什么,但有一种命运感突然降临。尤其是周遭极其寂静的时候,极其的寂静,极其的黑暗,极其——你感到有什么在走向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却使你拥抱了自己。
有时候我关上我的笔记本电脑走出门去,旷野,荒原,山,丛林,大街,或在窗户边屋顶上坐着,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我觉得一切尽在手中,自足高兴得难以自禁,这感觉在我完成了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事情时也有,但成就感几秒就结束了。赞美是徒劳的,在我这样的人这里,有一种赞美是代价和风险,赞美之后的感觉是光秃秃的。就像现在,我突然又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愚蠢、可笑、浅陋无知、可怜至极。
太阳照着我黝黑的大脸庞,像爸爸那样黝黑方正的大脸盘子,这使我看上去像个男孩,我像个男孩走在路上,走得很快,与乡邻打着招呼,太阳金灿灿但不能给我添光彩,太阳使我的黝黑更明显了,我感到很快乐,那都是内心的东西。
早上我曾想到思索使人年轻,而晚上却发现思索使人衰老。活着当然有累的时候,但又不能去死。
爱是排他的,只有在排他那一刻爱最像爱,爱的伟大在于它的强烈纯度和对爱本身的极致追求,爱甚至连和与它自身无关的爱的形式都排斥。否则何以称之为爱呢,如果爱和别的东西一样,爱这个词语何必存在?当爱的复杂时刻在世俗和内心中变化,这使爱这个单纯的字有着世间最复杂的形态。具有它们的无情与热烈,艺术性,自由性,极端,软弱。博大,强悍。
陌生的自由给我陌生的语言,危险的自由给我爱。
有一段时间我的人生什么也没有,只有写作,只有活着。没有交谈,没有外出,没有应酬,没有闲暇,没有爱情,没有废话,没有烟酒,没有电话,看上去一个人可以坐上一整天、一整年、十年、二十年,我很闲,但我跟所有人都说我很忙,我谁也不见,好像没有任何人我都能很好地活下去,太喜欢那感觉了,甘甜的寂静,自由的寂静,我就那样坐在屋子里,有时看看书,有时自己写。
我躺下,脱下我自己,我感到硬硬的壳着了地,轻了很多,我脱下自己,脱下躯体,穿上灵魂,在一种踏实的贴着地面的轻盈中躺下,闭眼,一种酸疼和紧张消失了,他们称这为休息。
我对不劳而获的东西充满怀疑和不信任,也许从来都是靠着没法手到擒来的重复付出,靠着并不轻松的习惯和踏实的生存,让人在沉甸甸的生活中感到毫不轻浮和接地气的实在,那是谁也动摇不了的生命力。
想写点什么,坐下来待了几分钟,停住了。有时是走来走去,什么也不想,一直走来走去,像在充电。写是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对我来说平常如喝水,但能不能进入满意的状态完全无法确定,让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暂时顾不上。
山中的辛夷花,风中雨中的辛夷花,雾中显露出一小点红色的辛夷花,在疾驰的高速公路,仿佛几片碎掉的粉红的梦幻。
语言并不能完全使我们理解,我们将选择合适的交谈者,出于对语言的尊重,对友谊的理解和对生命的关爱。我们将选择合适的交谈者,否则宁愿不开口。
这是属于后来者的世界,不完全属于死去的人,不完全属于活着的人,或不属于我们任何人。很多事物能够证明你的能耐,但绝不是你的自吹自大。所有得到的一切最终都会消失,任何人都会老,我们在舞台上出现,表达,沉默或光芒四射,然后站住,告别,再见,消失。
造物选择了单纯的人,让他们去创造复杂的作品,让他们极其专注地极致地不被旁事干扰地去思考一些事情,将那些庞大又尖锐的东西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