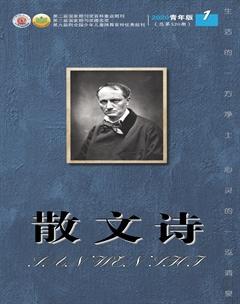镜湖故事
张玉泉
镜湖故事
用盐照亮我的面孔。照亮黑夜。
用咸涩堆积车轨,堆积雪山,堆积风的翅膀。
镜湖的游鱼,镜湖的夜风。镜湖的少女站在自己的身体上,站在柔软的目光上,站在天山的怀抱中,站在我的视觉里。
发酵的,冰冷的,一场又一场错过的溶解,只是结晶的失落。
谁知道苍鹰与群山的漠视,一颗盐灼痛另一颗盐。在体内开花,在血液里开花。
丰收的盐场
一切咸涩都在镜湖的梦中,风吹出了毕生的疼痛。丰收的盐场,青芒点亮的波纹,雕刻粗糙的时光。
山河的味觉,在水中分娩,在迷失中,用左脚寻找右脚。多少鱼儿的眼泪,埋葬多情的记忆,冷峻的沸腾,煮着一轮落日。
有人乘着小火车,目光腌制的惊心一瞥,到处都是花开的盐田。
盐的花朵
盐在湖水下面开花,举起一朵朵浓绿的浪,漩涡,一行行平静的双曲线,构成咸涩的起伏和雄浑。
我抚慰着一粒盐的忧伤。味觉早已对苦痛麻木。一弯月光,母性主义的化石,高海拔火焰,与我一起站在镜子的反面。
摇晃着一张中年的脸,我不再和体内的盐较劲,盐田里的阳光,正在孕育一片苦涩的丰收。
我攥紧了一把盐粒,轻轻握在手心,感受青海的体温。
在盐场
世间的咸涩全部堆积在此处,一片雪一样的山河,在寒风中飘飞着粗糙的西北之吻。
我端详他们的影子,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往事,都已经被腌渍成历史的标本,可以朝向我们的眼角,还保留着昨夜的热泪。
伤口上再也没有往日的疼痛,眼前只有一片苍茫。这是一片安静的神坛,我们的脚印即将带着人生的颠簸与艰辛,留在白色的浮雕。
少女正在盐湖上留影,她的目光如此单纯,仿佛盐粒正在养育着不老的容颜。
而我已经老去,我正在湖面上滑行,在与天空的交汇处,一片孤云升起了沉重的祈祷。
我是我的那颗不安的盐粒,让生命变得如此的酸涩,映射出阳光的棱角。
青海湖的抵达
不需要谈到自己,不需要谈到梦幻。一切都找到了柔软的答案。因为水和云、云和天、天和地,都在青海湖相约。我把灵魂献给已经平静的内心之湖,像是一枚不需要离开的落叶,像是一颗守候在湖边的石头,被你打了水漂。
又被你的云挟裹而去,带着雷雨的回响。
瞬时冷到内心,瞬时一亩油菜的金黄冷落无比,瞬时一匹马的脚步变得更加迟缓。牦牛披红挂绿,不问来者,把姿态降到胸口以下。
可以骑在马上,目光挂在一排大雁的结尾,让一圈涟漪渐行渐远,消失在颠簸的长途。
高原湖沙所见
面对一场黄沙,你想说出今生的夙愿、遗憾和悔恨。
面对死亡的高度,你愿意供述这一切已经失去的际遇和姻缘。你想在一场雨水里复原湖水的辽阔,在鱼的浮游里呼唤疼痛的鳔,呼唤一亩油菜的金黄。你想在雪花的播放机上找到岁月的年轮和爱情的坚贞。
只有一亩沙地上种满了月色和年轮。失守的星光已经落满了佛龛的皱纹。
走不出的是内心的一场雨的高度,正中你的命门。她已经搅乱了你的记忆和今生。
我要站在一场不灭的花事里,参照圆觉经写下偈句。写下一场淋漓、一场拥抱,浪花与鸥鹭,湖面与云雨,经幡与微风,我只是湖面、沙漠,我只是命运里微小的疼痛,与你的光线一起升腾,哦,这一个永远无法分清你我的湖,永远无法分清爱与恨的大漠,只能用执著的跋涉丈量温情与慈悯的辽阔、宽广,我只能相望一座无法读懂的雁阵、一场失约的日出,一切将在命运的背后发生交集,悲欢已经与苍凉发生交易。
在湖邊
这面湖是认真的,它打开一幅柔软的封面。
我在高原上端着一湖水,有神灵在湖边梳妆。
还有秋意,落下黄昏的铁锈。一群忘记危险的游鱼,在河流拐弯的地方亮出自己的雪白。
我是一颗善良的石头,安静地守护着高原的孤独。
白鹭的翅膀,像是女神的纱巾,飘落在湖的额头。
我看见桥梁晃动了一下,一个行人打了个趔趄。深秋的寒意,挪动北斗的勺柄。
黑马河的黄昏
黑马河的黄昏,凝固在浪花的苍白里。
黑马河的黄昏,驮在鹭鸟的翅膀上。
愈来愈浓的一杯苦菊,在接近神灵的高原饮下辽阔。我坐在一棵草的怀抱里,一枚褪色的刺,闪烁着青蛙的歌谱。
没有人在湖边的堤上静念黑马河的汹涌;没有人像河水一样凝重与坦荡,流向天际。青海湖,再也不需要跋涉在命运的高原,再也不需要流离失所。
波澜不惊的鹰,将苍生抬高到另外的高度,带着命运的轮回,在目光里沉浮,还会有更多的生灵打开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