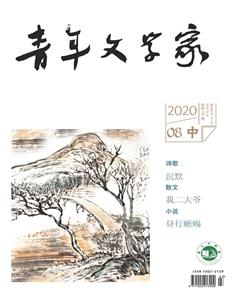苏轼佛印故事流传研究
基金项目:川北医学院校级科研发展计划项目《蘇轼佛印故事流传研究》(CBY17-B-YB13)。
摘 要:苏轼与佛印的故事自宋代产生以来就流传甚广,二人一士一僧的形象受到文学创作者们极度的偏爱。以苏轼佛印为人物题材的小说、戏曲、散文、民间故事等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也经久不衰,主要依赖于民间、文人、僧人群体的继承与创作。
关键词:苏佛故事;民间文学;禅宗典籍;文人创作
作者简介:谭婷婷(1988-),女,汉族,四川南充人,川北医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3-0-03
苏轼与佛印是宋代文人、僧人交游故事的典范。从宋至今,苏轼佛印故事(以下简称“苏佛”)嬗变过程漫长。故事由最初的史实逐渐步入虚构的如小说、戏曲,再到内容繁杂且数量可观的民间故事,二人也从历史人物逐渐演变为今天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苏佛故事的流传问题有着文学自身的流变因素,更体现着我国深厚的文化现象。
一、民间崇拜及民间文学对故事的传播
苏佛故事能口耳相传式地在民间传播,很大程度依赖民众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崇拜。加上自宋代起通俗文学的快速发展,使得史实中苏佛二人的交游之事为民间文学所吸纳,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故事的传播。
(一)民间崇拜
苏佛故事始于北宋,由于宋代“尚文抑武”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文人的地位被提高,也使得民间对文人的崇拜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这从古代文人流传下来的故事多集中在宋可以看出,如王安石、黄庭坚、秦观、柳永等。在浩如烟海的文人故事中,苏轼是被传唱最广、也是流传数量最多的一位,足可见世人对他的尊崇。佛印是僧人,属禅宗云门,而他生活的几十年恰好是云门宗最为繁荣的时期。佛印曾一度同时担任几所寺庙的主持,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言佛印下山“重荷者百夫,拥其舆者十许夫”,在当时有不小的名气,颇受僧俗大众的敬仰。又因“自宋民间的多元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非宗教性的祠庙中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山川、土地龙王的祠庙,可以说是自然崇拜的流变,第二类是纪念性祠庙,是历史上的皇王、功臣、名将、孝子烈女和乡贤等祠庙。”[1]在宋代民间多元崇拜的文化背景下直接导致了纪念性祠庙的杂乱现象。《宋辑会要》中也载宋时祠庙建筑之风突起,以至于不得不动用政府力量对一些供奉石通、妲己的“淫祠”进行强制销毁。“中国民间信仰对于人物的崇拜,除了对神化了的人物及仙化了的人物崇拜外,最为直接的就是对于圣化了的人物的供奉与崇拜。”[2]222当然,一些具纪念性的人文景观也是民间对人物崇拜的具体表现。
宋时景德镇修建的佛印湖,就是为纪念苏佛曾在此地论诗特以佛印之名所取。《镇江府志》载“金山旧有东坡佛印二像,李伯时笔,苏子由赞,岁久损裂,至顺壬申,广道都元帅本齐王都中请观敬钦命工装,仍付常住。”[3]891《江西通志》记载,明代复修宝积寺时,建起一座“三贤堂”供奉苏轼佛印、黄庭坚的塑像。浙江临安县的玲珑山大雄殿设有苏轼、佛印、黄庭坚像。江西永修,虚云老和尚在重新恢复真如禅寺时发现了由苏轼亲题“石床”二字的巨石,掘出此石后建“佛印桥”,还留颂一首《佛印桥谈心石》以作纪念。这些带着民间情感的人文景观,皆出于民间对苏佛二人的崇拜,也成为苏佛故事流传至今的一大媒介。
(二)民间文学
苏佛故事的本事主要源于宋人作品《问答录》,也称《东坡居士佛印师问答录》,共一卷,古本小说集成有著录,旧题苏轼撰。《四库提要》评:“所记皆与僧了元往复之语,诙谐谑浪,极为猥亵。又载佛印环叠字诗,及东坡长亭诗。词意鄙陋,亦出委巷小人之所为。伪书中之至劣者也”[4]3710。此书应为宋民间说书艺人的底本,全书共计27则故事,体制短小,多叙苏佛互嘲之事,又杂以行令商迷,情节性不强,后世创作多由此演变而来。《问答录》中苏佛对答之语皆是民间俗语口语,如《纳佛印令》一则中,苏轼戏骂佛印“不秃不毒,不毒不秃”,佛印嘲东坡多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稍后的《山中一夕话》中录苏轼、佛印及黄庭坚抢肉所对字令:“二八一十六,且吃一块肉;二九一十八,两片一齐夹;贫僧不识数,且吃一碟醋。”这些都是出自民间口语,语言俏皮幽默,符合民间审美。
在流传下来的苏佛故事中,民间故事占了很大比例,主要存于各地方县志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这些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是历经长时间集体创作的结晶,具有多种多样的题材、无比丰富的内容,不仅为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素材,还促使了苏佛故事在民间得以发展,扩大了传播范围。
二、文人对苏轼佛印故事的创作延续
任何文学作品能得以保存、流传都离不开文人的参与,苏佛故事亦是如此。由最初苏佛二人的真实故事经文人采集编入笔记、诗话,再到对小说、戏文的整理编撰,最终促成苏佛故事的繁荣。
(一)对故事的改编
苏佛故事经宋至清,每一朝代的故事主题及情节都会发生不同变化。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人在创作时会不断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念以及个人的审美对其进行改编和创新。在流传的苏佛故事中,“转世相逢”的故事母题,是极为重要的叙事模式。所谓“转世相逢”,即叙苏佛二人前世相识(多数二人皆为僧众,且为密友),转世后两人再次相见。宋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是苏佛故事中最早的“转世相逢”作品。故事叙五戒和尚与明悟和尚同在一所寺庙中修行,师兄弟关系甚好。寺中被僧人拾得的女婴红莲长大成人,五戒见其美色萌动凡心,淫污了红莲。此事被明悟察觉,五戒羞愧坐化转世投胎为苏轼,明悟亦相随坐化,投胎为谢端卿,后出家为佛印。佛印出家后,在潜移默化中使苏轼由不信佛法转而敬佛礼僧,最终得悟。
这种叙事模式一直影响着后世苏佛故事的创作,冯梦龙的《喻世明言·明悟禅师赶五戒》,《绣谷春容》中收录《东坡佛印二世相会》,陈汝元的戏曲作品《红莲债》《金莲记》等都是以此母题进行改编创作。
再有苏轼佛印游赤壁故事,同样以苏轼被贬黄州的史实为背景,元代杂剧《苏子瞻醉写赤壁赋》的整个基调都充满失意落魄,正如戏曲中唱词:“春事狼藉,桃李东风蝶梦回,离愁索系,关山夜月杜鹃啼。催促江水自奔驰,翰林风月教谁替。谩伤悲,滴不尽多少哭雄泪。” [5]799到了明代,许潮的戏曲作品《苏子瞻泛月游赤壁》就作了很大改动,单从名字就能窥视故事的主旨。戏中已看不到对政治的不满,多的是对人事的感慨,哲理性增强。像开头[菊花新引]:“江湖廊庙总关情,此夜蟾光处处明。载酒泛深清,潇洒一番情兴。” [6]97唱词中多了洒脱,超然。
(二)对故事的引用及评述
明清小说戏曲作品中,对苏佛故事进行引用的甚多,《水浒传》第29回武松与施恩前往快活林,经过一家酒店,那店中的赞词:“壁上描刘伶贪饮,窗前画李白传杯,渊明归去,王弘送酒到东篱,佛印山居,苏轼逃禅来北阁。”[7]388苏东坡写过《酒经》《浊醪有妙理赋》等以酒为题的名篇,是个品酒的行家,再加上佛印,寥寥几字不仅将二人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且又将二人巧妙地衔接在一处,使人一看,脑里便有苏佛逗趣的画面。《金瓶梅》第七十三回:“薛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请了一段五戒禅师破戒戏红莲女子,转世为东坡佛印的佛法”[8]97。薛姑子所念“佛法”的本事应为《五戒禅师私红莲》,也是苏佛故事中重要的话本小说。清代孔尚任《桃花扇传奇》第五出“访翠”中穿插了苏轼佛印与黄庭坚三人在吃茶逗趣的笑话;《南屏醉迹》中以济公之口道出苏轼、佛印及黄庭坚联诗之事等。
文人对苏佛故事的评述,往往是借助苏佛二人之事为例阐述所写文章观点。如《效颦集》中讲“束坡与佛印交,不过谐谑而已。至若护道论者,皆尔曹假商英之名也”[9]87。张商英在佛法造诣很高,颇喜与僧人交游,他所著《护法论》在我国古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赵弼认为苏佛交游不过谐谑,而论禅机佛法,则当属张商英。
文学作品中的引用评述无疑是对二人故事的再延续,起到寄生流传的作用,也造就苏佛故事成为传统的文学创作题材。
(三)对故事的整理与收录
苏轼佛印故事题材内容繁多,文人们对故事的整理与收录是苏佛故事能广泛流传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宋时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清平山堂话本》收录为《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仅一字之差,内容完全一样,同时《宝文堂书目》也有著录。《问答录》中共27则故事,在明清文人作品中无一遗漏地都能找到,如《山中一夕话》《解愠编》《捧腹编》等分别将故事直接辑录。苏佛游赤壁的故事兴于元代,至清戏曲小说加起来就出现了7部类似作品,经典的转世重逢故事共有5部,从这些数字中可见故事在文人介入下的传播效果。
三、僧人对苏轼佛印故事的传承
由于佛印是僧人,他与苏轼的故事自然也在佛门中广为流传,而僧人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推动群体。
(一)禅宗典籍的记载
本文所指“禅宗典籍”是指除翻译的佛经外由僧人们编撰的用于记录佛门历史及要义的典籍。这类作品多以僧人传记为主,以叙禅宗世系源流为宗旨,其记载大都符合史实,通常为僧人的学习教材,同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除去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最早对苏佛故事有复杂情节记载的应该是北宋僧人惠洪所著《禅林僧宝传》。书中有佛印传记,还叙苏轼常梦自己前身为和尚。
东坡曰:轼十余岁时,时梦身是僧。往来陕西,又问:戒状奚若。曰:戒失一目。东坡曰:先妣方娠,梦僧至门,瘠而眇。又问戒终何所。曰高安大愚,今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后与真净书,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契,愿痛加磨励,使还旧观。自是常著衲衣。故元以裙赠之,而东坡酬以玉带。有偈曰: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会当乞食歌姬院,夺得云山旧衲衣。[10]177
稍晚些的《五灯会元》《续灯传》《佛祖通载》与此记述相差不大。又因此类典籍为僧人教材,对故事起到了一定的传承作用。
(二)僧人其他作品的记载
除禅宗典籍外,二人故事也流传于僧人们的文学作品。作品多为记载苏轼佛印间的交往、诗词唱和之事,故事中少了俚俗,多了对禅宗义理的参讨。惠洪的三部作品《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及《林间录》都录有苏轼与佛印交游事。明末僧人真可曾作诗《游云居怀古》以怀念苏轼、佛印、黄庭坚三人友谊。近代虚云《佛印桥谈心石》一诗,就专为二人所作。
再有现今流传颇广的几则苏轼佛印斗禅公案,自宋到清都未找到任何文本记载,最早的记录是1955年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为弟子开示佛法而举例子。笔者推测,此应是僧人口头所作,作为禅宗公案流传。苏佛间的许多故事都成了佛门中有名的公案,且出于对佛门的尊崇,在叙述二人故事中往往有美化佛印的迹象,这也是在流传的二人机锋、斗诗等故事中都是以佛印胜利而告终的原因。更因有僧人们的参与,使得故事深入宗教,扩大流传范围。
苏轼佛印故事是一个庞大的世代累积的故事体系,巧妙融合了各个时代的文化思潮几经演变,在民间文学,文人文学及僧人作品的相互补充、影响下不断发展,使之流传至今。可以说,苏佛故事的流传也是古代历史人物故事流传的缩影。
参考文献:
[1]徐苹芳.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补记[J].文物,1996年5月.
[2]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3](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4](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5]隋树森《元曲选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6](明)沈泰《盛明雜剧二集》卷二十四,影印民国十四年董氏诵芬室刻本.
[7](明)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
[8](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明万历刻本.
[9](明)赵弼.效颦集[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7页。
[10](宋)释惠洪.禅林僧宝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
——李福清汉学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