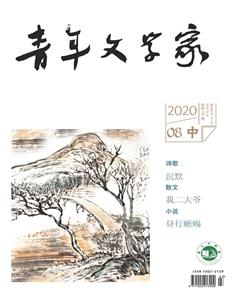论女性耽美读者的性别焦虑
摘 要:女性读者的性别焦虑是耽美小说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中被弱化的受方形象、刻板的女性角色、性压迫内容都与所谓的“性别反抗”构成悖论,暴露出女性读者徘徊在追求平等与贬抑自我之间,挣扎在“凝视”与“被凝视”之间,纠结在回避与释放性欲望之间。耽美小说中对同性恋群体的现实关怀十分有限,专注于为女性读者提供“代偿式”的幻想满足,只是女性掩盖焦虑的自娱自乐。相比较“积极的文本尝试”,耽美小说更类似女性主义理想失落下缓解性别焦虑的无奈选择。
关键词:耽美小说;性别焦虑;女性读者
作者简介:程雅南(1995.6-),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3-0-03
耽美小说作为以“男同性恋”为题材的类型化网络小说,盛行于青年女性群体。蕴含于耽美小说中独特的女性意識,常被研究者解读为性别平权的抗争。但文本中的种种矛盾都能够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并非坚定有力的性别平等呼声,而是无法抑制和平息的性别焦虑,它存在于女性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模糊地带,在文本中表现出来。
一.受方形象的弱化处理:平等追求与自我贬抑的矛盾
虽然耽美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都属生理男性,但耽美小说中的受方却是被弱化的。多数耽美小说中攻方的外形气质、职业地位、社会角色都更优于受方。受方往往处于被动、无力的一方。在一些耽美文本中,攻方与受方的职业或社会角色逆转了惯有的模式,乍看之下受方的权利地位、身高外形居于攻方之上,但受方与攻方的内心力量和相处模式并无变化,人物性格基模仍然是男权社会中二元性别的复刻。受方即使身居高位,内心依然可能充满不安全感或空虚感,或出于疾病没有完整健全的人格,或由于童年得不幸经历造成心灵某一处的缺损,对攻方依然有较强的依附性,在实现个人价值、寻求获得感或补全心灵中缺失的部分时,仍然依赖攻方提供的巨大能量才能得以实现,网络作家“priest”的《默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某网站,一个名为“为什么有人喜欢看耽美小说”[1]的问题下,高赞回答网友“蒋丞选手”说到:“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向往势均力敌的爱情。”女性读者之所以爱好耽美小说,是为其中体现出的平等意识所吸引,但事实上小说中人物关系却并非平等,存在了很大的力量差异,这正是通过女性作者对受方不断地弱化体现出来的,耽美爱好者陷入意识上的两性平等追逐与潜意识中不断自我贬抑的矛盾。
二.女性角色:无法摆脱的性别凝视
耽美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是挖掘小说中隐藏性别意识的重要切入点。边缘化的女性、刻板化的女性、屈服的女性是耽美小说女性角色的代表,“贤妻良母”、“性玩物”、“蛇蝎女人”等无一不是男性凝视下的刻板女性形象,女性读者对自我性别的想象仍然受制于男权社会性别认同。
女性角色在多数耽美文本中是被严重边缘化的。耽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篇幅,数量以及同主人公情感关系的程度都被大幅度淡化了,甚至被某些特殊题材完全规避掉了。不管女性是否参与攻受双方的情感主线,或只作为辅助性或工具性角色,她们的存在都有较大的局限性。“墨香铜臭”的作品《魔道祖师》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江厌离,对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和情感线索的推进都有重大作用,但出现的章节总共只有11章,只占全部章节不到10%。不仅在篇幅上被压缩,女性角色的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也很少给予正面刻画,相较于男性配角都是被边缘化的命运。事实上在现实中,异性与同性恋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同性的情感发展并非处于真空世界而是离不开异性的参与。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耽美小说并非将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进行积极探讨,更多的是作为提供爱情幻想的方式,这一点也将在后文予以论述。
破除性别传统印象,追求男女个性自由发展是女性读者爱看耽美小说的初衷,但是耽美粉却集体无意识地在小说中建构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角色,巩固了父权制审美对女性的束缚。耽美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实际上是按照主流体制下的女性刻板印象建构的,是耽美粉遵照男性“凝视”女性的方式创作出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包含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规约和偏见。《魔道祖师》中的江厌离,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父权制审美下的传统女性。
与江厌离的“天使”对立的“魔鬼”型女性形象,是男权文化对女性审美想象粗暴划分的另一个极端,在耽美小说中最为常见。例如心机深重的恶女、虐待主人公的后妈、破坏他人感情的小三等,这类女性角色在耽美小说中的分量感较前两种是最低的,她们多为工具性人物,通常情况下都为扁平角色。《魔道祖师》中反派头目的小妾王灵娇、“绿野千鹤”《妻为上》中的贵妃等都是典型的蛇蝎女人形象。
如果说江厌离是封建文化下的男性审美的终极标准,“淮上”的作品《难得情深》中攻方的情妇乔桥这一类女性角色则是现代消费主义与父权性别体制结合的产物。作者为乔桥赋予了很多传统情妇形象没有的元素:深厚的学识,理性的头脑,丰富的阅历,这使乔桥情妇身份的负面意涵被极大地“降低”了。然而这深刻地证实了该形象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男性“凝视品”。优秀女性完全放弃了个人努力而在传统男权体制中谋求生路,用一种“自发性”的假象,掩盖了这实际是女性在社会性别困境中奋斗之艰难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女性对男权体制与消费主义的共同屈服甚至趋附,被一种“为我所用”的至上姿态粉饰了。
如果将耽美爱好者的阅读感受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可以发现,耽美小说从某个角度上,并非对男性凝视的反叛,而是长久以来处于受视者的女性群体对男性控制心态矫枉过正下的产物。网络读者“李青青”谈及自己为什么喜欢耽美小说:“曾经都是观赏女人,突然有一天一种文化把男性摆上被观赏的地位,轮到男人被人品头论足肆意玩弄,那我肯定上赶着去搞,就怕速度不够快”[2]。福轲的凝视理论认为,“凝视”与“被凝视”是一种含有权力运作的关系。[3]男同性恋小说为女性群体所消费,似乎男性变成被凝视的对象和客体,女性借此完成了长久以来“男性凝视”的反拨,但这种“凝视”其实是无效的,耽美小说虽然拥有庞大受众,却仍然未能走出年轻女性群体的文化消费圈,极少有男性或真正的同性恋群体会阅读耽美小说,况且耽美小说中的各种设定完全为了女性读者的阅读快感服务,人物性格逻辑、情节发展规律都在真实性上大打折扣,并没有建立出全新的、真实立体且自由平等的性别形象,也就没有对改写社会文化中僵硬的男女性别气质做出有价值的突破。女性读者只是把在现实社会中“被观看”的无奈和怨恨等负面情绪在耽美小说中过犹不及的发泄出来,然而却根本无法挣脱男性凝视,才塑造出了一个个男权文化中的刻板女性角色,这种非善即恶,一分为二的建构显现出女性读者在父权制思维束缚下对自我性别的迷惘和错判,无法突破的男权性别想象犹如玻璃天花板一般,使女性挣扎在男性凝视与凝视男性之间。
三.同性生理与性压迫的悖论:难以直面的性欲望
男主人公相同的生理构造是耽美小说的首要特征,但是,耽美文本中的性爱描写却大量地体现着性压迫的特点,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悖论。耽美读者一方面追求性解放,一方面又难以直面自身性欲望,辗转通过耽美文本中压迫性色情内容实现性幻想、获取性快感。耽美小说的风行实际上是女性在传统欲望规训下的无奈选择。
大量的性暴力内容是耽美文本中性压迫特征的首要表现。性爱场面描写是耽美小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耽美读者的高吸引力来自它阅读快感机制中的重要组成——性幻想的满足。调查显示,47%的耽美读者会被小说中的色情描写吸引,超过一半的读者喜欢阅读具有较大篇幅色情内容的耽美小说,而喜欢“清水文”的读者只占不到5%。[4]在纯色情耽美小说中,暴力性爱几乎是全部内容。
在一些耽美文本中,受方无法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个人的性欲望,表现出性压抑或性抗拒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些女性耽美读者的写照。以《难得情深》中的受方朗白为例,当他面临身体伴随成长到来的变化时,无法正常对待自己的生理欲望和反应,表现出了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排斥。朗白对性的理解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女性读者达成了微妙的契合,即难以直视个人的生理需求甚至建立起了反射性的负面情绪。攻方和受方的性权利往往是不平等的,受方没有管理自己性欲望和性快感的权利,而是完全由攻方来控制的,受方实际上在性活动中被客体化了。
另一方面,女性群体在现实中努力想要为社会摒弃的封建贞操观念,却常在耽美文本中贯彻。多数耽美文本中的受方的首次性经历是与攻方完成,而攻方在遇到受方之前往往早已“御人无数”,表现为性态度放纵、性经验丰富的。受方的贞洁是被看重的,尤其是在带有包养、MB(money boy即男妓)、ABO(一种模拟兽类的人类性别分类设定题材)、主奴等标签的类别中,常常出现“雏儿”、“一张白纸”“没被标记过的后颈”等描述用以形容受方无性经历。在其他题材中也会突出受方首次性活动中的青涩和懵懂以强化其“处子”特质,与攻方的游刃有余形成对比。
耽美文本中的广泛性暴力、性压迫内容说明,相对于自愿性行为,被迫式的性活动描写可能更能够满足女性读者的阅读快感,这也许是令女性感到难以面对而辗转选择观看男性色情内容以规避性羞耻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贞操观、性活动中的自我客体化等文本表现,说明耽美爱好者还未能逃出父权制社会下对女性身体欲望的规训,将女性受到的束缚捆绑在小说中受方的身上,在无意识中再现了男性社会中的性压迫。
四.回避冲突:掩耳盗铃式的焦虑宣泄
“同性爱”本是极具探讨性的社会题材,但耽美小说往往对男同群体所可能面临的冲突做了回避或淡化处理。女性读者并非真正关切同性恋的生存状态或伦理性等问题,虽然同性恋话题在社会中的存在感和人群接受度不断提高,耽美小说包含一定的现实关怀,但女性读者更多关注对阅读快感的实现,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欲望宣泄不能根除却只能掩盖焦虑。
在一些耽美文本中,写作者会着意避开描绘同性关系所遭遇的阻碍,很少着墨于攻受所冲破社会阻碍时付出的努力,或者直接架空设置同性婚姻合法背景,或建立一个对同性恋接受度和包容度极高的真空社会。例如“漫漫何其多”创作的《婚约》,作者在文本里将现实中同性恋群体可能遭受的外部阻力统统清除,同性主人公们完全没有任何来自社会的恶意指控和歪曲理解需要面对,只需认真的上演两人间的爱恨情仇就好,这样的设定消泯了对现实社会同性群体的思考和关怀,只为作者一心一意描写两人的恋爱生活服务。
不仅淡化外部阻力的描绘,攻受对于个人性别取向认同的矛盾也很少在文本中得到正面展开的机会。一些耽美小说中,受方起初对性取向没有清晰认知,直到在攻方一次次关爱、解围或撩拨的时刻,才不知不觉中萌生出对同性的感情。但对于性取向这样偌大的自我认知调整,文本却往往寥寥几语带过,没有将正常人面临自我内心冲击时本该有的惊讶、挣扎和矛盾展示出来。例如“缘何故”创作的《情敌》可以看出,写作者隔离了耽美小说认真探讨同性恋群体内心挣扎和社会接受的可能,只停留在一种满足读者对“甜爽文”需求的层面。在狂欢化的幻想与意淫中,女性读者的性别焦虑得到一种“掩耳盗铃”式的释放,挣扎的性别“超我”和“本我”达成了短暂的和解。然而她们的迷惘并不能因此得到更多探索,耽美文学在直面社会禁忌和回避现实挑战之间选择了后者。
五.女性主义理想失落下的辗转选择
耽美小说之所以受到大量女性读者的青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焦虑的女性群体对女性主义理想的放弃追寻。现实社会不容乐观的女性生存困境,独特的文化背景与西方女性主义的隔膜,性别研究的学院化、封闭性,大众媒介对女性主义的种种误读等因素,使女性读者已无力相信,在生理差异是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女性仍有颠覆现有的性别秩序并最终达成两性平等的可能。同时,个人主义时代背景下,精英式女性主义责任感的消泯,致使她们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愿意以传统的方式为性别平权的共同理想抗争,而阅读耽美小说,更像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到的“滑下去到达极乐”[5]:相比焦虑的谋求出路,直接建构去生理差异的同性爱情小说,对于释放性别幻想和缓解焦虑情绪而言,明显是更容易的举措。
网友“不喜欢秋天的秋天”的留言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我向往男女平等,可我不得不承认,单从生理结构的层面看,男女平等就不可能实现。绝对的男女平等是个只能无限趋近但不能完全达到的理想值。现实中虽难以达到,但现代女性对于势均力敌的平等爱情的向往依然强烈,因此,既然追求平等,那就让两个性别相同的人谈恋爱吧,起码从生理上就做到了最基本的平等”。耽美爱好者的观点可以看出,相比有的学者眼中“积极地文本尝试”,耽美小说更像女性读者陷于对两性平等未来方向的迷惘与现实强烈平等需求之间的一种无奈选择。因为缺乏对理想性别关系的想象,自然也难以做出异性恋文本的建构,而辗转选择耽美小说获得代偿式的满足。本质上,女性读者的性别焦虑依然来自于现实与理想的困境,只是当“理想”变的“遥不可及”而又缺乏改变现实的责任感時,无处安放的焦虑感就寻得了耽美小说这一“代偿式”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知乎,“为什么有人喜欢看耽美小说”,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0050878.
[2]知乎,“如何看待耽美题材受到巨大欢迎这一现象?”,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0267500/answer/616713994.
[3]陈榕.凝视[A].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9.
[4]葛志远,庞明杰,蔡为,梁青.我国“耽美文化”的网络传播浅析[J].经济视角(下),2009(09).
[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M].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