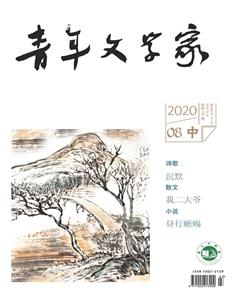论存文学小说中的民族文化书写
摘 要:云南哈尼族作家存文學坚持非功利的民族文化书写,描绘了云南边地独特的地域景观和文化景观。其民族文化书写的背后,折射出作家族内生活的真切体验与观察、对本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深情热爱、对多民族生存境遇及精神世界的关怀。作家深刻地反思了现代化进程对民族文化的灼伤,积极弘扬和传达边地民族天人和谐、感佩自然、崇怀先贤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存文学;小说;民族性;文化性
作者简介:徐惠芝(1997-),女,云南省曲靖人,云南省大理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3-0-02
云南哈尼族作家存文学,1952年出生于滇南普洱一个名叫南腊的小山寨,1975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归家乡山区中学执教多年,其文学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已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著有长篇小说《兽灵》《碧洛雪山》《望天树》等,中短篇小说集《兽之谷》《鹰之谷》,曾获第三、四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提笔以来,存文学一直坚持独特的民族文化书写,他以深切的民族体认、深沉的民族关怀,叙写了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的风情民俗和生存境况,刻画了古老族群的思维方式及生态观念,且不仅仅停留在民族风情的展示和民族元素的加工、外在的俯视和猎奇的观察上,而是完美地将民族性、文化性、现代性与文学性结合起来,以宽广的视野书写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1. 独特的民族景观描写
云南以美丽、神奇、丰饶闻名,而存文学写出了“最云南”的小说,以诗意的语言、神秘的笔触、丰富的动物写作,共同展现了云南边地独特的地域景观,通过迥殊宗教信仰和别样民俗仪礼的书写,刻画了边地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
诗意的语言总是给人以美的享受,作家对大山有着深厚的友谊与哲思,在他笔下平平无奇的山路便不再普通,洋溢着浓重的诗情——“这路啊,萦绕在我们的梦里,铺展在我们心上,将我们的现在和过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对于雾的描写也透着动态的诗意美,早晨阳光下的雾色是被野樱花和杜鹃染就的,风下的薄雾如蝉翼般透明,诗意盎然,诗意的语言着以神秘的笔触,则云南边地的神秘与美丽尽显其笔端。作家善于以夸张和魔幻的手法进行创作,《绿光》中从侧面切入对自然现象的描写,无一处写绿光到底是什么、究竟什么样子,给读者以强烈的好奇和巨大的想象空间。《兽灵》从大公鹿的视角写了豺狗和野牛等动物,也从其他动物的视角关照了大公鹿,渲染了原林中野兽争夺、弱肉强食的紧张氛围;《碧洛雪山》中借黑熊的视角叙述了雪山下的麦地村、村民、藏獒腊撒等,给人以毛茸茸的质感和置身原林的亲切体验。
存文学致力“于大山深处拾信仰”,将边地民族的宗教信仰考古般地复刻下来,并突出其迥异与特殊的一面,紧抓细节描写了多个复杂、神圣的宗教仪式和祭祀场面,如每年采茶时节,哈尼山寨里都要举行隆重的茶王、山神祭祀活动,猎人打猎前也会到猎神树下祭祀猎神。风俗民情、人生仪礼是多元文化中特定民族的精神基因和人情体现,作家在《兽灵》中进行了诞生、成年、婚姻、丧葬礼仪的阶段性书写,集中反映了哈尼人从出生、婚恋到死亡都有一套独特的礼节、习俗和禁忌。别样民俗的有意展示和描写,表现了作家对民俗文化浓厚的审美趣味,服饰、饮食、建筑、耕作方式等生产生活民俗渗透到了多民族小说的方方面面,如哈尼、傣族姑娘的筒裙,哈尼山寨的布局、懒火地,傣族的轮歇制等;贸易、历法、名号等民俗也有所涉及,如哈尼人与拉祜族、傣族的贸易交换,各种动植物的名称等;摇篮曲、情歌、挽歌、招魂曲、猎歌、节气歌等歌谣土语的直接运用,丰富了小说的情节与人物,使得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意味。
2. 深切的民族体认与关怀
进入文坛以来,存文学的哈尼族作家身份一直备受关注,族内生活的真切体验与内部观察,使作家不仅获得外在的文化景观记忆,也深刻了解到本民族的内在精神特质。存文学在哈尼山寨度过了童年、青年,幼年饥荒他与母亲到山林里挖野菜、摘野果,小时候也常常听到森林里许多动物的故事,青年学业结束后又回到家乡山区中学任教,和学生、家长下河摸鱼、上山打猎、收集民歌和民间故事。学生时期的存文学就以哈尼山的熟人作为模特,添枝加叶虚拟故事创作记叙文,后来族内普通人的命运、小人物的遭际都成为了他笔下的生动的文学形象和故事情节。其哈尼土地、文化书写的背后,是深情、由衷的热爱,“我们应该写它们,写高山和峡谷的雄浑与冷峻,写峡谷人的痛苦与欢乐,写峡谷人的坚韧,也写峡谷人的热情与愚昧,写峡谷塑造的人,写人塑造的峡谷,写出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2],映射了作家对朴素、热情、睿智、追求美好与幸福的哈尼族性格品质的高度认同与赞美,透露着民族自信与自豪。
作家出走自己的民族地接受着多元文化的洗礼,这一过程中很容易形成文化的对比、选择,甚至是自卑、批判,但作家仍然坚持自己的哈尼族身份,坚守自己的民族意识,带着对本族文化坚定的认同,继续民族文化的书写和弘扬。作为一个哈尼族作家,进行族性书写在一定意义上是种当之无愧的责任与使命,他关爱自己的民族也许是出自一种本能,但他还将眼光投向滇西南边地的众多民族,走向对多民族生存境遇、精神世界的关怀,体现着宽广的文化视野。从事写作三十年来,存文学一直行走在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入独龙江后写下了《独龙江的麦子》,为了写《山顶上的骝红马》走进哀牢山区,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边地民族的土地,怀抱对他们生存的关怀,将其真实的生存状态全然诉诸笔端——交通不便、医疗落后、物资匮乏、信息闭塞、教育落后、灾害威胁、野兽侵袭,比比皆是。其间恶劣的生态造成了人生存的困境,人的毁灭和背叛又造成了文化式微和生态的灼伤,着以了悲剧的色彩。
作家以真实创作关照着边地民族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条件,透过悲剧写作关切他们的生命、价值、命运和尊严,他认为一个创作者应当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深入体会一个民族的生活、性情和灵魂,也正是这种人文精神,使得他的创作更富于情怀、拥有更宽广的文化视角,也使得他的作品更加多元、鲜活而包容。
3. 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作家通过生态书写和历史笔触,传达与印证了古老民族长久以来与自然双向互动中形成的对于自然的态度和观念、朴实的思维方式、生存的智慧与历史进程等多元内涵。
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自从与自然互动以来就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从敬畏再到征服,现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尊重保护自然的观念,但作家力图强调笔下的古老民族因着独特的信仰,一开始就树立了感佩自然、天人和谐的正确自然观。他们将自然视作母亲一般的存在——“哈尼族常常唱这样的一支歌:藤子是我们的脐带,森林是我们的母親”[3],并且认为大自然的一切生灵和人类享受着同等的权力——“一颗树头投一片阴凉,一只野兽也有一个灵魂,对他们不能杀得太多,一条生命生出来总是有用的”[4],追求着人与自然的平等与高度和谐。
仰赖自然才得以生存发展、形成自己文化的边地民族取之万物的同时也明白万物有限,《碧落雪山》中按照麦地村的习俗,每次用网罩到一群山鸡或雪鸡,就得有意放走些强壮的公鸡母鸡,这样林子里的山禽就永不会绝种。万物有限与取之有度,反映了边地民族顺应自然规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和行为思维方式。科学理念的背后映照了边地民族多元平等、互惠互利、自我约束、保护建设的行为思维方式,作者的民族生态文化书写意在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意识,呼唤读者生态忧患与责任意识的回归。
先辈是人类得以继续生存与发展的最好的师长,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作家深入笔下民族的精神世界,解开他们存于世间迷惘之时所寻求的对象之谜。
出于对祖先的崇敬和历史的怀想,存文学所写的少数民族一代又一代将祖先定下的古规习俗约定视为珍宝,并且孜孜不倦地承继与传扬下去。《望天树》中作者记录了一项即将被世人遗忘的傣族传统官职——布闷掌,以专为傣王管理大象为职责,通过末代布闷掌波西的回忆,拉出了傣族历史上的一场血雨腥风的人象大战。《碧洛雪山》中亦是通过傈僳族老人阿梨邓拔的怀想,引出了碧洛雪山脚下傈僳人两百年来的斗争。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然的精灵,正是因为有了认识历史、继承历史的意识,对于祖先遗产的继承,既能够延续发展自身又有着教化的奥义。
综上所述,踏入文坛三十年,存文学笔耕不辍地书写着滇西南边地古老民族独特的文化,挖掘那些不为人所重视的有价值的东西,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以其熟悉的族内视角和生活积养在创作实践中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清晰淋漓地表达了出来,展现出了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以深沉的人文关怀和广阔的文化视野,悲悯边地民族的生存发展、精神境遇,呼唤人内心深处的柔软。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存文学的民族文化书写是独树一帜的,对于承继和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着重大意义,更引领文学寻找着失落的灵性与美感。
参考文献:
[1][3][4]存文学.碧洛雪山[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7. 131.49.
[2]李丛中.传统文化与哈尼族新文学创作[J].思想战线,1993(0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