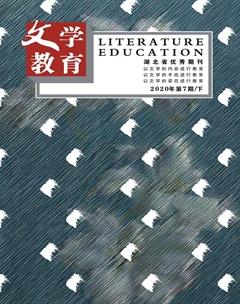匠人的未来

2019年下半年,一枚仙女在网络横空出世。她于百工技艺无所不晓,千年传承皆亲力亲为,着装风格则穿越在古风、淘宝之间,红颜倩影栖居于诗意田园之地,一时惊呆无数番邦看客,跪倒成片小资铁粉,以至于前几年在主流媒体走红的工业党人都相形失色。
有研究指出,熟练掌握一门复杂技艺,需要一万小时以上的重复训练,弹钢琴、学外语等都是这样。所以,只要稍微做点数学,就能看破影像中有几多假象。不过,影像即使是假的,流量却是真的,因为粉丝的情绪是真的。对于这些对屏兴叹的人群,近年另有一种来自日本的叫法,就是社畜——公司里的牲口。但我这里敢说林间的仙女和公司的牲口实际上是同一群人,倒不是掰着手指点数的,而是文科生熟悉的一种解题手法——物质与意识、社会现实与审美意象之间的函数关系,社畜的处境与仙女的手艺之间是种反比例关系。要更深刻地思考这个函数,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的著作《匠人》是个很好的导引。
一
当我们说起匠人,最直接的印象应该是木匠、石匠、泥瓦匠、金银匠等等这些手工艺人,但桑内特对匠人的定义要广泛和深刻得多。他把匠艺活动视为人性中的一种基本的、持久的冲动,是一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欲望。所以,所有在工作中追求质量至上者可以归入匠人的范畴。根据这个界定,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不被视为匠人的两类人群,其实正是匠人的典型代表。
其中一类是农民,对这一点我有深刻的体会。我的父母就是农民,他们和许多农民一样,有一种“闲不住”的特点,劳动对他们而言,绝非某种辛苦的麻烦事(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实际上,我的乡亲把苦变成了一个动词,劳动叫作“下苦”,种地叫作“苦庄农”。这种苦不只是陶渊明说的“田家岂不苦”,而是苦中有甜,辛苦中有沉迷。沉迷其实就是“把事情做好”的欲望;而之所以沉迷,是因为“把事情做好”是他们对自己存在价值的深刻体认和要求。第二类匠人是学者。优秀的学者和农民一样有“闲不住”的脾性,他们对工作的热情,首先出于“把事情做好”的冲动,不然就没法解释,为什么一些退休的学者,反倒爆发出更大的学术热情。就像写《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胡塞尔一样,这种严格性其实使他们的内心饱受折磨,但却乐此不疲、持之不懈。
总之,根据桑内特的定义,像农民和学者这样追求质量至上的许多职业,都可以包括到匠人中去,比如清洁工、育儿嫂,实验员、快递员、护士等等。实际上,桑内特明确说,古代的匠人就是今天的中产阶级。我们则可以补充说,这个定义其实更接近我们语言中的“劳动者”。而定义外延的扩大,确实更有利于分析我们这个劳动分工日新月异的现代。实际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传统的工匠日渐式微,今天谈及“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人,那些“码农”和“excel女工”等等恐怕才是最突出的代表。但此类自嘲的命名也透露出,高学历匠人对自己身份的失落与不满。在桑内特看来,这个状况确实与近几十年的“新资本主义”发展有关,但也与更古老的文化偏见有关。
二
实际上,匠人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不尴不尬,虽然不可忽视,但总体偏下。在印度传统中,工匠组成的首陀罗位于种姓的最低一级,仅比贱民高一些。在中国传统中,手工业者的地位同样不高,正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者的地位都不高,匠人在士农工商的社会象征序列中比农人还要低些。西方文明也差不多。桑内特的老师汉娜·阿伦特把劳动的人分成两种,一种叫劳动之兽,一种叫创造之人。顾名思义,前者只会像畜生那样闷头干活,后者还能抬头思虑。因为前者只知道“怎么办”,后者还会问“为什么”——所以后者得管前者。很不幸,匠人被划入了劳动之兽。但是,在桑内特看来,这些看法充满了偏见。
所以,匠人地位的低下,还有更深的根源,与思维中的“形而上学”偏见有关。形而上学思维往往把世界以及相应的知识分成高下有别的两部分,比如理念世界高于现象世界,眼或心高于手,灵魂高于身体,理论高于实践。匠人,因为他们首先与物质、身体、实践打交道,注定要低人一等。但是,在二十世纪,这种偏见遭到了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等人的深刻批判。海德格尔是个鞋匠的儿子,他彻底颠倒了前面那种秩序,而认为人类对世界的“把握”恰恰是从鞋匠式的敲敲打打开始的。人类是在与“上手”的工具打交道的过程中“体认”世界的,我们的生活世界首先就是这个工作構成的世界,超然世外、高高在上的理念或理论其实是种虚构。所以,人类的能力排序并不是“眼高手低”,相反,我们的认识始于手和手艺。其实,日常语言习惯中还保留着这方面的证据——在汉语、英语和德语中,我们都能找出一些表示“理解”的词,源于抓取、手等本义,如掌握、grasp、erfassen等等。
所以手艺并不是一种低等的技能,反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人类一出生就具备的本能。婴儿的发育始于试图抓牢物件的无意识举动,始于对任何东西舔尝的兴趣。儿童的游戏更是说明了手艺所具备的根本重大意义。研究者发现,男孩总是要将积木大厦或纸牌楼房搭到倒下为止,女孩子则会反复地给布娃娃穿上衣服又脱掉。但这类现象与弗洛伊德所谓的性器理论关系不大,男孩子其实就是在探索积木到底能搭多高,女孩子则是在尝试掌握熟练地解开纽扣和调整衣服的能力。这其实是一种早期的匠艺锻炼,是和物质“对话”以获取知识的过程。
而割裂大脑和双手,对于完成工作以及人的发展实际上都是有害的。桑内特研究过电脑制图软件CAD对于建筑设计工作的消极方面。许多设计师都指出,这种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设计任意造型的技术,虽然方便,却也带来了深层的问题。比如,设计会与实地环境和需求脱节。另外,过于容易的绘制过程,也缺乏手绘图那样的精雕细琢与情感投入,丧失了在实地考察与设计方案之间往复调整的可能。
总之,匠艺并不是一种低下的技能,而是我们“把握”这个世界的根本途径。在匠艺保持了大脑与双手协调的意义上,它其实是一种更健康的工作状态和生存方式,对我们这个机器时代、电脑时代是一种深刻的警示。而且,匠人的社会生活模式也值得我们珍视。
三
独自背着工具四处谋生,辗转于不同的主顾,靠手艺吃饭,合则来,不合则散,这似乎是传统匠人留给我们的印象。匠人,尤其是高水平的匠人具有独立能力和精神,在当代对中产阶级与公民社会的讨论中,我们仍能发现一点逻辑端倪。但与这个流行的形象相反,桑内特指出,出色的匠人活动总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匠人倾向于合作,他们的生活需要一种共同体,这既是匠人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匠艺精神的内在需要。
复杂的匠艺需要分工合作,这既包括不同工艺环节上的分解,也包括不同工艺难度间的分工,还包括技艺的传承与切磋。这使得任何工场都是一个拥有不同技能与权威的匠人组成的集体。而且,长久的共事也需要工作伙伴之间具有深层的交流和默契,当然也会自然生发工作之外的交往。而在社会分工的大背景下,匠艺的锻炼和发挥也需要一种稳定的生活环境。精深的匠艺需要旷日持久的学习磨炼,复杂的工艺也需要心无旁骛地慢工出细活。但匠人作为最早的专家,它不能像农夫那样能实现日常需求基本的自给自足。匠人的人生和职业都需要相对稳定的预期。
确实,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匠人都生活在某种共同体中,或者说在拼力争取这种工作状态。中世紀匠人就是如此,他们直接地在由师傅和学徒组成的共同体中生活,作坊就是他们的家,是他们工作、吃饭和休息之地,与师傅之间也确实有一种“师徒如父子”的教养关系。在作坊之外,匠人们还有自己的行会,这保证了他们能集体地解决工作之外的更复杂问题。现代的匠人——产业工人在较长的时期内多多少少也保留了这样一种作坊或行会式的共同体生活。
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源于军事,它分工明确,纪律严明,和军队一样是一种科层制,以至于马克斯·韦伯称之为铁笼。但桑内特指出,即使它是铁笼,也具有一种家园的因素,尤其在其作用发挥较好的时代。比如二战之后的日本企业,它等级森严,但也较为稳定,严格的高标准管理和年资制度为工人提供了稳定的职业尊严和人生预期。而且,日本企业培育了一种针对业务坦诚交流的民主作风,这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好好先生风气极为不同。用质量管理专家爱德华兹·戴明的话说,将一个组织粘合起来的,是相互交流和共同投入。这背后的制度条件,是20世纪的企业里熟练的中等阶层劳动者的科层位置比较稳定,他们可以从年轻时代一直干到退休,他们的生活预期与工作预期高度相关。所以日本的产业工人,为了完成任务,花长时间在一起劳动,甚至很少回家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生活共同体与匠人精神的发挥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
四
但在今天,始终有一些因素影响着匠人精神的发挥和匠人生活共同体的稳固,这些因素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首先,命令会让匠人失去责任心。桑内特研究过两个例子。一个是他访问前苏联时发现的,当地的建筑工人对工作敷衍潦草,毫不用心;另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系统采用福特制式的计件标准来衡量医护人员的工作后带来的问题。两个例子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却反应了同样的问题,即来自外部的命令式管理取消或干扰了匠人对工作的责任和投入。苏联的制度,是中央计划与现实的脱节。僵化的中央官僚机构在项目估算中往往错得离谱,规定的运输路线不合理,工人和施工队又缺乏沟通。这种命令的背后,则是当局对地方的不放心,生怕自我管理会导致对国家的抵抗。但对于具体工作而言,其后果是具体实施者缺乏根据实际情况修正上头命令的空间,工人的责任心无处发挥。
英国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它源于新的量化和精准管理脱离护理工作的日常,妨碍了医生对于病人的“不规范”的关爱,比如护士在和病人的闲聊中发现某些疾病的线索。这本来是护士对工作的内在热情的一部分,但在新的管理标准下却变得不合法了;对于医生而言,尝试不同治疗方案也本来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但在新制度下也被大大限制了。于是在面临疑难杂症时,胡编乱造一个病名反倒成了医生们符合规定的应对方式。总之,这些匠人本应是自己地盘的主人,应该有协调管理命令与工作实际的自主空间,但是体制化标准的强制推行——一种非人格的命令反而伤害了医护和病人打交道的职业精神。
其次,过度的竞争会破坏匠人的合作。现代社会迷信竞争,但对企业运行的实证研究颠覆了这种管理意识形态。比如在移动电话的发明中,摩托罗拉和诺基亚采用了某种合作模式,鼓励不同研发部门提供各种创意,构建“技术货架”,供各部门共享;或者模糊各部门的界限,邀请销售人员和设计师参与研发会议,等等。最终,这两家成了移动电话时代的胜出者。但爱立信的做法与此不同,它将问题分配给各个部门,导致缺乏有效的沟通以催生新产品,技术远远落后其他企业。这里的管理奥秘就是,如果一个组织的个人或成员之间存在竞争,而且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获得奖励,那么每个人或部门都会隐藏自己的关键成果。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领域都在加强优才统治,以及某种赢者通吃的规则,对它引发的消极后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三,利润追求会深刻彻底破坏匠人精神。在现在企业背景下,这个利润追求主要的还不是匠人个人的实用主义,而是他们寓身其中的组织本身的唯利倾向,会更猛烈地破坏匠艺发展和匠人精神。
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匠人的这一精神某种意义上也塑造了他的宿命,因为把工作做好能给他们事业感,给他们内在的尊严和价值感,当然,他们也渴望由于自己的出色工作而获得应有的回报。但是,近几十年里“新资本主义”文化(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在不同层面瓦解了匠人精神所需要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其中最关键的,是金融业脱实向虚以及泡沫经济盛行,造就了企业的短期利益导向,这一倾向随着全球化进程从西方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将全世界都带入一个盲目的投机经济中。与此相配合,企业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弹性”,匠人所需的稳定的职业预期完全消散,回报则越来越小,两极分化持续扩大。迅速的产业变迁也使得匠人技能的保质期越来越短,对无用的焦虑挥之不去。而且,这一趋势还在向企业之外的福利部门如教育、医疗等领域蔓延。总之,这个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谓的“流动的现代性”在持续地摧毁匠人和匠人精神。
五
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的匠人或社畜们至为熟悉的场景。在这个背景下,匠人要获得生存的尊严,甚至匠艺的维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正是现代都市中高学历、高科技领域的白领,突然迷恋起村姑的手工表演的原因。那个关于手工的幻影世界,正是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负片,表现了他们在工作中找不到尊严、价值时的治愈尝试。但是,沉迷于过去世界的幻觉虽然无限嗨,还能带来高品味的自恋感,却基本于事无补。作为一位社会学家,桑内特没有浪漫的乡愁,他更多地思考的是匠人(社畜)的未来。
但未来并不乐观。在桑内特的书出版十二年后的今天,破坏匠人精神和尊严的社会因素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而机器吃人的威胁随着AI技术的加速应用而变得日益严峻。另外,偶然的事件会让这个状况更为棘手甚至失控。但无论如何,想像一种未来是急迫的、必须的。
而要思考这个未来,告别乡愁式的自恋和社畜式的自怨自艾恐怕是第一步,唤回匠人或劳动者的真名则是第二步,而更关键的第三步,也许只是寻回匠人最为古老和朴素的那个梦想:安居、乐业。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