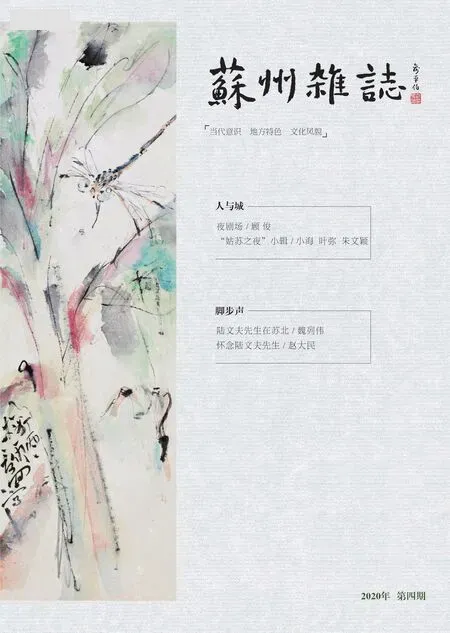美食四章
潘敏
青 梅
立夏的风尚有一点点凉,运河边梅树林里的梅子已青,比枇杷大了。
去年五月去洞庭西山明月湾村,坐在依山而建的小楼里听雨吃枇杷,一天过得缓慢而愉悦。黄昏离开时,主人送了每人一筐枇杷和一大袋青梅。我不知道要青梅作什么,便送到了母亲家。母亲把青梅分一半给大姑妈,留一半自己浸了白酒。今年春节后在母亲家说起酒,父亲把一大瓶青梅酒拎了出来,青梅浸久了已发黄,酒色淡淡的青。我尝了一口,微酸,很爽口,酒劲也和顺许多,似乎没那么凶了,便说今年也要做点青梅酒。母亲关照我,一定要白酒啊,最好高度酒,你大姑妈用黄酒浸,又加了糖,结果起了霉头。

☉ 青梅
前几天去平江路,见一身布衣布裙的孟婆,正往天青色的瓷碗里倒新酿的山楂酒,酒色玫红,看上去特别娇美。想起自己夸口要做的事,脱口说今年我要记得做青梅酒。孟婆笑笑,转身拎出一瓶,说是才做了两天的青梅酒。她晃晃手中的酒瓶说,青梅是雨后采的,一粒粒都干干净净,也没再洗,直接浸了酒。那瓶是白玻璃的,方口,白酒漫到瓶口,瓶里一半是青梅。
昨天住在太湖边的光福镇,是一个朋友的亲戚家,在石嵝村里。晚上有月光,亲戚家的阿姨叫我们带只布袋去山脚下采青梅。2006年秋天我搬到运河边居住,是看中了河边有成片的树林,包括有一小片梅树林。我喜欢树上结青梅的梅花,也是此后开始的。年少的时候喜爱蜡梅,也爱红梅绿萼,唯对开小白花结青梅的梅花很不屑。《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林黛玉和贾宝玉在妙玉房内品茶,黛玉问妙玉:“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妙玉说的梅花当然是苏州的。那玄墓是光福太湖边的一座山,在邓尉山南,山连着山,山上有无数的梅树,大多是这样开白花的梅花,号称“香雪海”,是每年早春苏州人探梅的地方。年青时不爱去光福看梅花,觉得那里的梅花长得小眉小眼,窸窸窣窣的,颜色白得也不透,远远地看,像洗不干净的抹布。搬家的那年,春节后不久,运河边的梅花便开了,比“香雪海”的早,应是向阳的缘故。有一次晚饭后散步走到梅树下,闻到一阵阵梅花香,心里诧异,以前从来不知道这小白梅有香味。那天折了两小枝,回家插在瓷瓶里,细看深褐色的花枝,花蒂暗红,花瓣粉白,花蕊是淡淡的黄,花香幽微,忽然觉得这小白梅很贴心。想想年青时对梅花的不屑,真是轻狂。
石嵝山脚边的梅树约有百来棵,树叶子茂密,藏匿了无数青梅。借着幽微的天光,我在树底下顺着梅枝摸采青梅。捏到硬而圆的青梅只要手指稍使点劲一别,青梅就采下了。摸了两棵树,便采得半袋青梅。回到朋友的亲戚家,在灯光下一看,青梅大小匀落,浮着一薄层茸毛,宛若处子。偶尔有一两枚老一点的青梅青里泛红,像女人害羞时脸上的红晕,艳得好看。挑了一颗青梅,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一番,咬下一丁点。知道青梅酸,但还是超出了想像,想吐出来,又一口咽了下去。真不是一般的酸。写到这里,我的腮帮子又酸起来了。
记得那次去西山明月湾,郁岚也拿了一袋青梅回家,她说她全做了梅酱。我很想尝尝梅酱的滋味,可每次去她家的时候又忘记。昨天看着采的那半袋青梅,有点后悔采得少,不能试试做梅酱了。
今天到家把青梅全部洗了一遍,然后摊放在匾里沥干。去三元二村的玻璃器皿店选购了两只宽口五斤量的瓶,又去超市挑了四瓶43度的泸州老窖和二斤冰糖,最后把青梅均分浸入。在浸入前,还用一根竹头牙签,在每一个青梅上扎了些小孔,也算用足了心思。家里人在瓶盖上贴了一个标签,注明年月日,说过一个多月应该可以吃了。晚上,灯光下,酒瓶里的青梅一个个青绿圆润,仿佛胖了一点。
咬 秋
今日立秋,去父母家时带了一只西瓜。古人在这一天讲究吃西瓜,这风俗我小时候还有,称为“咬秋”。
客厅里拉上了窗帘,父亲这两年视力越来越不好,怕光。今天风并不大,天却蓝得不可思议。深深的蔚蓝,深得出水,大团大团的白云,蓬松柔软,天空美艳得让人心里不安生。这一切,父亲却不能望一眼。
捧西瓜到水龙头下冲一冲,然后剖开。父亲说瓜不错,他听见了西瓜碰到刀刃一下爆开的声音。在所有的水果中,父亲最爱西瓜。从前一到夏天,卖西瓜的船歇在砻糠桥堍,有钱的没钱的,每家每户总要去抱只西瓜。家里富裕的买上一担,家里拮据的,凑几张毛票,买一两只。
黄昏,院子里泼过井水,搬出竹榻、木凳、小方桌,切好的西瓜放在脸盆里端出来。又沙又甜的西瓜很难得,若是恰好吃到这样的西瓜,父亲总是要吃个痛快,末了补一句:西瓜顶好。他嫌枇杷核大肉少,桃子吃了要肚子痛,杨梅酸的居多。总之,世上只有西瓜是最好的水果。他说,再不甜的西瓜,至少比黄瓜好吃。我不这样感觉,再怎么甜的西瓜吃两块就够,有时宁可吃黄瓜,刚摘下的长满刺的黄瓜,它的清甜我一直喜欢。
比起西瓜的瓤我爱西瓜皮。西瓜皮有三个层次,内层连着红或者黄的瓤,松软而有水分。这一层要用刀批掉。中间层是青绿的皮肉,厚薄要看西瓜的品种,皮厚它也厚。这是我最想要的。去掉软甜的内层,再扦去硬而脆、带纹路的绿皮,将中间层切成细条状,洒上盐腌一两个小时,然后挤去水分。点火起油锅,放进切碎的小葱,待油热,哗啦一下倒入西瓜皮和先前爆得半熟的毛豆子,铲子翻两个身便可装盘。除了葱、油、盐,其他一概不放。一盘生青碧绿的西瓜皮炒毛豆上桌,又鲜又香又脆,配一碗白米粥,再热的天,也有了好胃口。
西瓜皮的第三层,即西瓜最外的一层带花纹的皮。只要刀功好,这一层皮可以扦得纸一样薄。这一层皮也有不一般的好。这是我曾祖母年年要做的事,每年盛夏,她收罗起西瓜皮,扦去内里软甜部分。在她眼中,西瓜皮只分两层,内层与外层,去掉内层,就剩下了她要的皮。一脸盆西瓜皮,加上几把粗盐,捏过几遍后放到匾里,端到大太阳下暴晒。晒过一天,再翻个身,继续晒。绿底黑纹的西瓜皮在太阳光下蜷缩,越卷越紧,绿色的底色也渗出一点点玉白,摸一摸,像有韧劲的牛皮纸。曾祖母把晒得干透的西瓜皮当宝贝一样,装进有盖的广口玻璃瓶。家中有谁说喉咙痛,她会问要不要吃点西瓜皮。有一次见老太太的西瓜皮瓶忘记抱进房间,我学她的样拎了两块泡水喝,满口的咸味中竟吃出了一点甜津津。
前年夏天喉咙痛,想起许多年前曾祖母腌制的西瓜皮,依着记忆,晒了一小匾西瓜皮备用。谁会料到,多年后,我把嘲笑过她的一些作派,一一拣了起来,晒西瓜皮是其中之一。岁月总是在一旁冷笑,你慢慢活成了你曾不屑一顾的他人的模样。这是常有的事,不难堪。
遗憾的是,那么爱吃西瓜的父亲,现在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痛快淋漓地吃西瓜,只在炎热的三伏天,慢慢地吃一片两片西瓜。他说,吃多了会不舒服。
萝 卜
秋天已来,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季节,乡下的孩子大约都喜欢。地上的黄瓜番茄落市了,但地底下的萝卜已长大,山芋也快成熟,拔一只萝卜山芋在小河里洗洗,吃吧。
萝卜有一个古名字,莱菔。这两个字很秀气,很婉约的样子。而萝卜,一个萝卜一个坑,名字实在,少了点诗意。当然,这是没由来的,仅是人的臆想。
一点红,是萝卜的一个品种。有球状的,也有长圆形,总有一团胭脂色,洇开在雪一样白的萝卜皮上。一点红萝卜好看,水分充足,但宜熟食或者凉拌,拔起来就吃有点辣,辣中又有很清爽的甜。吃它有点美中不足,不吃又有点不甘心,简直有一点少年人恋爱中的摇摆不定。我喜欢一点红萝卜的皮,稍厚,酱油腌过之后很脆,就着茶泡饭,吃起来爽快。
杨花萝卜是萝卜的另一个品种。关于杨花萝卜,我记得汪曾祺先生写过,说是杨花飞舞时上市的,红皮,即北京的小水萝卜。我疑惑,苏州的杨花萝卜和高邮的杨花萝卜不是一回事?苏州的杨花萝卜春天有,冬天也有,比大拇指粗一点,一尺来长,皮白而细,不像从泥里挖出来的,倒仿佛雪堆里长出来。杨花萝卜好看,也好吃,切成菱形炖小排骨,一屋子的香。杨花萝卜在汤里白得透明,入口即化,比肉还俏。至今不知道,汪先生的杨花萝卜与我见到的杨花萝卜是不是一样物事。我想大约不是,除非杨花萝卜有红皮也有白皮的。
苏州也有大萝卜,我买过一只,足有三斤重,说叫苏州青。苏州青也是白皮,只根部有点淡绿色。苏州青可以白笃炖汤,一烧就熟。也可以与肉红烧,青花碗里盛出一大碗,浓油赤酱的。别看苏州青粗实,性子却绵软,烧好后很酥烂,吃口也不错。有一次我红烧苏州青,洗好切成条状,起了个大油锅,然后加好酱油、盐等等作料,大火烧滚后,再调至小火焖,然后我到电脑边上去了。你想,人一到电脑前,心思怎么还会在炉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在电脑前终于闻得了萝卜浓香,头一轰,大叫一声冲到炉子前关掉煤气,心想今天的萝卜要烧成焦炭了。开锅一看,菩萨保佑,萝卜微焦,红成了琥珀色,透明发亮。拿过筷子吃一块,滑糯,细腻,味道丝丝入扣,自认比大饭店做的还好。这样歪打正着的事不敢想下一次,下次谁知道会烧成什么样子呢。
但不知为什么,苏州人不怎么爱苏州青,买萝卜还是中意杨花萝卜,挑三四根,回去炖一锅排骨汤,关火前还喜欢往锅里洒一把大蒜叶子。最好是冬天,关上门炖出一锅杨花萝卜小排汤,肉香,蒜香,萝卜香,一屋子暖人心扉的香。有时候想想,苏州人对吃的心思过重,在小细节上斟来酌去,未免太计较。
北方有名的心里美萝卜我也吃过,大约不懂得它的风情,没吃出它的好来。倒是哈尔滨的萝卜缨子,让我吃出了惊喜。多年前的冬天去东北,路过哈尔滨的平山镇,在一家暖气打得很足的小饭馆吃午饭。桌上有一只特别大的白瓷盆,盆里一半放着拇指大的小红萝卜,一半放着萝卜缨子。萝卜缨子,也就是萝卜叶子,那些萝卜缨子碧绿细嫩,蘸酱生吃,像是吃了一把清心润喉的嫩草。几年过去,还想着那些萝卜小缨子的美妙,可惜苏州看不到这么嫩的萝卜缨子。
听人说,白萝卜开白色或淡紫红的花,青萝卜开紫色花,而红萝卜的花却是白色的。我只见过白萝卜的花,其他两种萝卜花没见过。心里想着哪天买三只花盆,一只种白萝卜,一只种青萝卜,一只种红萝卜。想看萝卜开花。
泡泡馄饨
刚入秋的光景,天气晴朗,碧青的天上有鱼鳞似的薄云。午后,在小巷子里转了两个弯,到艺圃吃茶,同座的是陶老师、常老师等几个朋友。茶还未上,召集吃茶的吴校长便说,喝好茶去吃泡泡馄饨。从她郑重的话语里,听出泡泡馄饨似乎是今天的大餐。
艺圃几年没去了,还是老样子。坐在延光阁里吃一杯龙井,听一桌又一桌的老苏州人说话。外面临水的假山树木,与从前没什么两样,一切像是从未改变过。茶过五巡后,陶老师站起来说,去吃泡泡馄饨吧。
出艺圃,往东走,快到头的时候,看见馄饨店了,原来在吴趋坊,不难找。店不大,一开间的门面,门口支着一口大镬子,一个身材饱满的中年女人在下馄饨。此时是三点半,馄饨店里居然客满,好在屋外有一大桌子,我们一人一把匙,坐在桌子边上等馄饨。镬子边还有只小台子,上面放着调料,无非也是油盐酱醋,一碗切细的小葱。听得花好桃好,没吃到还是不知道滋味。
一大镬的水沸了,女店主开始下馄饨。这家的泡泡馄饨果然与别家有些不一样,转眼间,一镬子的白泡泡翻起来了。女店主摆开六只碗,上汤水,起馄饨,洒小葱,一只托盘把六碗泡泡馄饨端到了我们桌上。一桌人感慨,一看就不一样啊。
是的,看看就不一样,泡泡起得这么大而圆整,这样的泡泡馄饨已经很难看得见了。陶老师分明有点激动,他想起来这是他少年时吃过的馄饨,也是在这条街上,但不是现在的位置。他问女店主这家店从前开在哪里?女店主手一指说,喏,就在这条街的里面点,六年前搬过来的。女店主还说,这店原是她嬢嬢的,传给了她,她16岁就在店里做了。陶老师点头,就是这家店,我看出来了。
每人一碗,我们坐在倒西太阳下吃泡泡馄饨。馄饨热汤热水,加上太阳光强,一个个吃得额头上冒汗。象牙白的泡泡馄饨有点透明,里面是一点隐隐的绯红。这绯红,是猪肉的影子,点到为止。汤水清爽,有一点点猪油香,细细的小葱漂在上面碧绿生青。一口一只,皮子有一点韧劲,吃口极好。我问女店主,这皮子是你们家自己做的?女店主说是请人定做的,和别人家不一样的。她又说,我们家的馄饨皮子好,做得好,汤水好,当然好吃。我们笑,这是三好馄饨啊。还有一好她没说,价钿便宜,一碗泡泡馄饨二元五角。我还吃了一只肉汤团,汤汁鲜美渗到皮子里,一只一元二角。吃罢,擦擦汗,各自心满意足回家去。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同吃馄饨的陶老师去年冬天去了天堂,不知道那里有没有馄饨汤团。没有的话,他会想念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