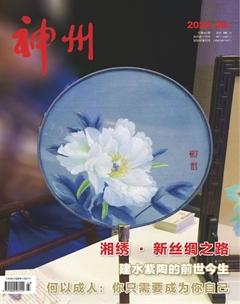文学作品中的动物隐喻
摘要:隐喻是语言学中一直以来探讨的热点问题,在文学界,隐喻为文学创造带来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那些或残暴、或羸弱、或“安分守己”的动物映射着人类社会,以之为牵引的绳索,立足隐喻的视角,去窥探鲁迅笔下人与兽的共性。
关键词:鲁迅;动物隐喻;语言学和文学
一、语言学与文学中的隐喻
隐喻被亚里士多德定义为“把一个事物的名称转移到另一个事物,要么根据模拟关系从种转向种”[1]。隐喻的存在是无时无刻的,正如《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指出“它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而且还存在于我们思维和行动中”[2]学术界认为语言学和文学尽管都属于中国语言文学大类之下,但两者并不存在交叉性。但以语言学中的“隐喻”这一学术要点为例,它在文学作品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学作品中,许多思想内涵的表达不会直截了当,而隐喻就为作家思想的表达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手段,通过对隐喻的认知和理解,读者也能体会到文学作品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
二、动物隐喻
由于动物不同的特性影响了人们对其的认知,人们转换这种概念,而这种转换的过程就是隐喻的过程,从而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例如“黄鼠狼给鸡拜年等熟语,日常中我们使用某一种动物的某一行为与人类的表现作对照。
文学作品中的动物隐喻是具有独特的艺术性,鲁迅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小说集《呐喊》中有《兔和猫》、《鸭的喜剧》;《朝花夕拾》中有《狗·猫·鼠》,在散文诗集《野草》种有《狗的驳洁》等等,还有随人物而出现的动物,例如《伤逝》中的小狗,《阿Q正传》中的狼等,在鲁迅的笔下,动物的意蕴是与人共生的,即便是同一种动物,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时代背景,显现不同的含义,而作为加工机制的隐喻就是将本来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进行一定的意义转换。
三、“驯服”背后的“奴隶”——狗
狗作为一种容易驯服的物种,为人类所喜爱,“听话”的特性满足了人类极大的征服欲。但传统文化中塑造的有关狗的文化现象绝大多数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会在涉及狗的语境下传达出的不友好的意思,狗的的性情映射到人的身上就会发生变质,例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叭儿狗,叭儿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哈巴狗,“叭儿狗”隐喻着当时时代铸造下的一种自认为是文化人的“伪知识分子”,他们的人性被驯化,摇尾乞怜是他们的常态,世故的作揖陪笑是他们的苟延残喘,它们表面看似温和,实质上是被驯化的悲哀,它们看似顺应时代,实质上是旧时代的奴隶,它们经不起时代的变革,早已依凭主子惯了的叭儿狗是高傲之下不能戳破的无可奈何。
四、“凶猛”背后的“腐朽”与“觉醒”——狼
在古代,人们对狼还怀着敬畏和恐惧,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狼的形象衍生出不详的意蕴,甚至隐喻的是遭人恐惧而唾弃的封建时代。《祝福》中祥林嫂这样讲,“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向,都没有。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狼是什么,为什么祥林嫂只知道春天会有狼,却不知道冬天也会有狼,那是因为隐喻封建制度的狼是无时无刻不存在,在这种制度之下,无力反抗的人只能被旧时代所埋葬。
于鲁迅自身来说,充满野性的狼也是对自己的隐喻。那个时代好似无垠的荒凉之地,一匹伤痕累累却拼命奔向远方的狼,它孤独地舔舐身上的伤口,双目却依然凌厉地望向远方不尽的终点,它不知是否能到达,但它脚下的步伐依旧迅捷,远远的将狩猎者抛在身后。作为革命思想的先行者,鲁迅已经具备了超越时代的意义,他用锋利的爪子撕破旧时代的伪装,让人们看到它面目可憎的样子,他以笔为枪,惊醒了企图在沉默中灭亡的人民。
五、斗争之外的生命柔情情怀
鲁迅始终保持着对生命的尊重,在《兔与猫》中表现了对兔子的喜爱,而当黑猫吃了兔子的幼仔之后,鲁迅又发出“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的失意之叹。鲁迅一面对黑猫深恶痛觉,一面又哀叹孱弱的兔子的不幸,这一现象的隐喻基于当时列强侵占中国的历史,以此来唤醒中国人民民族意识。
《鸭的喜剧》中,喜爱小动物的爱罗先珂买来小蝌蚪,之后他又买来小鸡、小鸭,但是不久后,小鸭子却将小蝌蚪都吃掉了。这些小动物展现出不同于以往作品的“稚气”,读此文章,忽而感到心境愉悦,仿佛身处其中,与之玩耍。在《鸭的喜剧》中的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与“《兔和猫》中的不同,因此鲁迅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认为这是自然条件下的法则,弱肉强食的环境之下更多的是新生命的希冀。
六、人兽纠葛之下思考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3]。鲁迅是以兽来象征人,以动物界来隐喻整个人类社会,以一种诙谐的方式来激发国民性的思考。人类思维的丰富性造就了行为的复杂性,因此在行动的时候会考虑到诸多因素,而在动物界,一切行为的执行都是直率而简单的,人类无法认识到自己身上所反映某种问题,当把视角转移到动物之上,用物域来映射人域,视角将会变得更加清晰。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与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人不可能对照动物来生存,文明不可能退化至蛮荒,人性存在着原始的淳朴与野性,也具有了时代进化后的七情六欲,在那个封建礼教与战乱横行的旧时代,许多人逼不得已只能如“苍蝇”一样苟活,只能像“叭儿狗”一样依仗而存,甚至还会成为“狼”的帮凶,没有一个人不想掌控自己的命运,可于他们来说,那个时代远比我们想象的险恶,奋起抗争的有冲破桎梏的幸存者,但也有倒在血坡中的牺牲者,时代逼着他们作出选择,只要生存得下去,善恶之间的界限也已变得模糊。
结束语
隐喻的手法在鲁迅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一种写作的技巧,它更是一种艺术性思维的体现,著名学者李欧梵就认为:“我想把鲁迅早期杂文这种独特的方面称为`隐喻方式,这就是一种通过可以加强文章内容寓意广度的形象和警句来表达非系统思想的形式。因为,由此而达到的抽象程度,是可以使那些形象变成暗含复杂层次意义的隐喻的”。这就是艺术性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独特的魅力。
參考文献:
[1]保罗·利科.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罗一丽.动物隐喻文献综述[J].科技信息,2014(04):285.
[3]《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施雯(1998.10-)女,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学历:江苏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