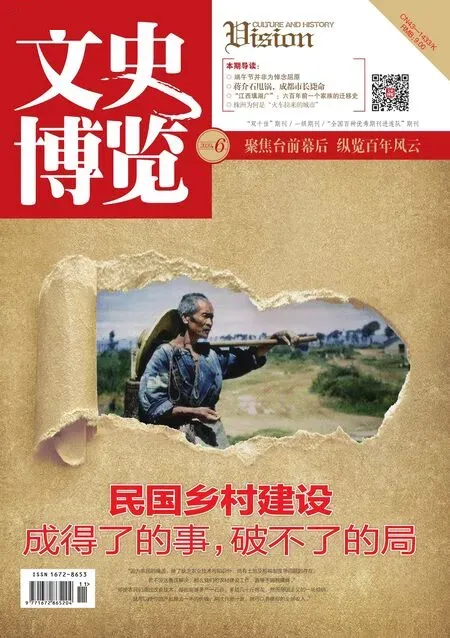曾国藩家族战“痘”记
2020年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并影响全国。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阻击疫情,谱写了人类抗击恶性传染病的新篇章。
恶性传染病自古有之,天花即是其一。天花是由病毒感染所致的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急性危重出疹性疾病,中医称为“痘疹”。明清时期,痘疹造成婴幼儿甚至青少年大量死亡,其猖獗令人谈之色变。乾隆年间,和邦额在《夜谭随录》中描述:“自是小儿多患痘疹,百无一生。”可以说,那时候养儿育女的家庭,没有哪家不会遭遇痘疹,曾国藩家族也不例外。
《曾国藩年谱》载: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乡里天行痘症大作,公季妹及子桢第皆染痘殇。“天行痘”是天花的另一种称呼,曾国藩的满妹和儿子又是怎样染上天花去世的呢?我们可以从《曾国藩日记》中寻找答案。
这年新春,新科进士曾国藩在年前乞假回家,由于“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荣耀归乡的他在新年伊始,便开始用日记记录自己的生活。翻开曾国藩日记,其开篇便是:“初一日,家居,季洪弟受风寒。”

曾纪泽
季洪弟即曾国藩五兄弟中最幼者曾国葆,年前刚满10岁。由于天花病毒主要是通过飞沫吸入或直接接触而传染,初期症状会表现为寒颤、高热、乏力、头痛、四肢及腰背部酸痛, 三至五天后患者的额部、面颊、腕、臂、躯干和下肢会出现红色斑疹,故起初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伤风受寒,未料是感染了天花病毒,初四日曾国葆出现了皮疹,曾国藩日记中谓之“季洪弟自来痘”,乃这个春节曾氏家族的第一例感染者。曾国葆病情发展如何,又是如何治疗的,曾国藩日记其后没有记载。但按明太医院医官龚信所著《古今医鉴》之“发热三朝决生死例”,痘疹“发热时,身无大热,腹痛腰不痛,过三日后才生红点,坚硬碍手者,勿药有生,所谓吉证”,曾国葆为大年初一发热、三日后现痘,可以判定是轻症患者,容易痊愈。
由于天花病毒传染性极强,旧时民谚也有称:“生娃只一半,出花才算全。”既然曾国葆染病,家里其余幼童也难以逃脱感染。可能是出于对国葆“出花”的乐观评估,根据曾国藩日记,笔者推测曾家请医者对九弟曾国荃(字沅甫,号叔淳)、满妹及桢第(曾国藩长子)实施了“人痘接种”。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
家中种痘者,满妹痘不好,甚危急;叔淳弟初发现,尚好;儿子未发热。夜着刘一、王荆七走刘冠群家,请医弟、妹。
所谓“种痘”,即为“人痘接种术”,这是古人按照以毒攻毒的治疗思路,通过接种天花患者的痘疹泡浆、痘痂等,期待出一次轻微天花而获得终生免疫。种痘方法很多,我们无从得知曾氏家族采取的是哪种方法,但“人痘接种术”本质上是将被动感染变为主动感染,依然具有相当的危险性。种痘后,除了满妹“痘不好,甚危急”,儿子桢第也非常不乐观。正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日记:
昨夜儿子发热,本日现痘不甚多。发热必三日始现痘为佳,兹仅发热一夜,非吉报也。
家中种痘后的“光景不好”,事关三位骨肉至亲,曾国藩痛心牵挂,几次延后赴友人朱尧阶家,全心陪护。虽经极力医治,但满妹、儿子病情依然持续恶化,曾国藩“心知不可救药,犹冀幸万一”。正月二十九日辰刻,满妹死,临死之前“遍呼家中人”,却“独不呼桢第”,“知其危也”。第二日上午,桢第亦亡。不幸中万幸的是,九弟曾国荃种痘后虽也有“甚危”之时,却总算是熬过这一关,“痘渐落痂”。
两日内痛失满妹与儿子,给曾国藩带来的不仅仅是失去骨肉至亲的悲伤,还让他对“死神的忠实帮凶”天花病毒有了高度的戒备。身为京官的曾国藩很快就关注到了“牛痘接种术”这一新生事物,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二十七日,他在禀祖父书中写道:
曾孙兄妹二人体甚好,四月二十三日已种牛痘。牛痘万无一失,系广东京官设局济活贫家婴儿,不取一钱。兹附回种法一张,敬呈慈览。湘潭、长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乡间无人知之。
曾国藩向祖父禀报,3岁的曾纪泽和仅5个多月的曾纪静都已接种牛痘。为免家中长辈担心悲剧重演,他还特地说明,牛痘“万无一失”,并随信附回牛痘接种方法。
1796年,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1749—1823)发现挤奶女工感染牛痘后不染天花,尝试用牛痘疱浆替代人痘获得成功。与人痘接种术相比,牛痘接种术毒性更低、效果更稳定,嘉庆十年(1805)传入中国后很快普及各地。担任顺天府尹的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望颜在北京南海会馆设立“京都牛痘局”,免费接种牛痘,“以此为济世之举”。
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再次向祖父禀报:“曾孙兄妹二人种痘后,现花极佳,男种六颗出五颗,女种四颗出三颗,并皆清吉。”此后,次女曾纪耀、三女曾纪琛、四女曾纪纯出生,曾国藩依然为她们接种了牛痘。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月十八日,曾国藩告知父母:“一男四女,痘后都好。”
或许是因为戎马倥偬,无暇顾及,曾国藩也有百密一疏,次子曾纪鸿出生后没有及时接种牛痘。同治六年(1867),20岁的曾纪鸿携娇妻幼子与母兄返湘住老家富厚堂新宅,自己随侍父亲身边。三月十四日,在金陵城里一心备考的曾纪鸿突然发病。
曾纪鸿生病,曾国藩虽然焦虑,却以为只是因考试用心太过,而“体弱生疾”。十九日,曾纪鸿“遍身疹子发得极满”,请医诊断,方知“乃天花痘喜也”。曾国藩闻之尤为忧灼,深悔前四日半用药“无一不误”,旋请痘科老医生刘蔚堂前来治疗。傍夕,又择净室敬奉痘神,亲自沐浴拈香行礼。是夜,忧心忡忡的曾国藩夜不成寐,下半夜竟披衣“至其窗下潜听”,曾纪鸿“气息尚匀”,方得慰怀。
二十日,曾纪鸿之痘“甚险”,甚至饮食不进,药水难入。曾国藩不仅闭门谢客,一贯勤于政事的他在核批公文时都是草草了事,“余则绕室彷徨”。好在医者精湛,治疗得当,曾纪鸿病情大有转机。二十二日,曾氏幕僚、书友莫友芝问曾纪鸿病情,答“可无虑也”。二十八日,曾国藩日记载:
是日,鸿儿痘症平顺如常。食粥四次,凡二十碗,燕窝比昨日减一次,未服人参,换以洋参,肉汤、鸭汤均能食其精者,痘痂亦落十之一二。此次由至险而得至安,实初意所不到。一则赖痘神祐助,一则刘叟之老练精慎,叶亭之劳苦维持,均难得也。
曾纪鸿体质较弱,加之没有及时对症下药,痊愈过程缓慢,至四月初十日,“将满一月而面痂尚有一半未脱”。五月十六日,应曾国藩之邀在金陵书局校勘书籍的张文虎入督署办事,他看到的曾纪鸿“痘后满面胡麻矣”。此“胡麻”即天花发病痊愈后留下的瘢痕,俗称“麻斑”,清朝十二帝中侥幸从天花魔爪下捡回性命的康熙和咸丰,也是麻子脸。
儿子曾纪鸿罹患天花,一向稳重的曾国藩也是惶恐失措。自三月十四日发病至四月十二日能够下床坐谈,从曾氏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每天对曾纪鸿的饮食起居无不仔细关注。其舐犊情深固然令人动容,但之前满妹、长子因痘而殇,却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曾国藩平日笃信祖父不信巫道之教,当儿子经此痘患无恙之时,也是无比感恩“痘神祐助”。四月初八日,曾国藩作祭文“四言三十二句”,以金陵之俗礼送痘神。还于祝文中许以两千金修痘神庙,“保金陵城内男女永无痘灾”。九月庙成,曾国藩撰联:
善果证前因,愿斯世无灾无害;拈花参妙谛,惟神功能发能收。
曾纪鸿患病之时,正是江南战乱之后,为了便于炖人参、燕窝给他进补身体,身边的戈什哈(侍从护卫)打造了一把银壶,费银八两多。曾国藩得知深为愧悔,在日记中痛骂一番:“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除了反思为“鸿儿痘症用钱太多”,曾国藩还检讨自己为儿子的操心费力远过于对父母的关爱,恐遭“薄孝厚慈”讥评。
作为传统封建士大夫的曾国藩,对病疫的认知固然有其蒙昧迷信的一面,但他对病疫始终保持恭敬谨慎的态度,对于今人看待疫情、处理危机,还是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当面对亲人为疫病侵袭时,无论是他归功“痘神祐助”的蒙昧,还是“用钱太多”的自省,皆是源自他内心的家庭担当,还有情感上对待亲人那种无法脱离世俗的脉脉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