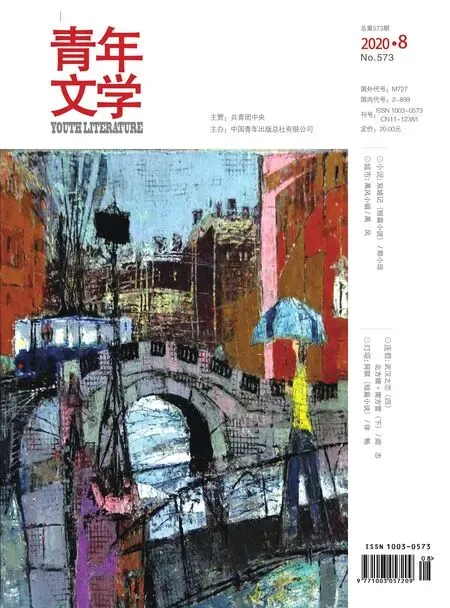世间已无冉阿让
编者按
本次的《雅座》,由蔡骏老师带领读者朋友们品读《悲惨世界》。这部由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一八六二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多次被改编为歌剧、电影,广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在创作日趋成熟之后,小说家们常常会有意识地对写作技巧和写作理念进行总结。作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悬疑作家之一,蔡骏也完成了这种自我总结,在过去半年内接连出版了《蔡骏24 堂写作课》《故事写作》两部与写作相关的书籍。
通过阅读本篇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蔡骏在文学创作中的思想脉络,以及他对当前阅读环境的反思。当下种种新的媒体形式日益兴起,人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切割。在海量的信息之间,在无数“爽感”的冲击之下,什么才是更应当被不断反刍的?愿与读者共同反思。
(修新羽)
一
今年冬天,全中国人困于疫情,足不出户的时光里,我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戴珍珠耳环的淑芬》。这小说基本是我的半自传,其中一段,是我小时光真实的阅读经历——
我家里藏书,多是我妈妈老早买的小说,文学期刊如《收获》《当代》《人民文学》,华师大中文系自学考试教科书如《古汉语概论》《中外比较文学》,还有我爸爸的养花指南,他当兵时的防核武器跟生化武器手册,统统藏了壁橱底下,被我一本本翻出来,摊开来晒太阳,家里洋溢了反帝反修、批林批孔、儒法斗争、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丰富且吊诡气味。曾经让我如痴如醉的三百本连环画,已被它们的小主人束之高阁。这是我一生当中的青铜时代,等于古埃及在尼罗河,古巴比伦在两河流域,古印度在印度河,商朝人在殷墟的甲鱼壳上刻字的阶段。《水浒传》宋江招安后征辽国讨田虎平王庆擒方腊后三十回,我读了十遍;《悲惨世界》第二卷滑铁卢战役,我读了二十遍;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我读了三十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读了四十遍。我外公常常摊开文稿纸,捏了狼毫笔,抖抖豁豁抄写,不是佛经,不是唐诗宋词,而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不是原著文言文,而是后人译的白话文,这样外公才看得懂。《聊斋》故事,三分之一美艳女鬼,三分之一仙侠狐妖,三分之一市井无赖,我欢喜看打打杀杀,比方《田七郎》,我外公抄过三遍,田七郎为好兄弟报仇,杀了御史阿弟,再自杀,再尸变,杀了县官,看得我汗毛凛凛。
而给我印象最深,至今都难忘怀的,还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书中一个叫冉阿让的男人。坦率而言,十八岁以前的孩子是无法看懂这本书的,哪怕你长到二十八岁,恐怕也只是在字面意义上读懂了《悲惨世界》,若要从灵魂层面深入到本书,三十八岁或者四十八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理解的世界,你所经历的生活。尽管,我们无从再经历一遍十九世纪,但在我们身边依然可以看到芳汀,看到珂赛特,看到马吕斯,甚至沙威警长与德纳第夫妇。
可你见过冉阿让吗?
二
《悲惨世界》是这样开始的:一八一五年,冉阿让从被关押了十九年的苦役中释放。他来到狄涅城中,没人愿意收留他过夜,哪怕狗窝都进不去,主教米里哀先生收留了他,邀他共进晚餐,还为他铺了一张洁白的床过夜。这是冉阿让十九年来第一次睡床。半夜里,冉阿让却偷走了主教家里一套值钱的银器,刚逃出去不久便被警察抓住。警察带着冉阿让来到主教家,米里哀却说,那些银器是他送给冉阿让的,还说冉阿让忘了带走一对银烛台,警察只得将冉阿让释放。主教对冉阿让说:“不要忘记,您拿了这些银子,是为了去做一个诚实人”。
为什么,一个堂堂的主教(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主教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与权力),要为拯救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偷而向警察做伪证?因为他知道,如果为了法律的正义,要把小偷交给警察,冉阿让必然又会坐牢。或许,雨果写得过分美好,过分强调人类弃恶从善的天性——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法律更有效的约束是道德,比道德更有效的约束是信仰,法律只能约束一个人的行为,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内心,法律可以把一个罪犯关进监狱让他不再危害社会,但法律不会保证这个人被放出监狱以后不再危害社会。当时法国的司法制度,不可能感化一个罪犯,只可能使罪犯在坐牢过程中更加危险和仇恨社会,结果是毁灭一个人而不会拯救一个人。道德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道德的力量有些薄弱,最有效的力量则是信仰,只有信仰才能深刻影响一个人的心灵,从心灵深处约束人的行为。
主教选择了信仰,选择了道德,抛弃了法律,他为了信仰和道德做了伪证,不仅仅是拯救了冉阿让不再被关进监狱,更重要的是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若没有米里哀主教做的这个伪证,芳汀可怜的女儿珂赛特也不可能获救,或许这个小女孩将永远在小旅馆里暗无天日地长大直到无声无息地死去。米里哀不但救了一个人,而且间接地救了好多人。
主教拯救冉阿让并非随意地施舍,因为自己也要付出代价。因为天主教徒,尤其是天主教的主教,撒谎和不诚实是一桩很大的罪过,主教宁愿由自己来承担罪过,也要拯救并改变一个人的灵魂。他以违背某种信仰的代价,来实现了信仰中的一个更高的准则,那就是牺牲自己拯救他人。
可是,现代人已经无法理解十九世纪,更无法理解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我们只看到自己的生活,也只关心自己的生活,看不到自己身边大多数人的生活,看不到一个虽然残酷却近在眼前的现实,雨果所说的十九世纪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这三大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暴力可以暂时压制暴力,但无法永远控制暴力,因为千千万万人的暴力,相加起来永远会超过少数人的暴力。所以,米里哀主教放弃了警察的暴力,而选择了他自己的方式,用宽恕对待仇恨,用给予对待窃取。我们可以说他是妇人之仁,也可以说他会姑息养奸,但不能怀疑他有一颗虔诚善良的心。
暂且不把米里哀主教归入圣贤一列,只当他仍然是个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那么看看我们这些平凡人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冉阿让是个身无分文之人,一套偷来的银器是他全部的财产,米里哀主教想必衣食无忧,一套银器可能只占据他的财富的千分之一,损失自己的千分之一,来拯救一个人全部的命运,对自己来说无关痛痒,对那个人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米里哀主教用自己的千分之一换来了另一个人生命的全部。
三
《悲惨世界》是一部充满“闲笔”的巨著。
每次中国城市内涝成灾,就会有人提出雨果老爹的名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没错,这确实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一章“利维坦的肚场”中所说。译本中却不是下水道,而是“阴渠”(因为这两个字,网上许多版本是被和谐的)——
阴渠,就是城市的良心。
人类的历史反映在阴渠的历史中。古罗马罪犯尸体示众场叙述了罗马的历史。巴黎的阴渠是一个可怕的老家伙,它曾是坟墓,它曾是避难所。罪恶、智慧、社会上的抗议、信仰自由、思想、盗窃,一切人类法律所追究的或曾追究过的都曾藏在这洞里;十四世纪巴黎的持槌抗税者,十五世纪沿路拦劫的强盗,十六世纪蒙难的新教徒,十七世纪的莫兰集团,十八世纪的烧足匪徒都藏在里面。一百年前,夜间行凶者从那儿出来,碰到危险的小偷又溜了回去;树林中有岩穴,巴黎就有阴渠。乞丐,即高卢的流氓,把阴渠当作圣迹区,到了晚上,他们奸猾又凶狠,钻进位于莫布埃街的进出口,好似退入帷幕之中。
对巴黎下水道的展现,在许多个电影版的《悲惨世界》中都是最精彩的段落之一。以至于我小时候认为每个城市的下水道都如此宏大,密如蛛网,在我们的脚底下还有另一个世界,也许还生活着另外一群人。我在二〇一九年写完的长篇小说《春夜》中,便有一个在巴黎的梦,来自雨果笔下的巴黎下水道。
童年时第一次阅读《悲惨世界》,我津津有味地读完了关于滑铁卢战役的那一段(估计写了五六万字)——几乎跟小说主要情节毫无关系,没有冉阿让,没有芳汀,没有珂赛特,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历史学。我读到雨果事无巨细地描述战争细节,纪录片一般重返战场甚至在残垣断壁上找寻累累弹痕,描述战争双方的拿破仑与威灵顿公爵,描述法国胸甲骑兵呼喊“皇帝万岁”,气吞万里如虎,视死如归地冲向那道致命壕沟,顷刻间千万须髯男儿,在英军的铅弹、刺刀面前化为一腔英雄血……
那是任何电影镜头都无法表达的效果,值得在我脑海中重演无数遍。哪怕日后我看了邦达尔丘克导演在一九七〇年拍摄的《滑铁卢战役》那史诗般的冲锋画面,在电影界几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许电影版《战争与和平》能与之比拟,据说《滑铁卢战役》就是用了《战争与和平》剩余的道具物资拍摄的),但比之雨果老爹留下的文字,那也不过是九牛一毛。然后是滑铁卢战役后的那一夜,作为神的拿破仑轰然倒塌,在战场上偷窃死人财物的德纳第出场,死里逃生的马吕斯的爸爸出场……
今天的小说家,如果写上这么大段数万字,并与主线故事无关,大概要被读者骂作骗字数骗稿费,也会被评论家贬为无意义的“闲笔”吧。
去年,我跟一位如今活跃的纯文学作家认真讨论过这个问题,达成的共识是:今天的小说家不是不能这样写,而是没有能力这样写。也不是今天的小说家丧失了这种能力,而是我们所处的语境剥夺了我们的这种能力。
四
不但作家被剥夺了能力,就连读者的能力都被剥夺了。
再举雨果的另一部历史巨著《九三年》,有这么一段——
炮队里一尊二十四磅重弹的大炮滑脱了。也许这是海上事故中最可怕的一种。对于一只正在大海中行驶的军舰,没有更可怕的事变了。这尊挣断了铁链的大炮,突然变成了一头形容不出的怪兽;也就是说,一架机器变成了一只怪物。这件沉重的物体用它的滑轮走着,像一只弹子球似的滚来滚去,船身左右摇动的时候就侧下来,船身前后颠腾的时候就沉下去,滚过去,滚回来,停顿,仿佛沉思一阵,又继续滚动,像一支箭似的从船的一端射到另一端,旋转,闪避,脱逃,停顿,冲撞,击破,杀害,歼灭。这是一只撞城槌在任性地冲撞一垛墙。还得加上一句:这只撞城槌是铁制的,这垛墙却是木头的。这是物质获得了自由,也可以说这是永恒的奴隶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切仿佛是隐藏在我们所谓无生命的物体里的那种恶性突然爆发了出来;它那样子像是发了脾气,正在进行一种古怪的神秘的报复;再也没有比这种无生命物的愤怒更无情的了。这个疯狂的庞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灵巧、斧子的坚硬、波浪的突然、闪电的迅速、坟墓的痴聋。它重一万磅,却像小孩的皮球似的跳弹起来。它旋转着的时候会突然转一个直角。怎么办呢?怎样解决呢?暴雨可以停止,台风会吹过去,断掉的桅可以换一根,一个漏洞可以堵上,火灾可以扑灭;可是对这只庞大的青铜兽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来制伏它呢?你可以驯服一只恶狗,吓唬一头牡牛,诱骗一条蟒蛇,威胁一只老虎,软化一只狮子;可是对这样一个怪物——一尊脱了链的大炮——却没有办法。你不能够杀死它,它是死的。同时它也活着。它的不祥的生命是从无限里来的。它的底下有甲板在摇动它。它被船摇动,船被海摇动,海被风摇动。这个破坏者只是一只玩具。船、波浪、风,这一切在玩弄它;这就是它的不祥的生命的来源。
你能读完吗?
你可能在上班的地铁上,在工作和读书的间隙,在饭局刷手机的时候,或者在马桶上,看到前三句话就放弃或者跳过。
你也可能在漆黑的深夜,或在阳光灿烂的午后,在幽冥与炫目之中,一字一句地读完这段文字,少一个字不行,多一个字也不成,比如——前进,后退,撞到右边,撞到左边,逃避,冲过……
你仿佛来到两百年前的欧洲,一七九三年的英吉利海峡(法国人叫拉芒什海峡),那是海军提督纳尔逊的年代,那是青年拿破仑在土伦血战的年代。
这是你的三生有幸。
这不仅是小说,不仅是历史。你就像看到一张张照片,看到一段用视觉、听觉、嗅觉甚至味觉与触觉构成的虚拟现实游戏,或者一场主题乐园的冒险,乃至于乘坐时空穿梭机的旅行。
这是《九三年》,雨果的巅峰之作,比起《悲惨世界》只高不低,相比较那个时代的巨著们,并不算长。
你能读完吗?
时至今日,我并不觉得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巨匠们能超过雨果老爹。
尤为悲剧的是(正如《悲惨世界》之名),我们失去了有能力的作家,失去了有能力的读者,也失去了有能力的主人公,无论在小说还是在现实中。
五
二〇一五年,我写过一部短篇小说《眼泪石》。故事来源于一个真实新闻,某个少女能流出石头般的眼泪,后来送到医院检查,确认是某种眼结石。我便把这少女写成一个农村留守儿童,母亲也像芳汀一样在东莞从事某种行业,她孤苦伶仃地来到上海投靠舅舅一家开的四川麻辣烫小店。女孩没怎么读过书,唯一读过的便是城里人捐献给乡村小学的一套《悲惨世界》。这本书她读过无数遍,无论是否能读懂,她已把自己当作了珂赛特,把舅舅和舅妈开的麻辣烫小店,当作德纳第小酒馆,把妈妈当作芳汀,把街对面小区的保安当作沙威警长,把停在上海街头的汽车当作欧洲的四轮马车,把二十一世纪初的上海当作十九世纪的法国……而她唯一的朋友是作家“我”。每次当她悲伤或者思念妈妈,便会流出珍珠般的固体眼泪。有一回,有人拍摄了会流宝石眼泪的女孩的视频传到网上,她迅速成为网红,人们高价求购她的眼泪,认为是某种稀世珠宝。舅舅与舅妈还把她的泪水放到网店售卖,甚至加以虐待逼她落泪以获得宝石。经过一番风波,“我”终于解救了女孩,带她去医院做了眼结石切除手术,从此再无眼泪石,也再无珂赛特。若干年后,等到作家“我”与女孩重逢,她早已被世风同化,遗忘了《悲惨世界》的故事。她等待了一生的冉阿让,始终未曾出现过。
这篇小说后来获得了郁达夫小说奖入围奖。还有评论家说过《眼泪石》与《悲惨世界》的互文性,老实说,我并不懂何为“互文性”。我仅仅把这故事当作一个都市童话,当作《悲惨世界》的同人文。我既是故事中的作家“我”,何尝不是那个寻觅着冉阿让的珂赛特?
请原谅我,毫不讳言,我依然深爱着雨果老爹,深爱着《悲惨世界》,深爱着那个叫珂赛特的小女孩,深爱着那个叫冉阿让的男人。
世间已无冉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