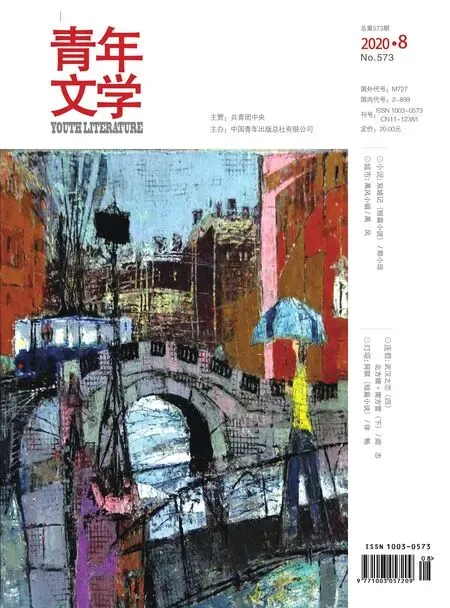凉 亭
吃过早饭,严东生下了楼,出了小区向北,过了红绿灯向西走了五百米,来到那座叫作永乐的街心公园。街心公园不算大,却有山有水,有花有树。附近居民都喜欢到这里来,尤其是那些退了休没事儿干的老年人,没了单位的管束,更是乐此不疲。公园里打太极拳的、跳广场舞的、跳水兵舞的、玩扑克的……大伙成群结伙聚在一起,公园一下子热闹起来。
严东生径直走向公园南侧的山丘,顺着台阶向上走了不到七分钟就到了山顶的凉亭。凉亭是仿古的四角凉亭,上覆琉璃瓦,飞檐上卧着麒麟。那几个唱京戏的还没来,严东生在亭子东侧的座位上坐下,这个位置他坐了五年,五年雷打不动,谁也休想让他离开这个位置。
凉亭居高临下,跟下面的聒噪相比,显得清静了许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几个唱京戏的票友也喜欢上了这个凉亭。那天他们上来的时候,严东生正靠着柱子坐在长凳上,半闭着眼悠闲地晒太阳。几个唱京戏的人走上来,瞥一眼严东生,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一个白胖的老头来到严东生跟前咳嗽一声,示意他起来给自己腾个地方。严东生没理会,仍旧微闭着眼。
嗐嗐,起来点,别一个人占着一条长凳,这不是你家的床。见严东生装作看不见,白胖老头不高兴了。
严东生说,问路还得叫声老乡呢,何况什么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严东生睁开眼,斜睖胖老头一眼,一副带搭不理的样子。
嘿,你这人,把公共座位占为己有,你还有理了?白胖老头挨了呛,有些恼,还想说什么被同来的几个人扯到一边。什么人呢!白胖老头嘟囔了一句。
吱吱呀呀杂乱的乐器声响了起来,杂乱过后正式“演出”的是《贵妃醉酒》。严东生斜眼打量那几个人,两个拉二胡的,一个是干瘪老头,看模样有七十多岁。另一个瘦高的老头年轻些,也得有六十多岁了。和他争吵的那位白胖子看上去也得有六十岁,他拉三弦。站在中间的大脸女人,是唱青衣的。另一个戴眼镜的中等个头的男人,虽然显得文绉绉的,但实际年龄跟白胖老头差不多,只不过看上去显得年轻些。眼镜男人手里没有什么乐器,想必不是唱老生就是小生,果然大脸女人唱过,他唱起了《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坦白讲,除了拉二胡的那个干瘪老头胡儿拉得不错,其余几个纯业余水平,就是凑在一起寻开心。
严东生闭上眼假寐。
严东生想起很多年前的四月,绿肥红瘦,草长莺飞,他骑着老式自行车,前面车梁上坐着春风拂面的陆小词,严东生向前俯着身子,这样瘦小的陆小词整个人便依偎在了他怀里。严东生轻微的气息吹得陆小词耳边痒痒的,禁不住扭过头去,在严东生脸上鸡啄米一样啄了一下。从县城到陆小词的家不过十里路,这十里路,两个人走得卿卿我我。
真是晦气,大脸女人唱《大登殿》没唱两句,白胖老头的弦就断了一根。老张你说说你,来之前让你查查家伙,你说没事,这多扫兴。干瘪老头脸上露出了不悦。前些天还使来着,谁知道今天会发生这事?怪我今儿出门没看皇历,倒霉。被称作老张的白胖老头扫了大伙儿的兴,脸上挂不住,扭过头去狠狠瞪了严东生一眼,将不满怪罪到严东生身上,好像他的琴弦是严东生给扯断的。
算了,算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干瘪老头说着收起二胡,明天再来吧。
看着几个人背起家伙下了山,严东生站起身,站在凉亭下放开嗓子唱了起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
这一天,严东生又去了街心公园,在亭子下坐了不到半个时辰,那几个唱戏的就进了亭子。只是几个人里少了上次那个瘦高的老头,而且瘦高老头出现过一次之后再没出现。严东生后来从几个人的聊天中才知道瘦高老头的妻子病了,在家照看妻子出不来。像往常一样,他们谁都没有搭理严东生,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坐下来,调琴、开嗓。大脸女人坐在一旁,旁若无人地对着镜子涂口红,好像她的舞台不是一个亭子,而是一个偌大的戏剧舞台,不打扮满意了对不起台下的观众。严东生看一眼大脸女人,拉弦的、被称作老张的白胖男人,便使劲咳嗽了一声,好像严东生是坏人,要把女人勾走似的。严东生在心里不屑地哼一声,将双手支在脑后,阳光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
一切准备就绪,先是大脸女人唱《锁麟囊》片段,接下去是眼镜男人唱《三家店》,干瘪老头的二胡刚欲拉起,这时,眼镜男人的电话哇啦哇啦响了起来。这是谁呀?眼镜男人掏出手机,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干瘪老头的二胡便停了下来。眼镜男人摁了收听键,打电话来的是个女人,女人满腔怒火,声音很大。严东生佯装望着远处,竖起耳朵,就听电话里女人说,窦满意,你管不管你家老爷子?他现在开始拿砖头砍我了,我这日子没法过了,你再不管我就去法院告你们。
我家老爷子没在我班上,这月在老二班上,你该找老二才对。被唤作窦满意的眼镜男人对着手机说。
你以为我没找?找了,你家老二不管,我才找你。你们要是都不管,我就到法院告你们。
好好,我知道了,你消消气,回头我找老二谈谈。眼镜男人挂了电话。
你说我这个爹呀,可让我怎么好?眼镜男人挂了电话一脸的无可奈何。
你家老爷子怎么了?见眼镜男人无奈的样子,干瘪老头忘了手中要拉的二胡,关切地问。眼镜男人叹口气,不顾严东生这个外人的存在,禁不住向众人诉起了苦衷。一旁的严东生,像个名正言顺的偷窥者,窥听着眼镜男人的家事。
刚才打电话的女人是眼镜男人老家的邻居,自从眼镜男人把在老家和父亲共同居住的残疾弟弟送到敬老院后,八十多岁的老爹就不断走失,后来摔伤过,才不走了,但开始闹。没想到老爷子越闹越欢,跟女邻居较上了劲,不管黑天白天,只要睁着眼就上邻居家敲门,说女邻居把他的残疾儿子藏了起来。女邻居不让他进门,老爷子就破口大骂。
你家老爷子,是想你的残疾弟弟了,带他去敬老院看看就好了。干瘪老头说。
谁说没带他去看,看过,每次去,到了那儿就闹,谁还敢带他去?
要我说,你就不该把你弟弟送走,两人在一块生活一辈子了,你把他送走了,老爷子能干?大脸女人插话说。
我不送走,有什么辙,伺候一个老爹,再伺候一个残疾弟弟,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就是我答应不送走,我媳妇和老二两口子也不会答应。
眼镜男人话音一落,本来干瘪老头已经准备拉弦了,谁知白胖老头又接了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完,他转向大脸女人问,你家怎么样了?媳妇还不让你见孙子?大脸女人见白胖男人问自己,无所谓地说,不让见,让她妈看吧,眼下不是时兴丈母娘看孩子吗,这样更好,我还自由呢,想干吗干吗,要是整天看孙子,我想唱戏了,我出得来吗?
你也就说说,放着大胖孙子见不着,你心里能不闹得慌?眼镜男人接话说,要我说,你也是自找,当初要不去俄罗斯不就没这事了。
我去俄罗斯怎么了?我去俄罗斯是她没生孩子前就定好了的,机票早就买好了,大脸女人被戳到短处,有些急赤白脸。
几个人你来我往,完全无视严东生的存在,使得严东生无意之中又窥听了大脸女人的家事。
大脸女人跟儿媳的矛盾源自她的俄罗斯之行,她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正赶上儿媳妇要生孩子,她丢下些钱,就按计划去旅游了,等她从俄罗斯旅游回来,孙子快出满月了。因为婆婆没照顾女儿坐月子,丈母娘怨声载道,在女儿面前尽数婆婆的不是。女儿受了母亲情绪的传染,一怒之下,和婆婆开始抗争,不光不让婆婆看孩子,而且连孩子的面也不让婆婆见。
她不让我见,我还不想见呢,眼珠子都指不上,还能指上眼眶子?老娘把家产吃光花光,一分钱也不给他们留。大脸女人愤愤地看着众人,仿佛众人都招惹了她。
瞧瞧,我这一句话,惹得你生这么大气,我这嘴真欠,别生气,别生气。白胖男人本是好意,想讨好关心一下大脸女人,没想到竟惹得大脸女人一阵愤怒,赶忙向大脸女人赔不是。
大脸女人瞪了白胖男人一眼,并不领情。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瞧你一个电话招出这些事,干瘪老头用手指了指眼镜男人,转头对大脸女人说,你先消消气,我们先给满意拉一段《定军山》。
来,我先唱,眼镜男人附和着。
大脸女人没说话,人还在愤怒里。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天助黄忠成功劳,站在营门高声叫,大小儿郎听根苗……。眼镜男人随着二胡声唱了起来。
眼镜男人唱的时候,严东生睃见白胖男人一个劲地用眼神讨好大脸女人,大脸女人却视而不见,白胖男人只得讪讪地收回目光。
给我拉一段《秦香莲》,眼镜男人唱罢,大脸女人对干瘪老头说。
大脸女人的《秦香莲》唱得悲悲切切,仿佛她唱的不是被丈夫抛弃的秦香莲,而是被儿子儿媳抛弃的自己。
始终被众人忽视,却一直支着耳朵听故事的严东生,听到女人凄凄惨惨的唱腔,不禁一蹙额,他环顾了一下亭子里的人,当看到白胖男人的时候,男人冷漠地跟他对视了一眼,瞬间将目光停留在手里的琴弦上。自从头一天跟白胖男人发生口角,白胖男人就一直对他充满敌意。
秦香莲凄苦的唱腔,让他无法忍受。严东生站起来,悄悄下了山,这要搁往常,严东生是做不到的,他得伸展一下四肢,掸掸衣裤弄出点响动,让几个人听见。而今天,因为无意中知道了令他们苦恼的家事,严东生从心里,蓦然间对这几个人有了一丝亲近。
一路上,严东生想起,很多年前的那天,严东生和陆小词约完会回到家,老婆陶玉新递给他一张检查报告,报告上“宫颈癌”三个字,清清楚楚地像钉子一样戳进严东生的眼睛,严东生愣怔了半天,他不相信,怎么电影里才能发生的巧合会发生在他身上。他和陶玉新结婚快二十年了,虽然感情一般,可这么多年陶玉新为他养儿养老,从没做过什么错事,天天在一个屋子里生活,自己怎么连她病了都不知道?严东生拿着诊断报告问,多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一个月前的事儿,月经老是稀稀拉拉的,我也没在意,后来是我妹妹让我去查查,一查,就这样了。陶玉新说着眼泪落下来。
你怎么这么傻呢?这么大的事你竟然瞒着我?严东生把比他粗壮的陶玉新拉进怀里。陶玉新在他怀里委屈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想告诉你呢,你天天心里长草似的,你心里哪有我呀?我知道你外面有人,我不想知道她是谁,我只想让你多陪陪我,我的时间或许不多了。
一场春雨过后,天气说热就热了,夜里睡觉忘了关窗子,早上醒来严东生有些头痛,吃了片感冒药后,双腿又受惯性驱使走到了街心公园,等他登上亭子,却发现他坐过的地方,躺着一个男人。男人蜷缩着身子背对着他,睡得正香。
你怎么躺在这里睡觉?严东生拍拍男人的屁股,有种圣地被别人侵犯的感觉。
你干吗打我?男人翻过身,严东生才发现原来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你怎么在这儿睡?你家哪儿的?严东生问。
你是警察吗?问这么多干吗?男孩睁开惺忪的睡眼瞧着严东生。
我不是警察,我是问你怎么不回家睡?
你管得着吗?男孩梗着脖子站起来。
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家哪儿的?不用你管,男孩推开严东生,迈开步子往下走,走了几步又回来,上下打量严东生,仰起头说,你看那亭子上面趴着的是什么?严东生顺着男孩的手指望过去,亭子顶部没有什么东西,他正想转过身问男孩看见什么了,却感觉衣兜里一阵骚动,他赶忙用手去捂,钱包瞬间跑到了男孩的手上,等他反应过来,男孩已经冲下了山。
好小子,你竟敢给我使诈,你给我站住!严东生急忙追了下去。
男孩对公园里的路径很熟悉,三绕两绕就跑出了公园。
哎,钱你拿走,把里面的照片还给我。严东生气喘吁吁地追出公园冲着男孩的背影喊。
谁要你的破照片,给你。男孩抽出钱,把严东生的钱包扔了过来。
严东生跑过去,拾起钱包。钱包里他的银行卡、医疗卡、驾驶证都在里边,妻子陶玉新和陆小词的照片也还待在里面,只是六百块钱的零用钱被男孩抽走了三张。严东生把钱包重新放回兜里,站在马路边喘着粗气犹豫着要不要去派出所报案。这孩子没有把钱全拿走,看来不是诚心要偷东西,肯定是饿了。算了,饶了他这一回吧,三百块钱,当是自己弄丢了。严东生在心里自言自语着返回公园。
凉亭上,那几个京戏迷已经来了。严东生走过去,靠着柱子坐下,今天那个唱老生的眼镜男人没有来,由大脸女人“包场”了。严东生上来的时候,她的《霸王别姬》刚开始: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愁舞婆娑……。大脸女人边唱边舞,亭子里空间太小,眨眼就到了严东生面前。严东生别过头,没看女人,眼睛望向山坡上那株花开得正旺的山楂树。
十几年前的这个季节,严东生坐在这里,以同样的姿势,神情落寞地对陆小词说,我们得分开了。陆小词站在严东生的旁边,咬了一下嘴唇说,这么久不见我,今天你把我约到这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
我必须得见你最后一面,当面跟你说清楚,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你坐下,听我跟你说。严东生伸手把陆小词拉到长凳上坐下。在严东生断断续续沉闷的叙述中,陆小词听清了,严东生跟她分手的原因,她低着头沉默良久说,你想分就分吧,回去好好照顾她。陆小词说着站起身。
我也舍不得你,不放心你。严东生一把揽过陆小词,紧紧地把陆小词抱在怀里。陆小词把头放到严东生的肩上,在她目光所及的地方,一树山楂花白得灼了她的眼睛。
再来一段《宇宙锋》吧,一曲唱罢,大脸女人意犹未尽。
再给她拉一段《宇宙锋》,白胖男人讨好地对干瘪老头说。
干瘪老头嗽嗽嗓子,从背包里掏出水杯,或许是杯子里的水太烫,只喝了两口,又放了回去,说了声“走”,乐器又响了起来。
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摇摇摆,摆摇摇,扭捏向前……大脸女人扭扭捏捏的样子,白胖男人看得摇头晃脑眉飞色舞。严东生没心思看大脸女人和白胖男人眉来眼去,他起身下了山。
出了公园,严东生没回家,径直沿着大道向南走,在街上走走停停。开始退休那阵,一个人闲在家,严东生嫌屋子里憋闷,总跑到街上溜达,什么也不买,只是闲逛,有时候能从城西转到城东,再从城东转到城南,走累了就坐在街边的椅子上歇个脚,瞧着街上东来西往的车子发会儿呆,直到肚子里的雷声轰隆隆地打起来才起身回家。街边的门面都做了统一规划,一水儿的大理石镶嵌的墙面,各色的招牌尽职尽责地替商家招揽着过往的行人。往前不到十米的地方,一家新开张的花店,门前铺着红色地毯,一个高绾发髻的女人正招呼着客人。恍惚间严东生觉得女人长得有些像陆小词,不由得紧走几步来到店门前。
大叔,你买什么?迎接他的是一张年轻女孩子的笑脸。
不是。严东生自语道。
你说什么?女孩诧异地问。
没,没什么。严东生有些狼狈地逃离花店。
那是陶玉新病了之后的第八个月,好像也是夏天,严东生在另外一条街上偶然遇到了陆小词,当时陆小词刚从超市出来,手里拎着一袋子水果,四目相对的一刹那,两个人都愣住了。
去超市了?严东生问。
陆小词点点头,随后问,她怎么样?好些了吗?
重了,做了三次化疗了,严东生一脸凝重。
你也多保重,陆小词望了望一脸倦容的严东生,将手里的水果递过来,这个送给她。
你谈朋友了吗?严东生没有接水果,有些犹豫地问。
见了一个,不如意。
如果……如果我说让你等等,行吗?或许她的日子真的不多了。严东生试探地问。
陆小词低下头,半天无语。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有些自私,不该问这话,就当我没说吧。见陆小词不说话,严东生讪讪地说。
进去给我买朵玫瑰花吧,陆小词抬起头,望着斜对面那家正在开张的花店说。
严东生买来了玫瑰,两个人在玫瑰的芬芳中告了别,自从有了那朵玫瑰,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盼着那个日子。可等那个日子真的来了,两个人终于在一起的时候,严东生眼前总出现陶玉新的影子,这个影子阻止着他去亲近陆小词。而陆小词每次和严东生在一起后,心里总会有一种忐忑不安。清醒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一种犯罪感,感觉是他们预谋杀了陶玉新。
溜溜达达的严东生围着县城转了一圈,天黑的时候在外面简单地吃了碗拉面回了家。
夜里,严东生被一阵“咔咔”的啃咬声音惊醒,起初他以为是老鼠,楼下的门脸房是饭店,会不会是饭店的老鼠顺着管道爬上来了?他屏气凝神静听。不对,老鼠啃东西的声音怎么会这么大?他悄悄地下了床,来到门边站了一会儿,声音立刻消失了,等他重新躺到床上,声音又响了起来。他起身拉开屋门来到客厅,把客厅的角落看了一遍,明亮的灯光下,客厅里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怎么回事?难道是自己听力出了问题,还是产生幻觉了?严东生重新疑惑地回到床上。
第二天晚上,他躺床上似睡非睡间,“咔咔”的啃咬声又响了起来。严东生坐起来,侧耳听听,“咔咔”的声音很脆,似在耳边。他下床拉开屋门,来到客厅,什么也没有。他在客厅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床上,等他一回到床上,声音像跟他作对似的,再次响了起来。闹鬼了?他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心想,会不会是陶玉新在那边缺钱花了,来跟自己要钱?缺钱你托个梦不就行了,干吗整这一出?严东生脑子里浮现出陶玉新临死前那张瘦得只剩下一张皮的脸。
不对呀,清明刚给烧的,怎么这么快就花完了?难道是没收到?严东生在心里嘀嘀咕咕的,到底是不是陶玉新?这样想着,严东生下了床。
谁?严东生大声喝问。他小心翼翼地向着刚才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去,靠客厅东墙立着一个大衣柜,那是几年前儿子装修时淘汰下来的。严东生蹑手蹑脚地走近柜子,支起耳朵听了听,柜子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出来,柜子里有人!严东生一惊,随手抄起桌子上的一把茶壶,猛然拉开柜门,随着哐的一声响,蜷缩在柜子里的人球一样滚了出来。
是你?待那“球”爬起来,严东生看清了柜子里的人,竟然是偷他钱包的那个孩子。好小子,你偷了我的钱包,竟然还敢追到我家里来偷,瞧我不收拾你。严东生说着探过身子,伸手想抓住男孩。
哎,我可没偷你东西,我也不是贼,男孩躲闪着跑向桌子的另一端。
不是贼,半夜三更你怎么进来的?
是你没锁门,我跟着你进来的。
没锁门?严东生愣住了,怎么又没锁门?不锁门对严东生来说不是一次两次了。有时候吃了早饭准备出去,走到房门前,发现门一推就开了。至于昨晚怎么没锁门的原因,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
老头,你可真够抠的,冰箱里连点肉都没有,残渣剩饭都几天了,还在冰箱里搁着,害得我只能啃苹果。见严东生不说话,桌子对面的男孩说。
你一个入侵者还挑肥拣瘦的,能有吃的给你就不错了。严东生放下茶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冲男孩招手说,你过来。
你干吗?我不过去,有话隔着桌子说吧。男孩怕严东生使诈。
我问你,你家哪儿的?叫什么名字?看你这乳臭未干的,应该还是学生,怎么不上学,天天在外面游荡?
男孩翻翻眼皮,看了看严东生说,告诉你也无妨,我叫张李阳,就住彩虹新城,我爸嫌我天天打游戏,砸了我的电脑,把我轰出来了。男孩说这话的时候晃着身子跷着二郎腿,懒散的样子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
瞧你这身打扮,我就知道你住得不远,就为这事儿就不回家了?严东生盯着男孩。
他不光砸了我电脑,还说我早恋。
早恋?严东生笑了,就你这小屁孩儿早恋?
我没有早恋好不好。
没有早恋,你跟他们说清楚不就完了吗?这事有多久了?
一个星期了,男孩的目光掠过屋子里简单的陈设,停留在挂在西墙的一堆旧照片上,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你钱包里怎么放着两个女人的照片?你有俩媳妇?
你胡说什么?严东生沉下脸,呵斥男孩粗鲁的问话。
呵呵,急了。男孩撇撇嘴没再说话。
第二天,严东生破例没去街心公园,而是去超市买来了男孩喜欢吃的肉菜,他要给男孩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昨晚他和男孩聊了一个多小时,睡的时候已是半夜了。做好了饭,严东生叫醒男孩,男孩吸着鼻子,闻着满屋子的饭香,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起来。
吃完了饭,我送你回家。严东生边吃边说。
弄半天你这使的是鸿门宴给我下套,我不回去。男孩放下筷子。
你必须得回去,几天不着家,你爸妈得多担心。
他们才不担心呢,他们正准备要老二呢。男孩翻了翻眼皮。
要老二,你也是他们的孩子,也是你妈十月怀胎生下来辛辛苦苦养大的,你总不回去,他们能不担心?
哼。男孩晃晃脑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快吃,吃完我送你回去。
我不回去,你送我回去,我就走。男孩说着站了起来。
行,不回去,先吃饭。见男孩一副坚决的样子,严东生缓下口气妥协道。
吃完饭,从家里出来,顺着向南的便道,拐了几个弯,严东生走到彩虹新城小区大门口,他想进去问问,小区里有没有个叫张李阳的孩子?他想跟孩子的父母谈谈,让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领回家。但转念一想,倘若自己问来问去的,让孩子知道了,孩子不光会恨自己,弄不好,叛逆起来更加麻烦,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叛逆期,别再弄巧成拙,还是再等等,等着孩子自己愿意回家了再说,这样想着严东生沿路返回家。进了屋,见男孩子正弯着腰东一下西一下地给他拖地。
真懂事。严东生心里划过一丝温暖,嘴里夸赞道。这么多年了,自打陶玉新走后,还没有人给他拖过地。
我不能白吃你的饭,我得给你干点活儿,省得你嫌弃我,把我轰出去。男孩头也不抬地说。
嚯,自尊心还挺强。严东生越过男孩,从抽屉里拿出象棋,问,你会下棋吗?咱俩下一盘。
不会,我只会打游戏,男孩墩完地走过来。
我教你。严东生摆好棋子,两人各执一色,严东生执黑棋,男孩执红棋。
瞧着,如果我先出起马局,你就得以兵制马。严东生手把手地教,男孩认真地看着,一盘棋杀下来男孩略懂一二,嚷嚷着再来一盘。
太阳从客厅的沙发上跃到桌子上的棋子上,停了一个时辰,便一转身又调皮地跳到有些发黄的东墙上。下了八盘棋,两个人的肚子开始抗议,咕噜咕噜的像各自藏着两只青蛙。
不下了,先吃饭。最后一盘棋下完,严东生收了棋子。
一连下了三天棋,第三天上午,严东生出去买菜回来,发现男孩站在阳台上。严东生所在的小区对面,是县城的重点中学一中,而他家楼下正对一中的体育场,此刻体育场里一片喧闹。
严东生来到阳台,见男孩正一脸羡慕地盯着操场。他探头向下望望,看见一群男孩子在你追我赶地踢足球。
上体育课呢,严东生说,嘿,真笨,到脚的球,还让人家抢了去,严东生用手指着球场上身穿红色背心的胖男孩,之后又睃一眼站在身边的男孩,见男孩一脸羡慕地盯着球场,便丢下男孩离开阳台去了厨房。
吃了午饭,严东生回屋睡午觉,这么多年,午睡已成了他的习惯,哪天都得睡上一个小时。下午三点,严东生午睡醒来,沏了杯茶,拿出棋盘,喊男孩出来下棋,喊了几声没人应,推开男孩寄居的北屋门,男孩不在。人呢?严东生把几个屋子找了一遍,也没见人影,干吗去了?出去也不说一声,严东生正纳闷,忽听桌子上手机“丁零”响了一声,严东生拿过手机,见是条陌生手机号发来的短信,刚要删掉,觉得不对劲,打开短信看见上面写道:老严,这会儿你睡醒了吧?我回家了,我想上学了。
短信是男孩发来的,手机号是第一天晚上严东生告诉他的,当时看男孩玩手机,他便问男孩手机号,男孩很警觉,说什么也不给。他便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了男孩,说以后有事就来找我。当时男孩很不屑地把嘴一撇,说我要你手机号没用,我就是蹭你家Wi-Fi玩玩游戏,没想到他还是把自己的手机号记了下来。
严东生看着短信会心地笑了,放下手机,严东生打开棋盘,摆好棋子,左手执黑棋代表自己,右手执红棋代表男孩。
严东生说,瞧着啊,别让我的马吃了你的卒。
男孩说,不怕,我有相可以吃了你的马。
……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男孩走了,严东生又成了一个人。一个人的严东生出了小区,向北过了红绿灯,向西走了五百米,又来到街心公园。亭子里那几个京剧票友已经拉上了二胡,亮开了嗓子。几天不见,严东生竟然发现自己有些想念他们了。
严东生的座位仍旧空着,几天没来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严东生看看亭子里的人,走过去掏出手纸在长凳上擦了擦,可他并没有坐下去,就那么站着,看着几个人吹拉弹唱。
大脸女人的《贵妃醉酒》唱完,是眼镜男人唱《三家店》,眼镜男人今天的嗓子不知怎么回事儿,唱着唱着就嗽一下,这么一嗽,就过了节拍。严东生心里有些起急,一起急,“杨林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就冲出了喉咙。
在座的几个人一惊,谁也没想到严东生会突然张嘴唱起来,几双眼睛齐刷刷地望过来,乐器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又吱吱呀呀地响了起来。眼镜男人和严东生你一句我一句地唱道: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