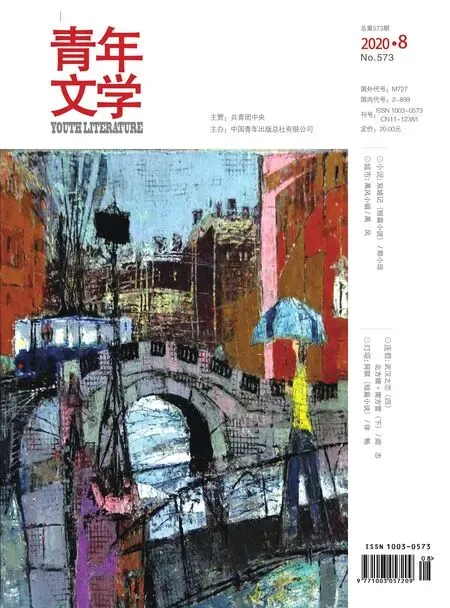里外看大城
话题始于这两篇从内部写的外企题材小说。
何谓“从内部写”?就是先进外企去“卧底”,觉得落笔对得住读者,才开写。
大学一毕业,我先当十年城市记者。当时年轻,没日没夜地勤奋,在这东部大城采访过的人数不胜数。那十年的后一半时间,无论走到这座城市的哪里,都有人喊我的中文名或英文名。如今回想,就是“如梦似幻”的流年。
辛辛苦苦顶压力冒风险写现场报道的人,无论性情如何温柔,都实在无法忍受那些堂而皇之瞎编的小说或电影,尤其当小说家或编剧忽悠到我们常年报道的专域里来。我们那时简直想请报社的文化部安排一次会面,让我们提问嘲弄这些小说家或编剧。
我也想写小说。我的小说处女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文学》上做过头条,当年收到过雪花般从全国各地飞来的读者来信,叮嘱我“写下去”。我始终记着呢,只是一直写不了,自知阅历不足,不敢糊弄人。直到有一年看见通篇瞎编的外企职场连续剧大肆走红,我实在恶心到受不了,觉得不写不行了。但我先得有“生活”。
于是我做了让很多人吃惊的决定:裸辞,报“新东方”复习班,考托福,考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申请,法国大使馆面试,终于如愿出国读硕士……毕业后直接加入跨国企业管理层,就此展开长长的“卧底期”……斗转星移,等体验够了,辞职写作。
当然,写外企题材小说只是我的开始,我的写作雄心不止于此。我既肯如此下死功夫体验生活,你就知道我不是那种靠查查资料就抖笔花的人。
且听如下问答:
“你想写你的城市的一个特征还是它的全貌?”
“后者。”
“怎么证明你写的确是你的城市?”
“只写自己眼睛见、耳朵听、心里信的。”
“写众人皆知的事还是你独具慧眼的?”
“写众人陌生的吧。”
“人既不知,你怎能知?”
“先‘卧底’。”
“深宅大院,‘卧底’那么容易吗?”
“‘卖身为奴’,埋头干个十年再说。”
“你拿哪位前辈的什么作品当作写作的量尺?”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
我来了。我生活,我写作,好汉做事好汉当。
真诚的写作难免冒犯人:朱丽叶在罗密欧眼里是皎洁明月,落他人眼中,可能就是个低情商的傻女孩。你想歌唱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情事?得了吧,会有人世故地冷笑的。
谈城市先致敬原乡。我们的先辈都来自乡野,定居城市是近事,无关血脉。我生在大城中心、长在大城,有人有时会暗示我身怀原罪。好,人本来就有原罪,多一项也没什么了不得。
城市倒是敞开着胸怀,谁都可以写。我不标榜自己所写的就是城市,有时候,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寄居在城市里。我常常怀疑我的城市是假的。
若肯依我之见,城市不代表欢欣,尽管欢欣是某类“进城文学”的底蕴;城市不代表成功,许多城市吸尽了周边乡野的脂膏,恶如大地的肿瘤;城市也不是我归宿,只是多人的聚居与寄居之地。
不由自主地降生于大城的中心,我却能免疫于这城市的自诩。我始终对它冷眼旁观。
我背起行囊,先后去往五十五个国家的三四百个城市,想通过对照了解我母城的乳汁里富有什么又缺少什么……
假如你真想了解城市是何物,你要一个劲儿地去体验。所有机会,你全要牢牢抓住:找回久违的带有童真的眼睛,走进地球上各种咖啡馆、酒吧、菜市场、鱼市场、居住区、电影院、书店、图书馆和中学、大学校园;尽可能多地找当地人交谈,放任自己提出种种尖利的问题,这些能帮你搞清自己的城市和自己的底蕴。
我穿行于哈瓦那的大街小巷,走进当地人的计划食品领取点、狭小的菜市场、提防着外国人的本地人街区的食堂;尽管被很多“街头浪人”瞪着,还是挤进他们简陋拥挤的小酒馆,像一只蝴蝶孤独地站在蜂群里,不是显示勇敢,是为了照照镜子;参加当地人高音喇叭的集会,听他们咆哮着发泄情绪,并害怕自己马上遭到抢劫;脱身后,走进唯有外国人才有能力消费的高档餐厅吃晚餐,俯视哈瓦那近百年无力修理的颓墙残垣和在昏暗街头跳着节奏感超强的拉丁舞的少女们;第二天,再去国家宣传部大楼和警察大楼,踅进博物馆浏览切·格瓦拉的遗物和照片,重温已熟读过的那段历史……
自由行,跳下印度火车,走在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我才恍悟甘地的独立运动带给印度的另一面:英国人离开后,加尔各答几乎没新建任何值得一提的建筑,大街小巷污秽不堪,宛如“弃城”。在加尔各答街巷里,在老鼠横窜的离城火车上,在那些向游客出售纪念品的小商店里,到处有愿意同我深谈印度历史和印度哲学的人……
而巴黎,举世公认的文化之都,所有走马观花的游览都是裹在浓雾里的“飞行”,我想办法住进巴黎的市井人家,包下他们的一个房间,然后到索邦大学上法语课。白天和教授讨论法国文学,晚上向房东提出对所有生活琐事和文化习俗的疑问。那些日夜,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吸收着这城中之城的一切营养。考进巴黎高等商学院之后,两百多个同届同学来自七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各大城市,都是跨国企业的经理们,我们的学业就是充分交流、尝试融合相异思想及行为方式,谋求跨国合作……
作为现代中国人,若不在首都真正生活一段时间,怎能拥有时代真实感和判断力呢?在巴黎拿到学位,我立刻选择去北京,为跨国公司工作。
我在北京的三年,上班在国贸,跟部委办的决策者们来往,游说经济及投资事务。居住在广渠门外大街,交往北京大爷北京大妈,但来往最频繁的是一群黑车司机,他们带我到城里城外那些值得玩味的地方消磨周末时光,让我如一只蝉落在北京的国槐树干上……
回到上海,我很想对我的母城说:拜托,请不负虚名,敞开胸襟,像海绵一样学习并接纳世界吧。我们不能自满于生煎馒头、葱油拌面和大饼油条;你的大剧院,还说不上是大剧院;你的陆家嘴,谈不上整体建筑美;你的图书馆,太多陈纸虚文,充斥伪信息;你的新天地,没有本地人去……大城,如果我爱你,我必须向你道出你的不足之处……
里里外外看大城的我,想把它看尽,看透,看穿,看扁,看转……然后才试着谨小慎微地写它。
不着急,我可以慢慢写,写到用钓鱼掩饰痴呆的年龄。
我不认为我的努力能光大城市文学,我只能贡献出自己的独特性,加添一股映射城市光影的文字流……然而,我将竭尽己力,忠实地记录我的时代,描画我所见所察的各色人物。
城市是时代的容器,倾尽旧酿,又满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