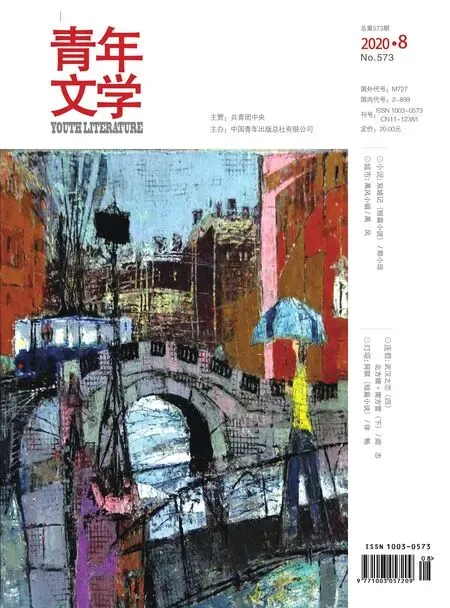致徐畅:时光最后剩下的东西,肯定是最沉的
答徐畅五问
徐 畅:童年的经历是作者最珍贵的素材,有的作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去写那段经历。我遇到的问题是,在重复书写这些素材(包括人物和事情)时,我们该如何做到不“重复自我”。或者说,如何在类似的题材中,写出不同的主题或是感悟?
张 楚:我回想了下,自己的小说很少写到童年经历。除了《小情事》和《朝阳公园》,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地重构过童年记忆。当然,这不代表我是个擅长遗忘的人,相反,我记事很早,三十多年前的场景还时常变形地在梦境中重现。童年除了与美好、明亮、温暖这些词汇相关,也与欺瞒、暴力这些词不无关系。我想我之所以没有在回溯中重建关于它的种种,多少源自它天然的隐秘与自私。很多作家擅长写童年记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担忧重复的问题,或者说,童年记忆正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得以鲜亮地诞生,这种诞生其实是过滤了的、修饰过的,我们在小说中小声讲出来的记忆,完全有可能是丝毫不心虚的杜撰。当我们明白它的属性时,记忆的重叠、写作手法的重复以及小说主题的狭隘性,都不能遣散它的光泽和质感——对回忆者来讲,时光最后剩下的东西,肯定是最沉的东西,它不拘囿于任何形式的羁绊与漠视。我读莫迪亚诺的《缓刑》时,这种感觉格外强烈。
徐 畅:作家应该还会读政治学、哲学类的书籍,去感受一些伟大思想的光芒。这与创作小说,虽然不是直接矛盾的,但是有意无意中会带来“主题先行”的问题(当然也可能不是问题)。我想问,是要求作者有一个思考的心灵,在普通人物身上呈现那样的主题,还是作为仔细观察生活的作者,去塑造那样一个有思辨精神的人物?
张 楚: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作家多读些社会学、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书籍,肯定没有坏处,至少这些书能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再一元化。它们也可能无意识地影响我的思维,左右我对事件的判断,但不会对我的写作构成一种疑惑,这可能源自我是个过于感性的人。没有必要担心主题先行的问题,当然,能主题先行并能在小说中彻底执行,也是有趣的创造。客观上看,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做个擅长思考的人,写那些引起你思考的人与事,是否塑造具有思辨精神的人、是否刻意去表述某个社会学意义或哲学意义上的话题,不应成为写作的前提条件。
徐 畅:当作者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写出了满意的作品,往往也是跟这个题材告别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打井一样,一口井打出了水,再去打另一口井时,作者会陷入有点焦虑的境地。一是素材上的陌生感,二是有更适合写这个素材的作者。想问您经历过这样的写作变化吗?您是如何应对的?
张 楚:很多写作者,包括一些文学大师,一辈子都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他打了一口又一口深井,全然不在乎井水的味道是否单调乏味。陀思妥耶斯基是这样的作家,卡夫卡也是。我想他们是没有焦虑感的。也许他们闷头干活,惰于思考这个在我们看起来貌似很重要的话题。当然也有一些伟大的写作者,其创作母题、创作手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探寻方向与风貌,他们精力充沛,更换母题和技巧只是源于他们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着好奇心,譬如马尔克斯,譬如阿特伍德,尤其阿特伍德,她的长篇结构与主题总是在自觉地嬗变,这或许是她的格外迷人之处,如果说门罗的小说是苏州园林,那么阿特伍德的小说则是广袤葳蕤的森林。我觉得写作风格延拓的焦虑,往往出于一种道德上的自信。我自己在创作中一直处于模糊、懵懂怯懦的状态,写什么,怎么写,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思考过,更多的时候,我根据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一个主题是否值得书写,而没有考虑过母题是否需要重置。我写过乡村小说,当我发觉自己对乡村的理解过于肤浅时,我开始写熟悉的县城题材,一直写到现在。我偶尔也写城市,它半是陌生半是熟稔,对我有种特殊的吸引力。随心所欲地写吧,别过多考虑风格的问题。
徐 畅:创作《阿联》时,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不确定,小说最后落在亲情上会不会显得取巧。对此,想听听您的看法。如果您读过我其他的小说,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和建议(无论哪篇都可以)。
张 楚:《阿联》是篇很有意味的小说,起点是对自我身世的追问,落脚点是追问失效,我不觉得它的结尾是讨巧的结尾,因果重叠,亲情混淆了哲学层面和伦理层面的界限,让小说有种由外至内再从内及外的光泽,这光泽似乎是经过了折射,抵达我们瞳孔的速度有些缓慢,但它终归是抵达了,可以说,这个结尾既符合生活逻辑,又符合小说逻辑。父母、姐姐和姐夫赶着鸡和鹅来家里的细节,犹如壁炉里的木柴终于燃烧了起来。我还读过你另外一篇小说《苍白的心》,那同样是篇很棒的短篇,它静气、节制、欲言又止,闲笔得当,意蕴丰饶,人物的情感状态犹如河滩里的水草慢慢摇摆,而照在水草上的光线随着水纹荡漾,光与影子交错斑驳,分不清到底是谁纠缠谁,关键是,又很清澈洁净。《阿联》这篇有着相同的特质,不过相对滞重黏涩一些。记得出小说集了,送我一本。
徐 畅:最后想问问您,近期的写作习惯,以及写作时间上的安排。
张 楚:我以前都是在夜晚写作。夜晚似乎更具有私密性和封闭性。对于整天面对着喧嚣世界的我而言,夜晚的颜色和风声能让我安静下来,让我在瞬间就能跌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心无旁骛。可当你休息时,那些小说中的人物仍和你纠缠不清,他们继续在你的思维中奔跑、哭泣或者为非作歹,这样睡眠就成了问题。以前年轻,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当一个人过了四十岁,夜晚写作就成了一种障碍。如今,我都是下午写作,晚上跑步。最近由于干眼症,写得越发少了,更多时候,都在喜马拉雅听小说。《呼啸山庄》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给徐畅的一封信
徐 畅:
你好。能以这样一种方式交流,感觉还是有些意外的。我很久没有给朋友写信了,多年以来,我似乎习惯了跟朋友们当面交流关于文学的话题,当然,通常是在饭馆里,在嘈杂的行酒令声中,小声地、秘密地谈论着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文学种种,多少有些意兴阑珊的意味。我记得我们多次见面,酒也喝过几场,不过,没错——即便我们饮了酒,也没有谈论小说,这也算是意外了。
在我颇为不准确的印象中,你是个少年老成的人。也可反过来说,你看着很成熟,身上却弥散着少年气。少年气弥散到你的小说中,便让小说有种洁净的气味,那种欲望被削减了的气味,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爱尔兰作家特有的疏离感。或可说,你的小说中有种周作人散文似的冲淡与冷清,不热闹,犹如河滩里的水草舞蹈,光线浅懒地照在上面。可是对人的复杂性的探讨,对爱与被爱错位的思索,以及那种欲说还休的自甘与委屈,又呈现出一种你自己的形态与体量。你的小说里也有闲笔,但并不突兀,它们出现在小说中,似乎是自行生长,而非一种刻意的搁置与安排,譬如《苍白的心》中消殆的庙宇,玻璃瓶中的蜗牛,譬如《阿联》中亲人们带来的活鸡活鹅,它们貌似是小说中无辜的闯入者,却在延拓小说的内部肌理和情感表述方面发散出奇妙的力量。我喜欢你对短篇小说的理解,我也喜欢你对短篇小说的处理方式——我们对短篇的建构方式和意蕴处理有着明显不同,可我必须得承认,你的方式或许更为有效独特。
从你的提问中,我发现你对小说的思考多出于宏观角度,其实在我看来,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技术层面(微观)的探索可能更为耗费我们的精力、耐心,无论怎样,这些问题在持续的创作过程中都会自行消解,哪怕在机械性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构建方式,如果将这些构建方式比作蜻蜓翅膀的纹路,那么,横、竖、横竖交叉的纹络的组合让造物主呈现出拙劣或精妙的面孔,这个面孔诞生的过程,可能就是小说写作的一种意外欢愉,它细小,却足以支撑我们在炎热的夏日夜晚与神灵对话,或虔诚,或油滑。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个人认为,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审美方式写下去至关重要。在我写作初始,我遇到过很多才华横溢的同龄人,他们在写作上流淌出来的光芒让我羞愧,意外的是,他们只走了那一段路,就转向了,当然,我没有权利评判他们的选择,腹诽他人的选择是愚蠢的,我只是为他们没有珍视他们的才华而感到惋惜,甚至比他们自己还要惋惜。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热爱写作,就像个傻子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吧。别回头,也不要探起身子张望,带好你的行李干粮,没白日没黑夜地走吧,没准,好运气正在等着你。
就到这里吧,中年人的饶舌总是让人无奈。非常之年,自行珍重。有机会了闲聚,纠结三五知己,喝点小酒,若是微醺了,谈点文学,也算是荒年惬意了。
祝夏安。
张 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