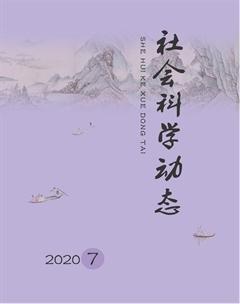中国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主体的自我建构
摘要:解构中国少数民族的建构,是1990年以后,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差异是事实存在的。中国的少数民族并不是通过民族识别创造的,民族识别的重点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和民族意愿上的国家的“确认”。而在少数民族的形成中,只考虑国家权力是对这一过程的简单化、片面化,少数民族作为主体的自我建构也值得关注。现代畲族的形成正是一个动态的、多方互动的过程,包含了历史上“畲”与政府的互动、畲族的主体能动性、畲客关系、“畲化”的可能等进程。
关键词:畲族;民族识别;主体能动性
一、民族识别遭遇解构主义
解构中国少数民族的建构,是1990年以后,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一個热点。许多来自西方的人类学家着眼于解构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建构,主张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国政府利用民族识别为工具而创造出来的。① 一批学者先后解构了壮族、彝族、瑶族等中国少数民族,希望以此证明中国的少数民族是被构建的“他者”,并与“落后”“偏僻”等形象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进一步确立“先进”的主流社会,并通过承认多样性与自治来更好地进行统治。② 大体来说,他们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建构路径有两种:一是将能分则分,将没有差异意识的群体划分为不同的单一民族;二是能合则合,将具有差异的不同群体识别为一个民族。例如,美国学者白荷婷提出“创造壮族”的观点。她认为,壮族在民族识别之前已经被汉族同化,这个民族以前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差异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对壮族进行民族识别与认定,才将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的一些小的民族群体宣布为壮族的一部分。③ 斯蒂文·郝瑞提出,由民族识别认定的彝族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在语言、经济、文化和族群自称上都有不同的族群在民族识别中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彝族。④
这种解构主义下的建构论随后遭到了挑战。一些有历史学背景的学者认为,此建构论过分夸大了传统和现代的断裂。通过历史视角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差异作为事实存在,虽然在不同时期群体间差异的意义不同,各个时期也有着自己的发明与创造,但不能因此否认差异的存在。⑤
对少数民族主体能动性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了对民族差异的存在及其变化的研究,反驳了建构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解构。美国历史学者柯娇燕提出,分析中国少数民族时,必须消除掩盖事实的具体化的国家社会二分法。⑥ 她认为,地方社会和原住民的形成无法与国家形成过程相分离,同时国家在认同的真正构建与表现上作用有限⑦,“没有任何认同是完全人造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控制其自身的‘族群身份。”⑧ 这种视角使研究者能够注意到,许多地方行动者和社区在静态的帝国表征下的能动性。⑨ 科大卫讨论了明代中期的大藤峡之战对于瑶族族群界定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斗争中,地方利益与明帝国势力的博弈与结合最终导致了广东地区土著民族的汉化和广西地区瑶人族群认同的产生。⑩ 安妮·塞特对黎族的研究探讨了海南当地黎族土著和移居海南的商人在资源争夺过程中,如何应对清政府微妙的态度,利用其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在此过程中主动地建立起黎族的身份认同,将自己与中央王朝联系起来的过程。{11}
民族形成的动态过程,中央与边缘的互动,地方的能动性和少数民族作为主体的自我建构,与帝国的扩张如何与地方的特点糅合在一起,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二、畲族确认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现代的畲族作为第一个是中国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居住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的部分山区”{12}。唐朝时的汉文文献泛称畲族先民为“蛮”“蛮僚”“峒蛮”“峒僚”。南宋末年,“畲民”首次出现在汉文史书上。畲族的“畲”意为刀耕火种,并且与畲族的自称“山哈”(畲语意为山里的客人)谐音。元代以来,“畲民”作为专有名称,较为普遍地出现在汉文史籍上。{13} 畲族的民族身份也曾存在争议。对于畲族是否是一个单一民族,曾有学者提出过异议。如古史学家董作宾教授认为,畲族是汉族农民的一种,主要论据是畲语近于客家话,故畲民就是客家人{14},还有学者认为,畲族是瑶人的一支{15}。
因此,1953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分别前往闵浙的三个畲族聚居地进行畲民族别调查。{16} 调查结果为:其一,畲族在历史上有共同的地域。至迟于唐朝,畲族就已经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处,后来一部分畲民往东北迁徙,现主要分布于闽东、浙南和赣粤皖部分山区。其二,畲族有共同的语言。除广东有极少畲族使用苗瑶语族的语言外,绝大部分畲族使用一种较为统一的接近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其三,畲族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畲族的服饰等物质生活、精神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格等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具体表现”,这对于畲族的确定十分重要。{17} 在畲族人民中最广为流传的历史叙事诗歌《高皇歌》,叙述了畲族祖先盘瓠王来历不凡,征战立功,娶高辛皇帝第三女为妻,后不愿做官,率领族人开山种田和一路迁徙的传说{18},反映了畲族家喻户晓的祖先崇拜“盘瓠传说”。整体上,畲族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如妇女服饰、祭祀、山歌等,这些特征与瑶族和汉族都有显著差异{19},即便有些地区的畲族在语言和生活习俗上与汉族相似,但他们自我意识为“山哈人”,并不是汉人。{20} 在具备客观民族差异的基础上,本着尊重本民族人民意愿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于1953年认定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21}
对于畲族的来源,各种研究众说纷纭,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武陵蛮”。汉晋时期居住在湖南长沙一代的“武陵蛮”,由于受到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陆续向附近地区迁移,在南岭山脉西部的成为瑶,在山脉东部的发展成畲。二是畲族是古代越族的后裔。此种说法内有不同主张,有的认为畲族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认为是源于战国、秦、汉时代的百越,也有主张是汉晋时期山越的后代。{22}这两种说法中,畲瑶同源“武陵蛮”的说法比较普遍,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结论。虽然对于畲族的来源,学者们各有论断,但是对于畲族如今已经发展为单一的民族这点没有争议。
畲族的确认是民族识别工作的重要一步。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是全国民族识别工作派出的第一个调查组{23},在此之前,“民族识别并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对个别族体曾开展过族别调查”{24}。由于畲族“长期与汉族人民交错杂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有些地区畲族的民族特点消失较大”{25},但不能因此就轻易否定这个群体的民族意愿与特征,所以通过民族识别“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的确认”{26}。斯蒂文·郝瑞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他认为中国政府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既不符合斯大林“四个共同”的民族定义,也不符合西方“自我意识和自我称谓”的族群概念。{27}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对这两点都十分重视。牙含章和孙青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的過程中,“每一个少数民族都碰上了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如果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两本著作中所提出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上去,那就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我国的少数民族几乎没有一个够得上称为‘民族,全部都是‘部族。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解放以前几乎全部遭遇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大部分处于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农奴制在内,少部分还处于奴隶制或者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它们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当然都还没有发展成为‘民族,而只能说是‘部族。我们认为,从事民族研究的同志不应该回避,而应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28}。我国学者追根溯源,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认识到斯大林所讲的是“现代民族”,亦即“资产阶级民族”。有观点指出,“人类发展史上一般民族最初由部落发展而成,而部落是原始社会时代的产物,说明民族最早起源和形成于原始社会的部落时代。但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旧的民族不断消灭,新的民族不断形成,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氏族部落制度消灭了,因而在阶级社会形成的新民族,就不是从部落发展而成的,而是由旧的民族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与其他民族的一部分人同化在一起而形成的。这就是说,对每一个具体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都应作具体的分析,不能拿‘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这一公式,往各民族的头上去套”{29}。对于民族识别工作中的民族定义问题,林耀华明确指出,“斯大林的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心理素质)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民族的实际,应看到多数民族在解放前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上述各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民族识别工作又不能生搬硬套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斯大林提出的四个特征,而应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30}。可见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本就不是机械地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解构中国少数民族的。
在畲族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调查小组科学灵活地运用了“四个特征”,例如,调查小组并没有僵化地要求一个民族只使用一种语言,与汉族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31} 居住状况也并不与“共同地域”相矛盾。同时,中国的民族识别过程包含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确认正是建立在少数民族主体存在的事实上,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承认诉求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名从主人”,“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是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以便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群最后确定族称或归属。‘名从主人就是说,族称要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定, 这是他们的权利”。{32} 在《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识别调查小组进入到每个畲族调研点,都会充分询问当地少数民族的自称与他称,并充分尊重他们对于民族称呼的选择。{33}
民族识别及相关研究工作不仅在于确认民族的差异性,也关注民族的动态性,这是因为,“民族的分化与融合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34}。对民族动态性的关注让学者们着眼于分析民族群体的互动与发展。
三、“畲化”的可能
畲族与客家关系的研究,是畲族研究的一个焦点。学者们通过文史记载和调查资料,论述了畲族与客家历史上长期的密切交往。例如,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讨论了闽赣粤三省边境上的畲客之间血统的混化和文化的混化。她认为,血统的混化有两种情形:一是客家先民娶土著妇女为妻,二是土著畲民的汉化,即今日客家族群中包含了部分汉化的畲民,当地已少见畲民了。文化上的混化是双向的,即畲民在语言上受到客家影响,逐渐采用客家话而固有语言消失,客家在生计活动上受到畲民影响,女性也参与重体力劳作。{35} 蒋炳钊认为,自客家迁入闽粤赣地区后,汉族文化在族群冲突中处于优势地位,迫使一部分畲族先民迁往闽东、浙南等地,而原住地的畲民有相当一部分同化于当地的客家汉民之中。{36} 吴炳奎在对梅县畲族的研究中,也支持了古代畲族先民融合于客家的分析。{37} 曾少聪认为,在畲客互动中,客家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畲族产生较大影响,而客家文化也吸收了畲族文化的某些特质,在语言、山歌、妇女地位方面受到畲族的影响。{38} 谢重光认为,早至唐末五代时期,畲族先民与客家先民就产生了合作而又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宋元之际,畲客人民进行了长期广泛的联合抗元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彼此互相涵化,进程的主导方式是畲族被同化为客家,少数未被同化的畲民要么退进深山要么被迫迁移。{39} 可以看到,这些关注畲族与客家互动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蛮僚”等同于畲族先民,汉族移民等同于客家的预设立场上,且多强调客家文化的强势和畲民的汉化。虽然他们也注意到畲族对客家的影响,但多认为这种影响是较为弱势的,并且只是对客家文化的局部影响。
陈永海的研究则别出心裁地提出了“畲化”的可能性。他更加着重于分析畲族作为主体的自我建构这一动态过程,提出畲族的构建很有可能是一种“汉化”的反向,一些现代的畲族正是汀州和赣州的汉族移民后代。{40} 对于同样的史料,他的视角与前人大为不同。例如,《云霄厅志》中记载的陈政、陈元光入闽和建置漳州的历史记录:“(唐)高宗总章二年,泉、潮间蛮僚啸乱……(陈元光)随父(陈政)领兵入闽。父卒(仪凤二年)代领其众,会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进攻潮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请于泉潮间建一州……开屯于此,以制诸蛮”{41}。他认为,这一史料展现了畲族和当地土著的连续性,然而,与传统的畲族研究理所当然地将之“蛮僚”等词汇视为一个民族标签不同,他认为当时的史料记载并没有将这一群体和任何种族或者文化特点联系起来。官方更多地强调的是,畲民因避税而定居至此,遁入山中,难以管理而成为土匪流寇的移民。甚至在“畲民”这一称呼出现在文史记载中之后,大部分的官方文件都将畲人等于拒不纳税、需加管控的流匪,期望通过诏安纳入为“民”,而没有将其视为一个单独的人群。畲族的民族文化特质在官方记载中是缺席的。及至明朝,率兵对赣南畲民“平叛”的王阳明对畲民的记载,也没有太多文化差异和风俗习惯的记录。《明史》中,对于畲人起义领袖谢志山的记载仍并未提及任何民族特性:“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浰头,皆称王,与大庚陈曰能、乐昌高快马、郴州龚福全等攻剽府县……守仁至,知左右多贼耳目……”{42}。
然而,这并不是要否认畲族民族特性的存在,或者强调国家力量构建了畲族。相反,畲民作为主体的主动构建,以及地方与中央、地方内部群体之间的多方博弈在畲族的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陈永海认为,根据传说中的名字来看,现在广泛流传于畲族中的盘瓠王神话的版本,可能是明朝才形成的。{43} 畲民在农民起义军中传播盘瓠神话,自称为畲,以加强起义军民内部的联系,畲族认同甚至可以作为周边移民抵抗政府的标志,相似的祖先神话也确保了来自瑶人的支持。{44} 王阳明在笔记中写到:“其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流传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45} “其初輋贼原系广东流来……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于内”{46}。可见当时的“畲”是一个很具有包容性的群体,无论是新移民还是较早的当地居民,都可以成为“畲”,并加入到与政府对抗的这一群体中。然而,在明朝政府设置了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和赋税制度后,“畲”很快成了一个边界地带的显著的政治符号,以彰显国家力量并且降低民众成为流民的刺激。此时,新的政策使得民众倾向于定居,通过纳税被归于国家管辖下,并且新的登记政策允许之前成为畲民的流民录入为当地固定居民,而“畲”依然和“流匪”联系在一起,因此明朝政府引入的措施降低了畲族自我认同的显著性,很多人放弃了“畲”的身份,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中。畲人认同的政治重要性逐渐消失。此后,只有一些比较边缘的还保持着盘瓠祭祀的畲人,强调血统、宗教仪式、内婚制等特点使其逐渐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群体,才逐渐形成了现代的畲族。在畲族的民族特性被官方注意到并确认后,清朝政府剥离了“畲”与“土匪”的联系,强调了“畲”的民族标签。所以,在此过程中,不断进入山区的移民与更早居住于当地的居民一起,成为不受管控的流民,成为“畲”,而不是“蛮僚”等同于畲族先民,移民等同于客家先民。现代的畲族中,很有可能有部分早期的漢族移民,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客家先民。
畲族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如前文提到,“不能拿‘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这一公式往各民族头上去套”{47},有着“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现代畲族,与史料中的“蛮僚”“盗贼”群体并不可相提并论。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民族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陈永海的“畲化”论可能会受到挑战,比如,对于谢蓝传播盘瓠神话以建构畲人认同,并用以团结瑶人,作为与中央博弈的手段的观点,并没有十分详实的史实去支持,只是对已有资料的一种可能性解读,并且其资料来源大多是谢蓝所对抗的王阳明的记载。然而,这样一种解读不应该被轻易否定。在过去对于史料的解读和少数民族形成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专注于确认少数民族的差异性以及互动中政府和主流群体对少数民族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去构建自身的能动性。一些更近的研究也关注了畲族在历史上和民族识别后的主体能动性。如曹大明先生认为,畲族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异态的、高度的稳定性。他以大量例证论述了畲族(主要是明清时期)如何利用族源传说等历史记忆向官府争取免除徭役等有利于畲民权益,以及畲族如何通过神秘性的记录、仪式与符号等传承民族历史记忆的事实。{48} 周大鸣教授通过在江西的田野调查指出,在1985年落实民族政策之后,江西省赣南部原属于客家的蓝、雷、种姓恢复成畲族后的族群重构过程中,凡是主动恢复畲族的群体,其族群知识的重新构建相当快,当地民族精英很积极地学习传播畲族的知识。并且,他还通过对当地族谱的文献考察,展现了当地畲族通过族谱构建畲族民族认同的生动过程。他指出,明成化年间的族谱并没有构筑族群来源,清康熙十二年的普序很严谨地论述了祖先的来历,从乾隆四十九年的普序开始则通过构筑族源历史,附会传说轶闻,树立家族楷模等形式构建自己的畲族认同。并且这一“认同的构建”在落实民族政策后达到了一个高峰,《汝南堂蓝氏续修族谱》中甚至写到“炎帝时开族为畲族”。{49} 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了,在畲族的形成、延续与重构中,畲族作为主体,能够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境、自身的政治诉求,成为行动、对话的主体,展示畲族的主体能动性。
四、关注少数民族的主体能动性
在民族识别工作的论述及大多数的相关研究中,少数民族作为主体对于自己民族身份的构建相对被忽略了,边缘与中央在互动中的博弈也被忽视了,尽管这种主体性与能动性在实际情况中是存在的。就畲族来说,畲族的民族特性被辨析并确认了。但在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能动性的论述中,畲族人民反封建统治的话语叙述成为了唯一的重点。学者们对史料的解读也多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专注于论述文史记载如何体现了畲族人民作为受压迫民族反抗封建统治。在《畲族简史》中,对于畲族和历代政府的互动,几乎全都是以压迫与反压迫的单向被动视角去描述的:“畲族人民反抗唐、宋王朝统治的斗争”“畲族人民的抗元斗争”“明、清时期畲族人民的反抗斗争”。{50} 尽管当时的学者们敏锐地注意到,明清统治者对于地方能动性的反馈,提到明王朝在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后对该地区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清顺治与康熙都曾下令免除当地田粮赋役。但是这些对于认识少数民族主体能动性和多方互动博弈的重要信息,在当时很大程度上被“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反封建”的叙述所淹没了。后来也没有着重分析这个过程中畲族的边界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以,虽然这些论述体现了畲族主体性,但是只从一种被动的静态的视角,忽视了畲族主体在此过程中主动地建构自身的动态过程,忽视了作为能动性主体与中央的对话,与地方其他互动的复杂情况,这是十分可惜的。在畲族与客家的研究中,对于客家文化的强势性认定和畲族汉化的单向同化观点,也是弱化了畲族主体的能动性,似乎完全没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尽管从陈永海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客家”到“畲族”的“畲化”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的主体能动性的忽视使得民族识别工作的记录和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思路被简化了,也为解构主义提供了土壤。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少数民族的差异性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既有对于传统差异的延续,也有多方的互动与建构。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只考虑国家权力是对这一过程的简单化、片面化,只看到中国政府的构建,认为是民族识别创造了少数民族,是有失偏颇的。要消解这样的解构主义,只是确认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是不够的,更要关注地方的能动性、少数民族作为主体的自我建构,展现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少数民族群体的多方互动博弈。对少数民族主体能动性的关注,其实本质上是回到民族识别的原则中,是对科学性、动态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陷入解构主义的漩涡之中。
注释:
① 潘蛟:《解构中国少数民族:去东方学化还是再东方学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② Dru C. Gladney,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4, 53(1), pp.92-123; Ralph Litzinger, Other China: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8.
③ Katherine Palmer Kaup, Creating the Zhuang: Ethnic Politics in Chin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pp.1-24.
④[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⑤ 欧立德:《清八旗的种族性》,《清史译丛》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128页;[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4—363页。
⑥⑦⑧⑨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Donald S. Sutto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1-21, p.7, p.3, pp.12-16.
⑩ David Faure, The Yao Wars in the Mid-Ming and Their Impact on Yao Ethnicity,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171-189.
{11} Ethnicity, Conflict, and the State in the Early to Mid-Qing: The Hainan Highlands, 1644-1800,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229-254.
{12}{13}{22}{50} 《畲族简史》编写组:《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1、6、11、44—52页。
{14}{16}{17}{20}{21}{23}{25}{31} 施联朱:《解放以来畲族研究综述》,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7、7、8—9、9、9、7、7、8页。
{15} 徐规:《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徙》,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8}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
{19} 钟昌瑞:《也谈畲族族源》,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24}{26} 秦和平:《“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民族学刊》2013年第5期。
{27} 郝瑞、杨志明:《论一些人类学专门术语的历史和翻译》,《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
{28}{29}{47} 牙含章、孙青:《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
{30}{32}{34}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33} 参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5}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6页。
{36} 蒋炳钊:《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邱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37} 吴炳奎:《广东梅县畲族考》,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1—297页。
{38} 曾少聪:《汉畲文化的接触——以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为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39} 谢重光:《客家与畲族早期关系史述略》,《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40}{43}{44} Wing-Hoi Chan, Ethnic Labels in A Mountainous Region: The Case of She “Bandits”, in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F. Siu, and Donald S. Sutton,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264, p.271, p.272.
{41} 《云霄厅志》卷11, 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字重印本。
{42} 《明史》卷195《王守仁传》。
{45}{46}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10《别录》;《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福建省编辑组编:《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360页。
{48} 曹大明:《论畲族历史记忆的稳定性特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年第6期。
{49} 周大鸣:《从“客家”到“畲族”——以赣南畲族为例看畲客关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年第00期。
作者简介:辜靖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陈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