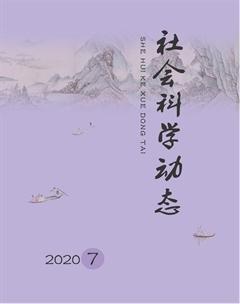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
编者按:李文才,男,1969年生,江苏省东海县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1998年先后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师从赵文润、牛致功、牛志平等先生,研习隋唐五代史;博士师从黎虎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先后任教于大连大学、河北大学、扬州大学,2003年晋升教授。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史》《文献》《汉学研究》(台)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文集8种,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等。
古语云:“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学习、研究历史使人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多年来,我国历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学风潮流等都有了新的趋向。2020年5月,我们就所关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生专业学习、学术研究中的困惑以及当前的学风等问题,对扬州大学李文才教授进行了采访。李老师从其本人的学术经历和治史心得、研究生史学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如何提高文献阅读和史料收集的效率、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以及当前的学风等几个方面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解答,对新世纪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与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兹据访谈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张林君(以下简称张):李老师,您好!作为您的学生,自从我们准备报考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您的学术成就,但是所见有关您的履历介绍,多数十分简单,并没有您从事学术研究的更多信息。能否请您稍为详细地谈一谈您的学术经历,特别是您如何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呢?
李文才教授(以下简称李):好的。实事求是地讲,在读大学之前,我从未想到过自己竟然会以治史为业。不过,对于中外历史,我自小就有着异常的兴趣,也是事实。至今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当时读了一套山东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读物,具体名字已经记不清了,内容是关于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我后来对古代文史特别感兴趣,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比较敏感,与小学时期的这段经历应当是有些关系的。我还记得,当时我读过之后,总是要给我身边的小朋友讲,而且往往讲得活灵活现。80年代初期,刘兰芳演播的《杨家将》《岳飞传》、袁阔成演播的《三国演义》、单田芳演播的《水浒传》《三侠五义》等评书陆续在电台播出,成为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综艺娱乐节目,我也是特别喜欢听,而且听完之后几乎都够复述,真有些“过耳不忘”的本事。以上这些可能就是我早年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吧。
1985年,我考入东海县中学念高中,高二时分科,选学了文科。1988年高考成绩不理想,结果进入自己并未报考的扬州师范学院,更没想到进了历史系。我高中时的理想,是报考法律专业,将来做一名律师或法官的。由于没有考上理想中的大学,所以刚入学时,对于所学的历史教育专业是有一些抵触情绪的,自然更不会想到今后会从事史学研究。不过,在扬州师院读书的四年中,我读的书还是很多的,也比较杂,涉猎过经、史、子、集的基本典籍,马列毛选也读过一些,还读过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著作,如《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等,不过存在主义的哲学著作不易懂,可能是读得一知半解吧,也就没有坚持读下去。大学期间还读过一些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武侠小说,一直到后来读博士期间,还是喜欢偶尔翻阅一下。大学期间读得杂一些,还是有好处的,从事人文社科专业的研究者,不能只看专业书籍,否则就会有局限性,思维也容易受到拘束。不过,读书多了、杂了,考试成绩就不行了,因为大学历史专业的考试,基本就是背诵教科书或老师的课堂笔记,我最不喜欢读的就是教科书,也从来不做记课堂笔记,因此大学四年期间,我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排在班级后面的(班上共61位同学,我们戏称“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大概是倒数前五名之内吧,总之从来没有达到过评定奖学金所要求的分数线,甚至还有过补考的经历。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只是我确实不适应那种单纯知识背诵式的学习,更不喜欢那种考试的方式。有一点我一直都很自信,那就是大学四年我读的书比较多,班上同学比我读书多的,可能有,但绝对不会超过三个吧。因为从来没有考出好成绩,所以后来我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多数同学都认为是个笑话,还有同学调侃说,你报考“烟酒生”我相信,考研究生,还是算了吧。甚至到了后来,我通过了初试,拿着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复试通知书,去系里请假时,很多老师都不相信我能考上。等到我进入陕西师大读书后,才知道师大历史系当年共录取16名硕士生(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共四个专业),我的总分第一,我到现在还记得各门成绩:隋唐史94分、中国通史(1949年之前)89分、古代汉語89分、英语50分、政治58分,当年英语、政治的国家分数线都是50分,我成绩高在三门专业课上,平均超过了90分。由此看来,我并非不擅长考试,只是不擅长某些考试罢了。
1992年9月,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从事自己理想中的隋唐史研究。其时陕西师大的隋唐史专业还是很强的,中国唐史学会也挂靠在师大,因此除了历史系招收隋唐史研究生外,还有唐史研究所也招生,历史系和唐史所在行政关系上属于互不统属的两个单位,但双方的师资却是互通共用、彼此合作,老师之间的关系一向非常融洽,因此,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上课、学习从来都是在一起的。我的学籍管理属于历史系,挂在赵文润先生的名下,但牛致功、牛志平两位先生也是导师,所以后来我们学位论文封面上的导师一栏,多数都是同时写他们三位的名字。赵文润先生为人爽朗豪放,不拘小节,总是大说大笑,因此讲课特别有感染力;牛致功先生为人敦厚温和,慈眉善目,是一位大有长者之风的谦谦君子;牛志平先生为人谦逊平和,言语温婉,可能因为以前在报社工作过,所以说话、文章都是字斟句酌,条理清晰有致。三位老师尽管做事和治学的风格不同,但都是具有渊博学识和美好品格的正人君子,都是令我十分尊敬的师长。那个时候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还必须听黄永年先生的课,这大概是史念海先生定下来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黄先生是公认的学术大家,不仅精擅隋唐史,而且在古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古籍整理等领域,皆堪称大家,特别是他所独创的碑刻学,已经成为学界研治石刻文献之学者所宗奉之学问。我有幸跟随黄先生学习了两个学期,当时黄先生就在家里授课,我们到了黄先生家,坐好以后,先生即开始侃侃而谈,听黄先生讲课是我在陕西师大最惬意和最值得怀念的一件事情。黄先生的治史思路、行文风格都给我以极深的影响,我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就是当年提交给黄先生的课程作业。还记得,当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交稿后,师大历史系的先生们看完之后第一个评价是:“怎么好像黄先生的学生!”意思是我的行文很有黄先生的风格。
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师从黎虎先生,研习魏晋南北朝史。黎先生作为当代史学大家,不仅开创了中国外交制度史新学科和构建了中国中古时期“吏民”问题研究学术新体系,而且在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问题上,也提出了全新的学术体系。所以,进入北京师大,忝列黎先生门墙,可谓我学术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一段历程,奠定和指引了我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方向。1995年,黎先生共招收了3名博士生,分别是王元军、张金龙和我,作为黎先生第一届博士生,我们可算是先生的开门弟子吧。大师兄王元军属于才华横溢型的,兼之读博前已在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工作多年,故学业优敏,另外王师兄擅长书法,1998年博士毕业后又随欧阳中石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并成为中国第一个书法博士后。二师兄张金龙温柔敦厚,学识渊博,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人格特征,198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至1995年已在兰州大学工作近十年,并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可谓魏晋南北朝史学界不多见的青年才俊,在师大读博士期间,我与金龙师兄相处时间较多,学业、生活方面均深得师兄之厚谊关照。师兄弟三人中,唯有我是本、硕、博连读,在同门中不仅年龄最小,学术水平也是最弱的,因此入学之后黎先生就有点担心我的学业,对我能否如期完成学位论文,应该是有些忐忑的,至于对王、张二位师兄,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也正因此,先生对我的要求也就较两位师兄更为严格一些,一开始要求我每周去他家一次,汇报读书情况,去时要带着读的书和做的笔记去,大概经过两个月的考察,黎先生可能确信我每天都在读书,此后便不再要求每周去汇报了。我后来能够顺利完成学位论文,如期毕业,与黎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博士毕业以后,我先是在大连大学工作了两年,承担了和中国古代史没有多少关系的《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任务。在大连两年期间,记忆较为深刻的事情之一,是曾经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一门公共选修课《隋唐文化漫谈》(后来黎先生说《漫谈》不好,到河北大学工作后,就接受黎先生的建议改成了《隋唐文化史专题》),由于学校不限制选课人数,结果竟然有700多人选课,我思考过原因,可能并非是因为我的教学水平高,而是当时大连大学博士较少,学生们都想听听博士讲课吧。在大连工作的两年,主要是调整身心,因为从本科到博士毕业,十年不间断地读书,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情,确实都需要进行一番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休息、读书,一方面思考学术方向。2000年6月引进到河北大学后,从下半年开始到2003年,我基本保持每年发表十篇左右的论文(而且多篇是今之所谓CSSCI刊物,当时没有C刊之说,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北大中文核心和社科院的人文社会科学核心),这应该就是在大连休息、调整所积累的结果吧,因为在大连的两年期间虽然发表的论文较少,但一直都在围绕博士论文的修订进行思考。在河北大学工作期间,我还先后申请并完成河北省社科规划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河北省教育厅博士基金项目等,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3年破格晋升教授。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在大连两年中的休息调整,实际上也是有些关系的,如果没有那两年的“休养生息”,也就不一定会有到河北大学之后的连续“高产”了。近来,我反思自己的学术经历,也考虑过学校现在的一些人才政策,那就是扬州大学每年都会引进一批青年博士,现在的他们就是过去的自己,因为我们的经历有很多相似性。我就想,学校能否给他们一、两年休息调整的时间呢?让这些青年博士围绕博士学位论文修订打磨,对未来的学术方向进行一些规划,可能比一上來就要求他们发表多少篇论文、上几门课程、完成多少课时,更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吧。
2004年,我被引进到扬州大学工作,回到了阔别12年的母校,工作地点就是我当年读大学的地方——昔日之扬州师范学院、今日之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在随后的十几年间,我继续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近年又上溯至两汉,并涉足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5部;2016—2018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唐五代扬州地区石刻文献集成与研究”,其结项成果即将于2020年10月出版。自2016年起,我又开始关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国古代吏民问题研究等。201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从2018年开始招收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目前已经有1名博士后出站,指导3名博士研究生、3名硕士研究生。在教学上,我承担了本科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隋唐史研究专题》两门专业选修课,另外开设了《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隋唐文化史专题》等校级公共选修课,还有几门研究生课程。
以上就是我大致的学术经历吧。
张:李老师,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治史经验,谈谈应该如何从事中古史研究?您在学术研究中有哪些深切的体会?
李:如何从事中古史研究,这个问题其实我是不太敢谈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各异,都有适合于他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和学术路径,因此你所说的“治史经验”,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为他人所“复制”的。不过,在从事中古史研究的过程中,我确实有些心得体会,还是可以和同学们分享一下。
无论从事中古史还是其它时段的史学研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而切忌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我自从2003年开始独立指导研究生开始,就经常遇到这样的学生,他们总是问我,怎样才能尽快学会撰写学术论文、如何才能够尽快发表学术论文等问题,表现得十分急切。实际上,这不符合历史学研究生培养的规律,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弄清楚一、两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就很了不起了。我认为硕士研究生阶段,首要的、根本性的任务,还是读基本史料,而不是急于“出成果”,也就是说,要沉心静志地读书,而不是尽快地发表论文。当然,平时的练笔还是有必要的,我认为最好是从撰写读书札记开始,在读书的过程中将遇到的问题或产生的疑问,记下来弄清楚,一条条小的读书札记积累多了,最后就会形成大问题、大看法,我有些文章就是这样形成的,就是在当年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最后成文的。对于同学们急于“出成果”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这也不能全怪同学们,更主要的责任在于现在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出现了问题,例如很多学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要求硕士生毕业前发表学术论文,而且要求发表在SCD刊物上,否则不授予学位、不能毕业,这就明显超出了硕士生的学术水平和能力范围,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不合理的要求,属于教育部所批评的“五唯”风气之一。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至多是有些老师会鼓励学生“出成果”,所以1992年9月我到陕师大读研究生,刚入学老师就要求读两《唐书》《资治通鉴》隋唐纪部分,这些都是隋唐史方向研究生必读的基础性文献。后来,到北师大读博士研究生,黎先生也是要求先读魏晋南北朝的“八书二史”等基础性文献。应该说,这种做法才是符合中国古代史治学规律的“正道”。正是因为没有毕业前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我们才得以专心读书,而专心读书便有所收获,反而容易写出高质量的文章,例如我早年发表在《晋阳学刊》《人文杂志》《中国史研究》《史学集刊》上的几篇文章,还有后来发表在《江汉论坛》《唐史论丛》的一些文章,都是硕士阶段写出来的,或者是在硕士生阶段所写札记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第二,要全面了解并掌握相关领域的学术史和最新学术动态。在认真、扎实阅读中古时段基本史料文献的同时,还要全面了解并熟悉这一阶段的学术史,也就是你必须洞悉有关这段历史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和代表性学者,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避免因为重复前人的研究而做了无用功的情况。当然,熟悉学术史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因此对于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论著进行精心研读,是十分必要的,如吕思勉、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黄永年、黎虎等先生的相关论著,都是应该认真阅读并深入领会他们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和治史思路。除了全面了解学术现状外,还必须及时关注最新学术动态,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学术发展似乎也“提速”了,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术论文、著作面世,对于这个方面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关注学术动态的意义,主要是为了预防自己的选题与别人“撞车”,从而做了没有意义的重复性劳动。不过,对于每年的学术动态特别是新出现的学术成果,作大致了解即可,而不必像对待基础史料和代表性论著那样花费太多时间去深究,一是因为每年新出的论著数量庞大而我们的精力有限,二是绝大多数“新成果”并无实质性的学术创新,不值得耗费太多时间在上面。但对于其中真正具有引领学术方向的创新性学术成果,还是应该花大力气去认真研读的,比如近年来我所一直研读不辍的黎虎先生论著——《汉唐外交制度研究》、“吏民”研究系列论文,以及他的关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论著,这些都是真正具有创新价值、能够引领未来学术走向的学术成果,这些就值得我们反复揣摩、深入研读和体悟。
第三,要努力培养读史、治史的兴趣,激发从事史学研究的热情,进而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件事情只有你真正对它发生了兴趣,才会充满激情,并最终由衷地喜爱上它,进而乐于将它作为你为之付出的一项事业。以我自己来说,原本并未想过从事史学研究的,后来无意间走上这条道路,在日积月累的读史过程中,我逐渐对中古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到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每天如果不读上一点史书,便觉得少做了什么似的,特别是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读上一卷或两卷正史,已经成为近两年的新习惯,因此说读史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大致是属实的。那么,这种由兴趣再到热爱,进而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是如何养成的呢?我想,只要你从历史中发现令你感兴趣的东西,再能够坚持下去,最后总是可以做到的。首先,要找准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我特别喜欢政治史,一开始是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感兴趣,例如我所发表的两篇论文《“唐武宗平泽潞”再评价》(《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江都之变新探——兼论隋短祚而亡的原因》(《人文杂志》1995年第1期),都是围绕人物、事件的分析而成文的。不过,随着习史治史的不断深入,我的研究兴趣慢慢转向对政治制度的探研了,因为如果不从制度层面探索历史,而始终纠缠于人物、事件的分析,终究会流于历史的表象而无法探知其真谛和本原的。其次,在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选题之后,就要围绕选题展开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不仅要全面收集整理相关的基础史料,還要梳理相关的学术史并了解研究的最新动态,在此基础上,要给自己多预设几个问题。也就是说,要带着问题意识去研究课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问为何是这样?前人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的呢?前人为何这样分析呢?我的探究和前人相比,有哪些突破?如果你能够将自己预设的这些问题解释通融,那你便初步掌握了史学研究的方法了。复次,在充分了解学术史、带着问题意识去探索的过程中,要学会并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跟随前人的研究思路前进,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敢于质疑前人的观点,即便是大师的观点,也不能无条件的盲从,也不要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幼稚,因为每个学者都是从幼稚走向成熟,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第四,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进行史学研究。我认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最后的成功,都必定是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因此从事史学研究,也必须有自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同学们,你们尽管不一定有着过人的才华,但肯定都具备从事史学研究的基本素质,我记得有个史学界老前辈就说过,中才以上者就能胜任历史研究,他的这番话是可以相信的。你们都先后经历过很多次升学考试,包括顺利通过高考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可谓是“身经百战”的胜利者,你们是在经过层层筛选,淘汰了众多竞争对手之后,而成为扬州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的,因此你们应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智商是完全能够胜任史学研究的。至于怎样才能够做好历史研究呢?这个没有特别的窍门,那就是要勤奋刻苦,广读博览,多读书、多思考、勤钻研、勤动笔,在学习读书的过程中要有只争朝夕的意识,在探索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要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我相信天道酬勤,只要你们肯付出,再辅之以科学合理的引导,必定能够养成较强的科研能力,而这种能力一旦养成,你们以后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工作,都将终身受益。
张:您认为从事历史研究需要具备哪些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这方面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呢?
李:从事历史研究所需具备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我认为这主要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概括:一是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积累,二是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三是具有开放的思维、独立的见解和创新的意识,四是要有高超的文字表达能力。
至于如何培养和提高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也是不可一概而论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史学研究者,其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肯定存在着一定差异,这是客观事实,例如有些人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时间并不长,即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学术素养和能力,而多数人则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训练,才能够养成。这是因为影响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因素,可以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个方面,比如有些学者对于史学研究天生就有敏感性,表现出来就是他的先天性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都比较强,这类学者或可谓之“天才型”的历史研究者,但“天才”毕竟并不多见。多数学者都是经过了刻苦勤奋的学习之后,才养成了较高的学术素养和史学研究能力的,我想我应该属于后者。因此,我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来培养和提高这两个方面的能力。
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广读博览、勤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所提倡的这一读书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指导我们进行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也可以用于培养我们的学术素养的研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读书而读书,还要进行思考,如果一味读书而不思考,就会被书本牵着鼻子走,从而失去主见,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即指此意,这样的人尽管读书很多,却没有什么思想,那他不过就是一个“两脚书橱”罢了。相反,如果一味空想却不去进行实实在在的学习和钻研,那也不行,那样的结果必将是空中楼阁,一无所得。所以我说,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大量阅读文献和时刻勤于思考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多看、多读、多思之外,还要多动笔,多写札记,所谓见多识广,当你看的基础文献多了、对学术现状和學术动态了解得多了,你所知道的自然就多了,知道的多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加强了,札记写多了、卡片做多了,你的积累就多了,看法也就多了,日积月累,你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史学观点也就形成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并逐步提高了。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独立的见解”这一条。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历史研究者,“独立见解”对于史学素养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史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门“独断之学”,也就是说,对于历史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不能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目前历史学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良学风,那就是有不少学者喜欢引经据典,甚至沉溺于学术史的梳理,连篇累牍地罗列学术界既有的各种观点,但是在一番长篇大论之后,却唯独没有提出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或立场,所以看了他们的文章,我们固然可以了解不少知识,却并不知道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究竟持何种观点。当然,我并不是说学术史的梳理没有意义,而是说一篇缺少作者独立见解的学术论文,就如同一个人缺少了灵魂,因此一个学者如果不能就其所讨论的问题进行“独断”,而只是一味步人后尘,拾人牙慧,那么这种所谓的学问,无异于复读机的工作原理,而绝对不可能做出真正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研究中的“独断”也就是必须有个人的独立见解,乃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根本保证,离开“独断”,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史学研究的。
繁琐罗列各种前人观点而缺少“独断”的不良学风,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重复前辈学者或所谓学术大师的某些观点,然后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削足适履,去证明大师或前辈相关论点的正确性。试想,这样的研究怎么可能产生创新性成果呢?无论其论证方法如何高明,或者论证得如何充分,至多是将前辈或大师的某个观点再一次证实而已,其下者则是复述一下他们的观点,谓之拾人涕唾,实不为过。实际上,这种靠诠释前辈或大师观点而成文的学风,不过是昔日“以论代史”学风在新时代的变种罢了,“以论代史”的基本套路,就是从马列著作中寻章摘句,从中拈出马、恩、列、斯说过的某一句话作为预设观点,然后再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编排、填充、裁剪和歪曲,去论证其预设观点的正确性、合理性。当今这种变相了的“以论代史”学风,从表面上看,它不再言必称马列而显得更有学术性,但在本质上和以往的“以论代史”并无不同,它只不过是将以前的马、恩、列、斯,换成了陈寅恪、唐长孺或钱穆而已,因此,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以论代史”的不良学风,只不过它的欺骗性更强,容易迷惑人,特别是对初涉史学领域的年青学者更具迷惑性。
张: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式与本科阶段有很大不同,比如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大量阅读文献、高效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等,这些都与本科阶段有质的差别。请问李老师,您能否就如何提高文献阅读和史料收集的效率这个问题,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另外,在阅读基础文献的时候,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为好?还是进行不带目的性的通读为好?
李:你这几个问题,可以合并一起回答。实际上,你们已经意识到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式,与本科生阶段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本科阶段是以知识性学习为主,而研究生阶段则主要是独立自主地学习,要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研究生”就是要研究。不同于理工科专业,历史学专业是建立在大量阅读文献、收集整理文献和分析理解文献基础之上的一门学问。中国古代史专业领域的文献资料,虽然不敢说是浩如烟海,但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全部掌握的。研究生专业学习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三年,其间还有英语、政治等非专业性的学习任务,再加上各种各样与专业学习无关的活动,也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因此,留给同学们用来研读专业文献的时间,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读书的效率,通过高效的阅读,尽可能弥补失去的时间。那么,应该怎样阅读呢?我仅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权且当作是经验吧。
首先,读书要讲究方法。诚然,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因而不可强求一律。但是,读书又确实有一定的方法,找到适合你的阅读方法,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有可能事倍功半。一些前辈的读书方法,确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例如,黄永年先生曾经讲过他读书的方法:他从不做学术卡片,读书时集中精力去读,对于其中涉及的人名、地名、读音等疑惑则一概忽略,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既定的读书任务。如果人名要去查、地名要去考证、读音也要弄清楚,那么一天下来是读不上几页的。再如,黎虎先生读书时喜欢做学术卡片,他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两部巨著,都是通过做卡片积累起来的基本史料。受黎先生直接影响,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也是做学术卡片,迄今我还保留着当年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所做的两百多张卡片。由此可见,读书无定法,对别人的读书方法,我们可以借鉴或学习,但不能照搬,上述两位先生方法不同,但都做出了一流的学问。我先后跟随两位先生学习过,从他们那里我都学到了很多。但是在做卡片和不做卡片的问题上,我选择了做卡片,并不是因为不做卡片的方法不好,而是因为我觉得做卡片的方法更适合我。如今,我仍然做学术卡片,只不过方式有所改变,以前是摘抄在卡片上,现在是直接勾画、标注在书上,形式不同,方法则一。
其次,读书要有计划。“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就是指做事一定要先有计划,才有可能成功,读书也一样。没有计划,毫无目的的阅读,首先就是一种低效的读书。读书计划可以分为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两种,长期计划主要是基础性阅读,比如我的长期读书计划,就是坚持每天阅读“二十四史”,不求多,一卷、两卷、三卷或四卷都可以,但每天必须读,日积月累,基础史料的功底就扎实了;短期计划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我近期要做的某项课题或研究,或者撰写某一篇论文,这时就需要高效率、高强度、指向性明确地阅读相关史籍和学界既有相关论著,目的就是首先完成这个任务。根据我的实践经验,长期阅读计划和短期阅读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同学们在制订和实施读书的过程中,要尽量做到长、短接合,相互促进,比如对于专业基础文献,可以作为长期读书计划,而针对所要完成的课程作业或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则不妨制订一个短期的、指向性相对明确的读书计划。读书计划制订好以后,关键在于付诸行动,也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去阅读,如果不去读书,再完美的计划也是虚幻泡影。我当年在陕师大读书期间,一入学就按照要求,主要读《资治通鉴》隋唐纪部分,同时读《旧唐书》,我每天坚持读三卷《资治通鉴》,并作笔记,那时我手头没有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读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的,很是费神,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大概经过一个学期,我就读完了隋唐纪部分,还做了一大本笔记,因此对于隋唐历史的梗概,便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来到北师大读博士,还是重点阅读基础性史料“八书二史”,大约经过一年的阅读,魏晋南北朝史的基础史料也大致心中有数了。因此,你们也一样,也要制订出自己的读书计划,计划制订好以后,就一定要按照计划的进度,按时完成每天的阅读,而且读书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我相信只要同学们足够努力,一定会学业有成。
复次,是否一定带着目的性去阅读。我认为这个需要辩证地看,不可一概而论,要视情况而定,关键是你读什么样的书,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有些书一定要帶着明确的目的性去读,因为有了相对明确的目的,你才有可能在读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才有可能发现你解决问题所需的有用信息。另外,有目的性的阅读,不能仅仅停留在阅读的层面,还要勤动手、多动笔,遇到引发你学术兴趣的内容,或与你所思考的问题有关系的材料,应该随时把它记录下来,随读随记是一种良好的辅助性阅读手段,切忌有那种“这次通读,下次精读的时候再做笔记”的想法,因为有些想法或灵感是稍纵即逝的,这次有想法,下次就不一定有了,而且时间不允许你这样做,因为供同学们读书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还有就是,阅读时一定要排除干扰,客观地讲,现在研究生的阅读量,远远不如我们那个时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牵扯你们精力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例如手机就是影响阅读量的一个“罪魁祸首”。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电脑极少,固定电话都很少,而现在你们是电脑、手机不离身,物质条件、技术手段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但是阅读量时间却大大减少了。我看有些同学,可能每天看手机的时间,要超过看书吧,你们有几个能够做到读书的时候不碰手机呢?所以,我给同学们提个建议,那就是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尽量把手机放得远一点,不要没读几页书便想着去摸手机,毕竟你们还是学生,还有什么事比读书更重要的呢?
最后,阅读要有选择性,即便是专业领域的书籍,也要进行认真的选择。这是因为现在的文献资讯可谓海量,即便我们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书读过一遍。以魏晋南北朝史或隋唐史为例,相关正史、《资治通鉴》、三通等基础性文献是必读的,也是要花大力气去读的,这是从事这段历史研究的史料基础。除基础文献以外,这个领域的一些经典论著,以及一些具有真正创新价值的新出论著,也都需要认真阅读、精心揣摩,前者比如吕思勉、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的论著,后者如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黎虎先生的汉唐外交制度专著、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以及他关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的专题论文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精心研读、反复揣摩的学术精品。通过研读这些学术精品,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体悟其学术思想、学术旨趣,还可以借鉴他们的立意构思,学习他们运用史料、解读史料的思路和方法,从而训练、培养和提高我们理解、驾驭史料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是运用最为常见的材料,却做出了富于启发性、充满创新性的真学问。
至于每年新出的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则不必也不可能每篇都去读,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无创新、无价值的老生常谈或陈词滥调,其中尽管也有一些貌似考证严谨的文章,然而其所讨论者多为邻猫生子式的琐细问题,难免“碎片化”之讥,其下者则谓之学术垃圾也不为过,因此对于这些数量众多、良莠不齐的所谓学术论著,从学术史的角度作大致了解即可,而不必费神深究。
张:我们目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困惑,就是在阅读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尽管有时候也觉察出作者的观点可能有问题,却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作者的逻辑思路走,甚至最后接受了他的观点。请问李老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摆脱这个困惑呢?
李: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很正常,因为这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阶段。尽管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思路,但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有正常、清晰而合理的逻辑思路,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并无正常的逻辑思维,他们的文章中经常出现一些不合情理的、混乱的、错误的,甚至是诡辩的逻辑,他们往往预设某种观点,然后运用这种混乱、诡辩的逻辑,对史料进行裁剪和歪曲,从而证成其所谓的观点。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也不是仅仅见于中国古代史学术领域,其他领域也有,不过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领域中,这种情况似乎尤为突出。
那些貌似合理实则荒谬的逻辑,为什么常常令同学们难以辨别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同学们的知识储备量还不够充足,由于你们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所掌握的史料还比较有限,对史料的辨别和解读能力也有较大欠缺,从而无法准确辨别其文中所引史料是否完整、对史料的解读是否合理、有没有故意曲解史料等问题,以致被其逻辑思路牵着走,并最终接受其观点。同学们都知道,小孩子较容易被哄骗,大孩子就不那么容易被骗,这与你们现在情况是一个道理,我相信随着你们阅读量的增加,以及掌握史料、理解史料能力的提高,你们“识骗”“防骗”的能力也一定会随而提高,从而也就不会再轻易被别人的逻辑思路带走,因为这个时候你们已经成长为有一定独立判断能力的“大孩子”了。所以,同学们要切记,要摆脱困惑或突破障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也没有捷径可走,那就是要求你们尽快丰富和充实专业知识储备,培养和提高学术素养与研究能力,而这一切都是需要你们多读书、勤思考、多练习才得以实现的。
张: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的学术兴趣和方向似乎有点转向学术史,比如您所关注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学术史,您给我们讲述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来龙去脉,您对黎虎先生关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专题访谈,等等。请问李老师,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进行这个“学术转向”的呢?您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否有新的规划?
李:这里,我首先要对同学们说明的是,我实际上并没有“学术转向”,汉唐史仍然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当然,你们所提到的上述情况,也是事实,但它们仍然属于汉唐史的范围。那么,我为什么近几年来比较关注上述问题,并且做了一些梳理性的工作呢?这倒是有必要和你们谈谈。
先来谈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及其相关的“吏民”问题。2005年我发表在《汉学研究》(台湾)上的《孙吴封爵制度研究》一文,就运用过走马楼吴简资料,这也是我第一次利用吴简资料以论证相关历史问题。此后尽管一直对吴简研究都有所关注,但在我的研究中却没有再利用这些资料,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研究重心相对偏向于隋唐史领域,而且主要是隋唐政治史的范畴。2016年,我系统研读黎虎先生《先秦汉唐史论》下册的“吏民”研究系列论文之后,对于走马楼吴简及与此相关的“吏户”“吏民”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深感这是魏晋南北朝史乃到整个中古史领域都值得高度重视的学术问题。在“吏户”“吏民”的问题上,黎虎先生的研究,无论学术观点还是研究思路,都与传统观点“吏户”论者大相径庭,而黎虎先生之所以对“吏户”“吏民”这样的老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并提出全新的解释,也是从对走马楼吴简资料的梳理和剖析开始的。于是,我便决定从“吏户”“吏民”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入手,去验证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学术观点的是非正误。
随着对“吏户”“吏民”问题学术史梳理的深入,我很快就意识到传统“吏户”论的观点不能成立,与之相关的“吏民”问题研究,一些传统观点也存在极大问题。长沙走马楼吴简新资料的问世,为“吏户”“吏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史料,本应有助于推动这些传统问题的解决,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囿于传统“吏户”论的思维定式,这些新资料反而被许多学者用来证明传统“吏户”论的观点,他们多数认为吴简资料进一步证明了“吏户”的存在。在多数学者众口一词地认为吴简资料证明了“吏户”的存在的情况下,黎虎先生综合运用传世文献与吴简资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户”“吏民”进行重新探研,不仅果断抛弃自己早年也认同的“吏户”论,进而在全面否定和批判了传统“吏户”论错误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关于中古时期“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体系性认识。通过对中国大陆史学界 “吏户”问题研究60年学术史的全面梳理和深入剖析,我认为黎虎先生以吴简研究为切入点,对“吏户”“吏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澄清了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在上述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而且构建起一个关于中古时期“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先后完成了《评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及其学术乱象——兼论大陆史学界“吏户”问题研究60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论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学术新体系》(《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3期)、《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户”“吏民”问题研究20年》(《国学茶座》第2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三篇文章,对中国大陆史学界60年来的“吏户”“吏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全面总结。我认为这样的学术史总结,不仅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领域有必要,而且对中古时期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也有必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吏民”问题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你们刚才所提到的“五种生产方式”、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等问题,实际上都和“吏民”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吏民”问题的认识上,特别是在其内涵的界定方面,存在着极大分歧,或认为“吏民”是“吏”与“民”的合称,其中的“吏”是编户齐民之外的特定群体——“吏户”,他们不仅身份低贱,而且一经为“吏”,全家服役,世代承袭,是为传统“吏户”论;或认为“吏民”是编户齐民中有爵位的、富裕的特定群体。针对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不同说法,黎虎先生以“原吏民”为题,通过5篇系列论文科学、全面地阐释了“吏民”的内涵,证明了“吏民”作为中国古代基层民众,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社会结构来说,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各级地方政权管治的基本民众,从户籍制度来说,他们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吏民”作为社会基层民众和国家编户齐民,其经济地位十分复杂,贫富分化现象普遍存在。
黎虎先生对中国古代“吏民”问题的研究为何最符合历史实际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以通识的眼光对此进行研究,而非局限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段,更不是就吴简而论吴简。正是得益于通识的学术视野,黎虎先生不仅对“吏民”问题有了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把握,而且助推其将三国时期的“吏民”问题延伸至整个中国古代时段加以考量,从而促进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观点的形成。黎虎先生在进入吴简“吏民”问题研究不久,就明确指出:“‘吏民问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重要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基础的关键。”(黎虎:《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后来,在一次回顾其吴简研究的谈话中,黎虎先生又说:“我的思路早已跳出‘吴简的范畴,考虑的是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的问题。为什么‘吴简的研究能够促使我考虑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呢?吴简是当时社会最基层的档案资料。过去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多是上层统治者的文字资料,而吴简打开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大门,让你好像身临其境一样。”(黎虎,董劭伟:《独立思考推陈出新——史学大家黎虎先生访谈录》,《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版)可见,正是从关注和研究吴简“吏民”问题开始,黎虎先生开始了他对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并于近期发表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一文,在這篇长达5万余言的宏文中,黎虎先生将中国古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并分别阐述了三个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关系,从而构建起一个关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
我之所以在这里重点陈述了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对我造成了较大影响,我近几年来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吏户”“吏民”及其相关问题学术史进行系统梳理,其机缘也正在于此。在黎虎先生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启发之下,我开始从宏观层面对汉唐史研究进行反思,对未来的学术研究也进行了重新规划,并初步形成了一些想法,例如汉唐职官制度史,我认为就完全有必要进行重新思考,因为既有的汉唐职官制度研究论著,无论思路方法,还是学术体系,都存在着较大缺陷,从而无法对其间与之相关的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给出合理的阐释。不过,由于现在这些想法尚在雏形阶段,还没有形成体系性的认识,待我思考相对成熟之后,再和你们详细谈吧。
张:您在汉唐史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来又兼习中国近代学术史,这也算是“跨界”了吧。能否请您谈谈史学研究“跨界”的问题?
李:首先,你们说我在汉唐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点我真的是愧不敢当,对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尽管从数量上看,我也发表了不少论文,也出版过几本著作,但是我自己真正感到比较满意的论文,也不过几篇而已。我觉得一个学者一生能够写出几篇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文章,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一个学者认为自己的所有论著都是精品,那肯定是在吹牛皮。
至于你们所说的“跨界”问题。我认为这不足为奇,古代史和近代史虽然时段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并无二致。对于近代史领域的某些问题,如果你有幸得到了一些新资料,或者有了新思路,那么撰述成文就不是什么难事。例如我发表的第一篇近代学术史的论文《评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就得益于当时黎虎先生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所提供的新史料;《1938年苏北惨灾与“苏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赈灾救济活动——以扬州新发现之成静生赈灾新史料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吕思勉与张毓英通信汇考——兼谈吕思勉与中国象棋界之交往》(《文献》2016年第1期)二文,同样得益于从朋友那里所获得的一些新资料。除了新资料有助于成文以外,新思路、新角度也可助推我们进行“跨界”研究,例如我还有几篇有关黎昔非与胡适关系问题研究的文章,即将于今、明两年内发表,则是在充分梳理近20年来学界既有黎、胡关系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打破既有研究框架和思维定式,对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进行全面剖析和重新思考,从而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看法。
实际上,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跨界”,在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即便你所研究的是古代史领域的问题,但你在梳理相关学术史的时候,也不免要涉及近代或现代,因为一个学术观点的形成和提出,往往会受到时代的较大影响,甚至成为时代的产物,例如我前面所讲的“吏户”论,其观点何以形成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学者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的深刻影响,传统“吏户”论的学术根源在于“魏晋封建论”,而“魏晋封建论”的理论根源则为“左”的阶级斗争学说,其时为了论证“魏晋封建说”而夸大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压迫剥削以及依附化等问题,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们对包括“吏民”在内的相关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再如,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从20世纪2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算起,迄今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其间各种观点聚讼纷纭,每个不同的时期都有其时代的学风和特点。所以如果你要讨论这个问题,能绕开近代和现代吗?显然不能。以此言之,斷代与分期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边界与藩篱,因为历史研究的方法是相通的,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如果有了合适的机缘,也可以涉足近现代史领域问题的讨论,近现代史领域的学者,同样亦可以关注古代史。“学术公器”,学术研究领域原本就不应该自设藩篱而作机械式的切割,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在学术领域划定禁区领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人为划定学术研究的范围领地,何谈真正的学术研究呢!
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以后,西方学界的术语相继进入了中国学术界,有不少学者热衷于套用这些舶来的词汇或概念以阐释中国历史问题,有人说这体现出了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创新。请问李老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李:你们所说的这个现象,实际上涉及到当今的学风问题。我曾对黎虎先生进行过两次学术访谈,对于当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以及一部分学者热衷于套用西方舶来词汇概念等问题,黎虎先生均畅谈他的一些看法,黎先生的看法约略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1)中国史学界所引入的西方学术语汇和概念,未必适合于中国史学,不一定有助于中国的史学研究,因此,源自于西方学术界的史学研究“碎片化”的说法,不能随意加诸中国古代史学研究领域。(2)中国古史学科领域近年来所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盲目套用舶来的、意涵不清的词语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某些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史问题时,热衷甚至是滥用西方舶来的词语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某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如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议,甚至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3)中国本土固有的词汇或概念,完全可以准确表述中国历史的问题,也只有本土固有的词语或概念所进行的表述,才最有可能贴近中国历史的实际。(4)研究中国历史问题,要尽可能使用本土固有词汇或概念,但并非完全排斥域外引进的词语概念,无论使用本土的还是域外的词汇概念,都必须避免意涵不清、含混模糊,而必须表达准确。黎虎先生的相关详细论述,你们不妨去看一下原文。我这里再简单说几句。
首先,使用西方舶来的词汇和概念,并不是如今才出现的新情况,而是早已有之。例如我们今天早就习惯使用的“社会”一词,就是从英文“Society”翻译而来,但是第一个将这个英文词汇翻译为“社会”的,却是日本学者。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著The Study of Society,传到亚洲后,日本人将它翻译为《社会学研究》,而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严复于1897年也翻译了这本书,取名《群学肄言》。尽管严复将“Society”一词翻译为“群”,较诸日本人翻译的“社会”,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演进历程,但终究还是日本人翻译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将Society对译为“社会”,在中国获得了普遍认同。可见,中国学术界从开始接触西方学术起,所受域外学术话语的影响就比较严重。
及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10年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深入,一大批西方社会、哲学、历史等领域著作陆续被引进翻译,西方的学术概念更为中国学者所知悉,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有相当一批学者从以前的“言必称马列”,转向“言必称欧美”,呈现出明显的“西化”倾向。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似乎“言必称欧美”的风气更盛,亦有学者模仿西方的话语体系,不断创造出一些新名词,从而形成一股“洋八股”的风气,仿佛只有在文章中使用了这些从欧美舶来的新词汇,才能够体现出学术创新,实则大谬不然,对于学术界所兴起的这一崇洋媚外的恶劣风气,有学者已经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其次,我反对“言必称欧美”的洋八股学风,并非完全拒绝西方的学术词汇或概念,对于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以为我所用,但不能不加鉴别地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模仿而生造词汇。例如近来比较流行的“华夏化”一词,就是一个披着传统文化的外套实则拙劣模仿西方学术概念而生造出来的词汇;再如,有的学者在论述北魏末期“六镇之乱”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这个问题时,竟然将之比拟为现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混战及“中东难民潮”,并自诩这是重要的“学术创新”,等等。诸如此类的所谓“创新”,根本就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矫揉造作,除了依靠哗众取宠而一时博得眼球、引起关注之外,对于学术的发展进步没有丝毫的助益。同时,这种纯属靠忽悠、“卖拐”式的标新立异,也是当前浮躁学风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某些学者急于“创新”却又不愿甘坐冷板凳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对此不良学风,你们一定要保持定力,引以为戒,切忌急于求成,需知欲速而不达!
张:李老师,最后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治史心得,给我们一些忠告或鼓励?
李:这里我想借用吕思勉先生集古句而成的一副楹联,和同学们共勉:“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
我第一次看到这副楹联,是在2014年的十月,当时我到常州参加“吕思勉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参观十子街吕思勉先生故居时,我注意到了悬挂在吕先生故居中的这副对联。当时,我以为这是吕先生自拟的一幅勉学楹联,后来看到一些学者的回忆文章中,也将它说成是吕先生所拟。今年年初,因为新冠疫情的发生,得以有大段时间居家读书,在《汉书》中分别读到了这两句,于是追根溯源,弄清楚这两句话原出《礼记》。上句出自《礼记·儒行》:“哀公命席,问于孔子,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下句出自《礼记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
这里,我为什么要特别说到这副楹联的事,并希望以之与同学们共勉呢?第一个想法,就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告诉同学们,读书一定要“求甚解”,特别是对于治史者来说,“求甚解”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无论《汉书》还是《礼记》以前我早就读过,但当时均未曾留意过这两句话,而在吕先生的故居中第一次关注这副楹联,当时就是感觉写得真好,觉得它恰如其分反映了吕先生作为一代史家一种精神境界,并想当然地认为它们是吕先生的自撰之句。而此番再读《汉书》,却注意到了这两句话,进而溯源至《礼记》,袪除了多年的误解。当时我就反省自己,觉得此事可谓教训深刻,告诫自己以后读书一定要追根究源,而不能不求甚解。我希望同学们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也一定要有“求甚解”的精神。
第二个想法,是我觉得这两句话的意思,完全可以灵活化用,并以之作为激励我们研究历史的格言。现在我甚至敢于猜测,当年吕先生也可能是灵活地别解了这两句的意思,以形容自己所从事的史学研究工作。这两句话在《礼记》原文中的意思,前者是说儒者夙夜强学,等待国君向他问询治国之道;后者是说对《书经》有深入研究,就能够做到疏通知远而不犯错误。而我在这里想这样来理解它: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要有夙夜强学的精神和实际行动,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和日复一日的知识积累,我们不仅无需担心别人的不断追问,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治学的道路上不断地追问;有了夙夜强学所带来的学术积累,我们终究能够做到疏通古今、知曉远近,从而在治史的道路不再迷失方向,也不再遭受莫名的困惑了。
在这里,我想把对这幅楹联的“新解”作为治史中的一点心得,与同学们分享。天道酬勤,我相信只要同学们坚持“夙夜强学以待问”,就一定能够做到“疏通知远而不诬”!最后,祝同学们学业有成,前程似锦!
谢谢李老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附记:2020年5月6日(星期三)下午,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文才教授工作室,由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张林君对李文才教授进行访谈,参与旁听者有:扬州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曹万青与硕士研究生卢平、徐艺璇。]
作者简介:张林君,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责任编辑 刘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