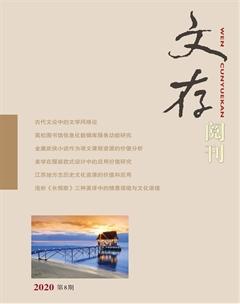《末代皇帝》:历史与想象的交织
李文韬
摘要:《末代皇帝》表现出不同于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影片风格,在看似宏大叙事的框架中,贝托鲁奇实则注重细小叙事,试图展现溥仪个人的心境变化。在此基础上,影片注重个人细节的刻画,通过人为设计的种种意象,影片将对于溥仪的想象详细描摹出来。
关键词:独白型影片;意象;蝴蝶
一、历史叙事
在分类上看,作为一部历史类影片,上映于1987年的《末代皇帝》在中国80年代电影群落中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如果说,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更倾向于依托细小的故事情节来展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那么贝托鲁奇则反其道而行之,通过看似宏大叙事的手段,将小写的叙事、私人的叙事置于叙事中央。这既是他作为西方人对展现历史叙事的独特见解(至少在80年代),也展现出他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思考。
不妨先看贝托鲁奇与“第五代”导演对历史叙事的态度。如戴锦华指出:“自80年代中期始,‘历史便成了大陆艺术电影中萦回不去的梦魇……在80年代的电影叙事中,正是这古旧的舞台,而不是其间剧目与过客,攫取了叙事人凝视的目光。”戴氏以《霸王别姬》为例,对以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历史叙事处理手段进行了分析。所谓“古旧的舞台”指的抽象化、背景化的中国,对于宏大叙事的追求,使得该片的任何一个场景、符号都溢出着“中国”的所指。需要指出,所谓的宏大叙事,其主要定义来源于利奥塔,指的是以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是一种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的现代性叙事方式。陈凯歌的处理手法无疑是符合宏大叙事的定义,由于缺少对历史中的具体事件、人物进行深刻的描摹,导致所有的看似细小的叙事都趋于扁平化、功能化,均服务于展现东方景观的目的。虽然《霸王别姬》中有展现时间性的迹象,但总体看来,影片所意欲呈现的是由无数东方特质构建起的中国景观,也即空间性特征压倒了时间性的表现。贝托鲁奇在《末代皇帝》中试图消解宏大叙事的中心地位,贝托鲁奇在1987年接受《首映》杂志采访时表示:“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不会拍这部影片。”事实上,从贝托鲁奇之前的电影已能看出,他所倾向于探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这在《巴黎最后的探戈》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影片中所展现出的是特定境况下个人的矛盾心理状态,与之相似,我们在《末代皇帝》中溥仪面对乳母离去时的悲伤、追求满洲国重建的决心等片段中能看到同样类型的拍摄手段。
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贝托鲁奇在历史叙事上所作的努力,让《末代皇帝》成为溥仪的独白。从片名已能看出,《末代皇帝》无疑是以溥仪为中心,展现其随波漂流的一生。贝托鲁奇采取时空嵌套的模式,在让观众体验溥仪战后被俘的现时性时间体验的同时,以闪回式的镜头切换技巧,又让观众回顾起溥仪的前半生。全片虽然没有溥仪独白式的表达,但无疑是一部独白型的电影,虽然溥仪无时无刻都处在与他人对话的过程中,但本质上看,其传达出的情感部分甚于思想,这无疑更接近于独白。导演也希望通过溥仪的独白,展现了其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
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以个人独白的形式探讨溥仪的心境变化,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中,必然会导致想象的、戏剧化的、不合理的情节出现。比如影片末尾,溥仪为红卫兵们所推倒之后,满身尘土并未抖落就走进夕阳下的紫禁城,在与少年短暂交流之后,他掏出了自己幼时所藏的蟋蟀笼子,贝托鲁奇在这里安排让蟋蟀从笼中钻出,而溥仪則旋即消失。这个段落无疑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溥仪自己的少年与此时紫禁城中的少年,自己少年时紫禁城的黄昏与此时的黄昏,当时的蟋蟀笼子与此时布满尘垢的蟋蟀笼子,贝托鲁奇以一系列的对比作结尾,寄寓了他自己的感情,同时传达出了他的认知。这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处理手法,贝托鲁奇意欲将影片的结尾塑造成一口大钟,希望观众能“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相较于“第五代”导演所面临的集体困惑,贝托鲁奇并未面临着这个困惑带给他的焦虑,也就无须通过这样一部历史影片来消解所谓的“困境”。也正因为西方导演的身份,相较于80年代其他导演的风格来看,贝氏的处理更具个人风格。
经过与“第五代”的对比以及个人相关影片,我们能发现《末代皇帝》并不能算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影片,即使在主题、人物,甚至影片所聘请的顾问等均试图还原真实的历史。当主体框架上的还原与细节上的想象交织在一起时,溥仪的独白便缓缓展开,观众的视野也就是溥仪的视野,溥仪听到1919年的枪声,观众也听到1919年的枪声。影片所呈现的一切,太过清晰地表明着溥仪的态度、导演的感情,宏大叙事的崇高感被削弱了,个人化叙事的细腻程度相当强烈地迸发而出。
二、作为意象的门、夕阳、动物
《末代皇帝》电影中最重要的意象有三个:门、夕阳与动物。作为两个世界的分界线,门的意象在影片中出现了多次,且多次出现在溥仪的人生发生重大变化之时。溥仪骑自行车来到午门时,卫队长关上大门阻止溥仪走到外面的世界;被逐出宫禁的宦官跪在午门前不得进入;分娩后的婉容为日本兵所带走,溥仪依旧是绝望地呼喊着“开门”。在门面前,溥仪从来未能掌控到主动权,对他而言,门既是外人为他设置的牢门,也是他最后的保护门。因此,我们能发现,当故事越往后发展,溥仪对门也渐趋被动的接受。这扇为他人所建构起的门,终究只能靠他人来打破,所以我们才看到,只有中华民国进驻紫禁城,溥仪才得以走出午门;只有日方被击败,溥仪才走出日军的阴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门的意象在该片中从未有过正面的内涵,即使新世界的大门向溥仪所展开,但在电影开头,溥仪依旧选择关上小门选择自裁;在电影最后,溥仪选择回到紫禁城,回到这扇门后。所有的关于门的意象,通过结尾的点题,一瞬间全部浓缩为紫禁城的门,其他的门几乎全部都是这扇门的变体。只有在这扇门后,溥仪才能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找寻到一个异族在满洲里之外所存在的意义,皇帝的身份对他来说并不是囚徒的属性,而是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的唯一途径。
如同许多人已有指出的那样,贝托鲁奇偏爱用自然光进行拍摄,而夕阳柔和的光影对于人物成像有着极强的提升效果。戴锦华指出:“所谓电影叙事正是‘用光写作的,作为一个视觉语言的单元,我们所强调的,是电影场景、画面中不同光源的设置、光的不同强度、明暗对比与光影变化。这是极为丰富的电影叙事、表意手段之所在。”除了在拍摄效果方面,作为意象之一的夕阳,在这里无疑象征着帝国的晚期,这是由帝师约翰斯顿的名作《紫禁城的黄昏》启发而来,氏著无疑表明着对帝国垂垂老矣的惋惜。从功能性叙事的角度进一步看,影片中所有关于夕阳的镜头,都是紫禁城的夕阳的变体。在影片中,溥仪遭中华民国卫队驱逐离开之时,是在傍晚的夕阳之时;影片结尾处,溥仪参观紫禁城也是在傍晚的夕阳之时。前者象征着帝国最后一丝尊严的逝去,后者则让溥仪的人生末路与帝国的终结发生重叠。与《巴黎最后的探戈》相似,在影片中,贝托鲁奇拍摄让娜和保罗相伴的镜头时,经常选择在夕阳的逆光进行拍摄,渲染了一种温暖却又令人不舒服的光晕,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消极的感受。因此,某种程度上,门与夕阳所承担的功能是相同的,它们在时间、空间上进行合力,让作为建筑物的紫禁城不再只承担故事发生地的职能,它是一座牢笼,是溥仪获得安全感的港湾,是溥仪获得身份确认的重要支撑,也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巨人。
而关于动物的意象,无论是蟋蟀还是老鼠,已有影评者对其进行过探讨,不再赘述,在此,笔者希望着重分析蝴蝶这一意象。在影片中,作为意象的蝴蝶只出现过一次。在溥仪的乳母被强制送走之际,溥仪绝望地感叹道:“但她不是我的奶妈,她是我的蝴蝶。”事实上,凡是经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初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有很大的困惑。在中国的传统诗文中,蝴蝶并非直接象征女性,而是与人生虚幻产生联系,这样的传统无疑与庄周梦蝶的典故相关。而当我们检阅其他相关诗词时,会发现蝴蝶的意象也还会涉及到田园生活。但以上两种含义并非与女性有直接联系,可见其内涵需从西方传统中探寻。
一是蝴蝶与灵魂有联系。有的论者已有指出,psyche在希腊语中有着丰富的含义,可以指代呼吸、生命、灵魂等。在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以及相关的希腊作品中,psyche 则与蝴蝶发生了联系,这一联系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化。但结合《末代皇帝》的故事情节来看,溥仪的意思并不是对自身完整性缺失的叹息,并不是对灵魂被剥夺的愤恨,而是对某个依赖物被拿走的遗憾。因此,以灵魂来解释影片中的蝴蝶并不合适。二是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创作的歌剧《蝴蝶夫人》有联系。如有的论者指出:“《蝴蝶夫人》塑造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成为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原型,指代着无比顺从的东方女性角色。”在《蝴蝶夫人》影片中,这样一个单纯、有魅力又极具牺牲精神的东方女性对她的西方爱人充满着无条件的爱。令人动容的同时,又促使着我们从东方学的视角进行反思,殖民思想经由艺术的媒介进入流行领域,为西方人重新提供了殖民的可能以及冲动。《蝴蝶夫人》中的蝴蝶意象也影响了《蝴蝶君》的创作。从互文性的角度看,《蝴蝶君》中不仅直接提到了《蝴蝶夫人》这部影片,而且片中宋丽伶更是直陈西方对东方的压迫,高仁尼作为西方世界的代表,表达了他对东方女性具有顺从性、被奴役性的幻想。贝托鲁奇在拍摄《末代皇帝》之时,让溥仪脱口说出:“她是我的蝴蝶。”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可謂是影响极大。《末代皇帝》中,乳母的亲生儿子被强制带走后,她的哭诉是无力的抗争,随后她将自己全部的爱给予了溥仪。这不仅显示出她对于权力的服从,在认同自己命运之后,她选择倾尽个人所有,展示出母亲对儿子、下级对皇帝的无条件的爱。然而,贝托鲁奇在这里运用蝴蝶之喻仍然显得十分生硬,这无疑反映出他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源于《蝴蝶夫人》的蝴蝶之喻,反映出的是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设想,一种异域风情的幻想,一种对被统治世界的骄傲情节。贝托鲁奇显然接受了统治者—被统治者的逻辑,认为中国的皇权政治之中,宫廷中的所有人必然对皇帝有着无条件的服从,皇帝的乳母由于兼具了侍从与母亲的双重角色,必然也兼具着服从与施爱两个属性。这样的逻辑一旦成立,就与《蝴蝶夫人》中的蝴蝶联系起来,贝托鲁奇试图以蝴蝶之喻升华溥仪对乳母的感情,但忽视了不同文化间的鸿沟,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蝴蝶意象本身就已经具有了难以摇动的所指。
结语
贝托鲁奇融入了个人浓烈的情感,《末代皇帝》也呈现出与80年代中国大陆电影完全不同的姿态。“第五代”导演对于中国历史强烈的探寻欲望与展现历史现实的立场与贝托鲁奇的个人想法相去甚远。《末代皇帝》某种程度上也是“紫禁城的黄昏”的代名,贝托鲁奇以末代/黄昏与皇帝/紫禁城,以时空并置的方式,将溥仪色彩斑斓的一生展现而出。细小叙事的理念贯穿全片,广阔的历史背景的变化不过是溥仪个人心境变化的触媒,在这之中,中国的历史变成了理解溥仪的参照物,对于溥仪心境的具体刻画也就成了全片的重心。贝托鲁奇自然是以历史作底色,用极具个人化的想象将全片填充完整,影片中出现的种种的意象也经由贝托鲁奇所设计,门是紫禁城的门,夕阳是紫禁城的夕阳,蝴蝶是紫禁城的蝴蝶,在《末代皇帝》中,当历史与想象联袂之时,想象无疑占据了主体地位,这是贝托鲁奇对溥仪的同情,也是他个人的拍摄理念所致。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陈莉:《蝴蝶之死:由〈蝴蝶夫人〉和〈蝴蝶君〉看蝴蝶意象的发展》,苏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