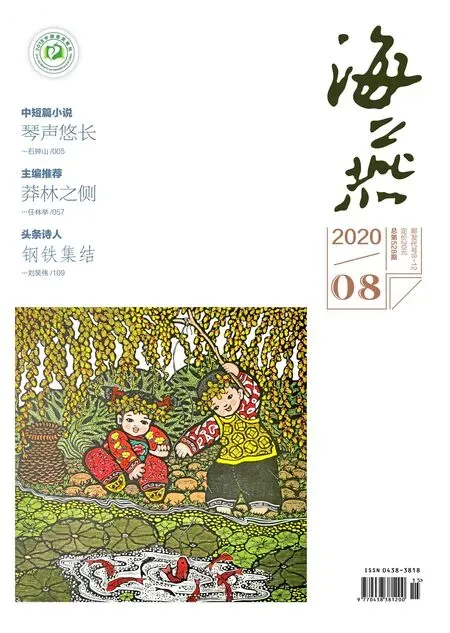宠物蚂蚱
文 卜庆祥
今年夏天,一个雾气沉沉的早晨,白薇家不知从哪里跳进一只蚂蚱。过后分析,大概是从一楼跳上来的,一楼的窗前有一畦菜地,要不从哪来的?
起初,她一点儿也没察觉到有异类的入侵。她习惯早上一起床就去拉窗帘,推开窗子,新鲜的空气可以给她带来一天的好心情。她发现窗台上的一盆姬秋丽受了伤,像被虫子啃过了,圆润的叶片有锯齿状的伤,有的啃了一半儿,滴里当啷即将折断。白薇喜欢养花种草,土栽了十多盆,水生了几十瓶,天上地下,家里像植物园,这些年又摆弄上了多肉植物。
好看的肉肉养在精巧别致的小花盆里,看着看着,白薇看到了一只蚂蚱,正落在一株熊童子上吃早餐。她大叫一声,去找铁镊子,没找到,再回头,蚂蚱没影了。
白薇居住的屋子不大,两室一厅,一个卧室,一个书房,一个客厅,肉肉们被她安排在客厅朝南的落地窗下。
白薇开始找,像当年上小学学校组织春游爬山找宝,一棵树一棵地摇,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翻,找得额头鼻洼布满汗珠,手上沾了不少泥巴。终于,在纱质的窗帘上找到了闯祸的小坏蛋。刚才没有找到铁镊子,她顺手操起了鞋柜旁的电蚊拍,甩掉花缎面拖鞋,蹑手蹑脚地接近它,发动袭击,一拍下去电死贪吃的小坏蛋。
白薇发现它在动,有棱有角的小脑袋挑出两根长须,金鱼一样鼓起的眼睛泛出柔和的光泽,它好像也在端详白薇,身前的小爪子微微抬起,挪了挪身子。
“小可爱,不,小可怜,你是谁,你来我家干什么?”平时,白薇爱跟肉肉们说话,肉肉们是她的小可爱;肉肉们肥嘟嘟的,样子憨,不会点头,也不眨眼,而这个偷吃东西的小家伙却在向她放电,“喂,”她也向它招手,“小可怜,你饿坏了,本宫一眼就看出来了。”
白薇决定开恩饶过它。她从茶几上的盘子捏起一片黄瓜,递过去,悄声说:“我改主意了,我们和好,这可是本宫用来敷脸的哟,给你当零食吃吧。”
奇怪,蚂蚱没有逃走,它乖乖地接受了白薇的馈赠,张开钳子似的嘴,咔嚓咔嚓,大快朵颐。

第二天,白薇给了蚂蚱一块胡萝卜,啃着啃着,它顺着白薇的手指爬到了她的手腕上,白薇全身酥了,“哎呀,受不了你了。”她赶紧把它空运到化妆台上的一个手饰盒里。
她给它吃西红柿、西瓜皮、葡萄粒儿,还让它跟自己吃一样的青椒、小油菜、芥兰。它吃得心安理得,旁若无人,它一点儿也不怕她了。当她躺在沙发上看着金庸老爷子的小说打盹时,它就嗖地跳上来,像疯狂的情人,紧紧地搂抱住她柔荑般的手指。
心情大好,白薇用手机给它拍照片,“喂,小可怜,摆个姿势,小鸟依人的,风情万种的,得了,你那么丑,不拍了不拍了。”
白薇打电话给她的好姐妹,让她们猜自己养了什么。她们个个胸大无脑,张嘴就来,猫,狗,猪,蛇,蜥蜴,蜘蛛,乌龟,一顿胡乱猜,她说都不对。她们问她是什么,她说,你们继续猜,猜对了我请你们吃牛扒喝拉菲。
她和它玩疯了,放任它爬上自己凝脂般洁白细嫩的肚皮,哦,左边的是乞力马扎罗山,右边的是富士山,哈哈哈哈,喂,小可怜,祝你登顶成功,欢呼吧。哈哈哈,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
她邀请它和自己吃同一份外卖。它似乎不感兴趣,无动于衷,结果惹得她大吵大闹。
一天晚上,电闪雷鸣,她梦见了它,它好大好大,像充气娃娃。它死死地搂着她,噬咬她的脖子,她大叫醒来,发出一身冷汗。
或许是受到了惊吓,它玩了一两次失踪。白薇像失恋的少女,痛苦万分,翻箱倒柜地找它,自言自语道:“我知道你去哪儿了,喝酒去了,寻欢作乐去了,找你的小情人去……哦,我错怪你了,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
有一次,白薇把它放在长款圆圈耳环上,带它去了商场。她看好了一件蕾丝花边的性感内衣。她进了一趟试衣间,出来又在收银台扫二维码付了账,等回到家,她就不在耳环上了。她记得把它放在了手饰盒里,手饰盒放在了LV包里……她急忙开车折回专卖店,服务生正笑吟吟地在门口等她。
她动情地哭了。
“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助?”服务生亲切地问。
她以为它丢了,丢在大街上,丢在专卖店,或是快餐店的托盘上,或是车上的真皮外壳的烟缸里。想想,她想不起来去哪儿找它。她的心像被挖了一个洞,空落落的。她用了三天的时间去放弃它、忘记它,她告诉那些快被她的猜猜猜折磨疯了的好姐妹,她的蚂蚱,不,她的小可怜丢了。她们在手机里笑得直嚷肚子疼,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气之下,她去城南的花鸟鱼市买了一后备箱的多肉植物。
其实它没丢。
那天下午三点左右,她从外面回来,在路边的披萨店点了份苹果派,回到家刚刚坐到餐桌前,就发现它落在她的玻璃杯的杯口,正喝着她出门前只抿了一口的橙汁,她啊的一声跳了起来,险些碰倒了椅子。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以为又是发生在梦境中的奇异景象。
它没丢,它还陪伴着她。
她优雅地伸出食指,像在舞池边邀请一个心仪已久的舞伴,而它更像情场老手,踩了弹簧似的跳了上来,紧紧地搂抱着她的手指,还歪着头在她的戒指上无耻地蹭了蹭脸。第二天早上,趁她没睡醒,它又胆大包天地落在了她的嘴唇上,弄得她好痒,“哎呀,你学坏了,敢占我便宜。”
一楼窗前的那一小畦菜地收获了。
秋天了,风凉了,晚上睡觉记着关窗。
白薇喊:“喂,小可怜,你去哪儿了,又去喝酒了,还是去约会你的小情人了,出来吧,我看见你了,你别骗我,你怎么躲着我,我才是最爱你的,宝贝,回到我身边来。”
它没有像往常那样扇动着透明的翅膀飞到她的眼前。她以为它又在逗她,它想让她牵挂,让她孤独,让她说软话央求它。少来,她决定不理睬它。她想,它早晚会回到她的身边。
她用手机循环播放一首歌。
她等了它两天,不,三天。她不得不向她的好姐妹求援,其中有一个没心没肺的还在电话里拿她开玩笑,让她去东南亚的热带丛林领一只大蚂蚱回来做伴。
她打了一个冷战,恐惧生出藤蔓爬满了她的身体。
她甚至考虑是不是报警。
最终,在客厅的长沙发下面,确切地说是在沙发的暗影里,它虚弱地露出半个头,在她看到它的那一刻,它也看到了她,然后,死了。
她伏在餐桌上,抱着头,久久地盯着它。它侧卧在她为它准备的碟子里,一动不动,干瘪,僵硬,扭曲。
她把它抛下楼,楼下的菜地已经没有一点绿色。
看着它小小的躯体在她的手上凌空而起,又疾风般地下落,她闭上了眼睛。貌美如花的她给它取了一个英雄式的名字:小飞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