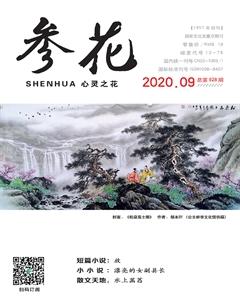浅析《酉阳杂俎》中唐代社会的“生死观”
摘要:《酉阳杂俎》是一部成书于晚唐时期的志怪和民间风俗杂说的笔记小说。在《酉阳杂俎》中承载着一些具有史料意义的文字,它向我们展示了唐朝的风俗人文、社会背景,在这些文字背后承载的是唐朝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取向。本文笔者整理关于《酉阳杂俎》相关篇目,主要集中在《天咫》《玉格》《壶史》《贝编》《诡习》《怪术》《感事》《冥迹》《诺皋记》的内容部分,浅析唐代社会呈现的生死观。
关键词:《酉阳杂俎》 “生死观” 文化
一、《酉阳杂俎》中鬼神故事所包含的“死亡”内涵
(一)“鬼魂”的存在形式与归向
《酉阳杂俎》(卷二·玉格)中介绍了道家鬼魂归处的地府结构;(卷三·贝编)介绍了佛家宇宙观中身体死亡后通过因果轮回和业力的驱动,鬼魂的归处是“极乐净土莲华”或者“地狱”。书中死后世界的构造解答了灵魂的去向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答正是在唐朝所处环境下社会背景中伦理观念、等级观念,以及结合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合理权衡之后的想象。
《酉阳杂俎》(卷十三·冥迹)中有许多幽冥还阳的故事,也是对鬼魂归向问题的回答。故事包括“亡夫韦英回魂抢婚妻子梁氏”“崔罗什误入长白上夫人墓遇鬼姑娘”“顾况长子夭折后再托生顾家子”等。这些故事将生与死看作是一种可以转化的机制,死者可以通过某种过程回归人间和人交往共处,鬼魂重生为人之后依旧受到社会的接纳。面对原始的未知,人做出的本能反应是逃避,然而这种对死亡的世俗化想象,减少了世人对未知的恐惧之感,人死而为鬼也正是这种逃避生理机制下的一种精神慰藉。
(二)神仙鬼怪“人灵的转化”
《酉阳杂俎》的神怪故事还展现了神仙鬼怪、人灵之间相互转化的一种过程。
1.谪仙变成人。《酉阳杂俎》(卷二·壶史)秀才权同休友人,雇佣犯了错被贬谪下凡服役的得道仙人。秀才惭谢雇者曰:“某本骄稚,不识道者,今返请为仆。”雇者曰:“予固异人,有少失,谪于下贱,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复须力于他人。请秀才勿变常,庶卒某事也。”秀才虽诺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雇者乃辞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说秀才修短穷达之数,且言万物无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发,药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1]
2.人死成仙。《酉阳杂俎》(卷二·玉壶)记载的道家异人术士,“太阴练形之术”即是如此。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恶,目光不毁,头发尽脱,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晓、向暮谓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卫肉,胎灵录气,所谓太阴练形也。赵成子后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于内,紫色发外。又曰若人暂死,适太阴权过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内闭,或三年至三十年。[1]
3.通过养生修炼或食用外物之法由人成仙。《酉阳杂俎》(卷十·物异)记载:石驼溺,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落尽得仙。出《论衡》:喝下不明液体,即可伐毛洗髓而成仙。[1]
4.死后转世为人。《酉阳杂俎》(卷十三·冥迹)中顾况夭折的长子,轮回转世又托生顾家的转世灵童的故事展现了这一过程。
出现这种不同形态的转化,与唐代文化交融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佛家自汉代传入以来,和道家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地中国化,如生死轮回的教义,而道家在吸收佛家的理论体系时,也丰富了对往生世界的构建。人与仙的相互转化,人死成鬼后的重生,是道家修行的理论也是佛家轮回观的呈现。唐朝较为宽容的政治环境、开放的思想环境、宽裕的物质环境为当时世人思想中增加了积极乐观的成分,拓展和鼓励了世人的想象力发展,寻仙求道、生死轮回正符合了唐朝百姓在生死问题上的浪漫主义追求。
(三)人与鬼神交往
《酉阳杂俎》中还记载了各种人与鬼怪神灵交往的故事,也反映着唐代的生死观:对生死界限的打破,体现着一种生死共存的状态。如(卷十三·冥迹)记载了选人刘某入京时邂逅志同道合的举人,但次日折回找寻举人时,却只见停着举人尸体的棺材。“于襄阳頔在镇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晤,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支迳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流水涓涓芹努(一曰吐)牙,织鸟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旦,刘归襄州。寻访举人,殡宫存焉。”[1]
鬼不以作为另一种状态而被排斥和异化,也就是说,在唐代的生死观中,对鬼怪神灵的态度不再是敬而远之,而是与之交往共存甚至是融合的状态。不妨把鬼怪神灵视作异体文化的象征,那么在《酉阳杂俎》中唐代社会对于文化多样的包容性也体现出来,这也是生死观中众生平等观念的冒头。
二、《酉陽杂俎》中包含的生命意识
(一)不怕死亡的特例
《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记载了蜂国精灵的故事。两蜂交谈,一蜂:“孔升为君筮不祥,君颇记无?”另一蜂回答:“君已除死籍,又何惧焉?”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人们的思维有了地狱轮回因果报应,在这些思想观影响下衍出了关于生死簿的故事。一叠小小的本子掌握着生死大权,看似十分严格,却可以随意更改,就像此则故事一般。”[2]“除死籍”即消除了其他外力对于生命的威胁,这是《酉阳杂俎》中对于自身命运掌控的一个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没有对死亡的忌惮,是唐代人对于死亡这一状态的坦然接受的心理,也是唐代人民自信精神和生命意识的展现。
(二)化鬼是对超能力理想的追求
《酉阳杂俎》中的鬼神故事,有生前心愿未了如郝惟遇到女鬼张氏,为其迁葬使她魂魄不再四处游荡的故事;或怨恨深刻的人死亡之后化鬼停驻在人间,先秦时有文献记载:“匹夫匹妇强死,其鬼魂犹能凭依于人,以为凌厉。”而使这种鬼不再出来害人的方就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书中厉鬼害人的故事如王申之子被女鬼吃掉,孟不疑目睹张译事骨骸等。
这类鬼怪故事皆是生前执念遗留在鬼怪载体之上的表现,化鬼之后拥有了超越凡人的力量和更顽强的生命状态,这是唐代人生命意识当中,对于超强力量的渴望,是借助超能力实现价值追求的理想。
(三)却鬼行为中的反抗精神
(卷二·礼异)记载:“梁主常遣传诏童赐群臣岁旦酒,辟恶散,却鬼丸三种。”[1]据说所谓“却鬼丸”即是用武都山谷采出的雄黄为主要原料,经过南朝阴阳眼刘次卿验证过功效的驱鬼辟邪药物。(卷十三·冥迹):“魏韦英卒后,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归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惊,张弓射之,即变为桃人茅马。”[1]向子集张弓射鬼也是该书中却鬼方法。
这些面对鬼怪而采取的主动进攻和主动趋避的方法,是唐代生死观中忧患意识的表现。对于鬼怪的观念或许是来自对未知现象的恐惧,对人间类似现象的恐惧,但是在《酉阳杂俎》一书中关于却鬼的描述,是唐代生命意识中反抗精神的表达,即对可能存在的危险,没有消极地逃避,而是寻找各种面对和反抗恐惧的方法,这也展现了唐代民众对生命的热爱。
三、结语
《酉阳杂俎》中包含的唐代社会对死亡内涵的思考和生命意识的展现,离不开唐朝社会辉煌磅礴的社会环境。唐代作为一个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其“生死观”展现着道家关注现实幸福、针对世间的不公平和不安宁的务实精神,佛家远离无常、超脱苦难轮回和注重因果联系的来世展望,儒家追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现世精神价值。这三种“生死观”的共存,是一个时代宽容精神的体现,对于现代精神价值的取向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段成式.酉阳杂俎[M].曹中孚,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苗贤君.《酉阳杂俎》中鬼怪故事的民间叙事研究[D].山西大学,2016.
(作者简介:龚新雅,女,本科在读,西南科技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于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