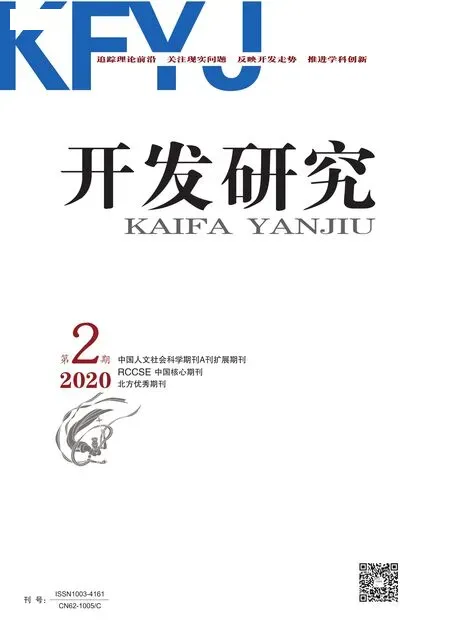从空间经济学学会什么?(上)
[比利时]斯特弗·普罗斯特,雅克-弗朗索瓦·蒂斯(著)
(1.比利时勒芬大学,比利时 勒芬市 3000;2.比利时勒芬基督教大学,比利时 勒芬市 3000)
安虎森,丁嘉铖,王 淞,周江涛(译)
(东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提要:空间经济学的目的是要解释财富和人口在国际和区域从城市到地方的空间分布中存在峰值和谷值的原因,其主要任务是验证导致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向心力和导致区域以及城市经济活动空间分散的离心力的微观经济基础。交通运输在城市和区域两种空间尺度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它重点研究区际货物流、区域尺度的乘客出行和城市尺度的个人通勤。
一、引言
空间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把区位、交通运输和土地纳入到经济学中的问题,这3个概念密切相关且都归入JEL分类系统的R类别。我们将展示给大家空间经济学是如何解决如下议题的:为什么经济活动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分布都不平衡?自19世纪中期开始,交通成本的持续降低以及近乎消失的通信成本,是否意味着距离和区位已经从经济生活中消失了?为什么在许多国家中都存在持续的、相当大的区际差距?为什么厂商会选择劳动力和土地价格都很高的区位?区际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是否有利于提高区际的公平性?城市为什么存在以及为什么存在规模差异?为什么大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和居住成本比在小城市的劳动力更高?在城市中劳动力是否是按技能分类的?道路收费是否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合理措施?我们将讨论从经典的区位理论到空间计量模型的众多的研究方法问题。
空间经济学,既处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也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地位。它处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是因为经济增长一直是具有局域化特征和不平衡特征的空间现象,经济史学家也始终认为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Bairoch,1988;Hohenberg & Lee,1985),因此空间及其相关概念,如区位、交通运输、土地等都成了经济学家工具箱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空间经济学在经济理论(外部效应、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方面仍面临着许多难题,因此空间经济学和它的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交通运输经济学,在高校教科书和研究生课程中常不能作为代表性课程而出现,在过去和现在,它在高校课程体系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一点不值得惊奇。然而,实证检验结果还是令人鼓舞的。
通过夜间影像,弗洛里达(Florida,2017)发现在全球各地分布着681个大都市区,它们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24%和全球产出量的60%。在美国,20个大都市区的产出量大约占美国GDP的50%,人口约占美国总人口的30%。反过来,欧盟28个国家首都地区的产出量占欧盟GDP的23%;巴黎地区,其面积占法国陆地面积的2%,而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19%,产出量占法国GDP的30%。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距离仍然对国际贸易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经济学中常用的实证方法就是把双边贸易流量与各自的GDP和距离联系起来的引力定律。黑德和迈耶(Head & Mayer,2014)总结该定律为如下:如果两国产出量保持不变,则双边贸易量一般与两者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上述这些事实和其他一些事实,与我们的一般认知是不相同的,一般认为我们仍然生活在均衡化的世界中。尽管通信和运输成本急剧下降,但距离和区位的影响还没有从经济生活中消失。迄今为止,在新作用力中自然因素仍占重要地位,然而这些新作用力以其诸多障碍和巨大的不平衡性,正塑造着那些很不均衡的经济景观。
空间经济学还研究其他一些重要的议题。住房和交通运输是与空间相关的典型商品,在家庭总支出中占据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在美国,家庭住房支出平均占家庭总支出的24%,在法国为33%;美国的交通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17%,而法国为13.5%。居住在纽约的人,每年花费在通勤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相当于3~6周的工作时间,对居住在巴黎的居民来讲平均是4周,但这些数字并没有诉说通勤是个人日常生活中最令人不愉快的活动之一(Kahneman et al.,2004)。
空间是人类活动的根基,同时也是以土地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和产出品。世界范围内的土地供给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它远远超过了对它的需求。因此,除了农用地租金以外,地价应该为零,然而实际上居住成本相当高,且其价格不随住房结构和质量发生变化,而是随城市规模和城市组成成分而发生变化。根据奥伯里、埃利希和希恩(Albouy,Ehrlich & Shin,2018)的研究,在2006年(也就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城市土地总值已超出美国GDP的两倍。这意味着城市土地价格反映不同于土地本身的某种稀缺性。
区位是通过商品流、人流(通勤者和乘客)、生产要素流(资本和劳动力)以及信息流等各种类型的流动相互连接起来的,因此人们认为贸易理论应成为最为关注空间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贸易理论所关注的是非常诡异的地理现象,即国家之间实际上相邻很近以至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运输成本近乎等于零,然而现实是距离足够远以至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无法在国家之间自由转移(Leamer,2007)。这种研究策略完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俄林很早以前挑战了上述传统观点,他指出“除非国际贸易理论与一般区位理论有关且作为其一部分,否则无法理解国际贸易理论;对一般区位理论而言,如果缺乏商品和要素流动,也难以被人们所理解”(1968(1933),p.97)。虽然晚了一些,但引力法则终究让那些国际贸易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自由贸易并不意味着无成本贸易。
经济学家和区域学家早已提出不同的理论和模型用来解释各种空间聚集体的存在,但这些理论和模型是不相同的,不过至今并没有明确指出其区别。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展示能够解释大量的空间聚集现象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区域、城市和交通运输经济学。区分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并不那么简单,我们认为主要区别在于所涉及的空间单位不同。
区域经济学关注的是商品和生产要素在一个大的一体化空间范围(如国家或贸易集团)内的转移问题。由于区域经济学关注的是在那些几乎不存在溢出效应的全球范围内的议题,且区际商品贸易又存在贸易成本,因此区域经济学主要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上述议题进行分析。由于市场价格没能准确反映个人决策的社会价值,因此货币外部性显得非常重要。直到目前,区域经济学忽略土地要素,因而区域经济学也被认为是不包含土地的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家研究城市形成、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社会构成问题。城市规模和专业化部门不同,因而也就出现了城市体系。土地利用是城市运行的关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有关土地利用的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显示技术外部性。
交通运输经济学涵盖了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两个学科,但有所不同。从区域角度来考虑,交通运输经济学研究国际和区际输出(入)货物运输和乘客(商务出行或休憩旅行)运输。从城市角度来考虑,主要研究利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通勤问题。大多数交通运输经济学把厂商和家庭区位视为是给定要素,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失去了衔接,因为在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中区位是内生确定而不是外生给定的。因此,一方面需要交通运输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或城市经济学之间的结合,另一方面也需要交通经济学之间的相互融合。空间经济学文献很少关注交通运输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反之亦然)。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问题,这种权衡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空间经济。除此之外,我们还讨论了引起无数争论的问题,即如何更好地描述空间竞争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引用了一般均衡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第三部分关注了“区域问题”,也就是关注了像意大利那样在区域之间存在人均GDP方面的巨大的、持久的差距的现象,或像欧盟那样巨大的空间不平衡导致巨大的区际贸易障碍的现象。人们一直不缺乏对区际差距的猜测,然而克鲁格曼首次提出很成熟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了在市场背景下如何在稳定均衡中产生区际差距的问题。一旦开启这种过程,则将产生“滚雪球效应”,影响力将不断自我强化。
我们沿着克鲁格曼的研究思路,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与贸易理论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厂商和家庭的流动性。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十年间,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关注减弱了。然而,得益于新的分析方法的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又获得新生,且其主要观点已得到空间计量模型的验证。此外,新经济地理学的关键参数是运输成本,所以这种方法自然是研究贸易和交通运输政策对经济活动区位影响的首选方法。
在第四部分我们继续研究城市,城市是空间不平衡的极端表现形式。城市经济学,在阿朗索、米尔斯、穆特(Alonso,1964;Mills,1967;Muth,1969)的开创性研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关注的是单中心城市模型,在该模型中,就业主要聚集在城市中心商务区。但这个模型有一个优点,它强调城市内的非贸易品对居住活动的重要性。然而区域经济学主要关注的仍是贸易品,因而仍保留了传统的贸易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对城市经济学就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至今还没有出现减弱的迹象。城市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单中心城市模型是以完全竞争范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最近,人们的兴趣已转向研究厂商和家庭主要聚集在少数几个城市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城市不仅是承接经济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参与者。聚集经济解释城市存在以及城市规模重要性的原因。交通拥堵是城市的主要问题,交通运输经济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五部分,我们讨论了可用来融合发展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各种模型,包括城市系统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第六部分提出了未来研究的一些建议。
尽管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经验研究上,但本文的重点仍放在理论问题上。《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五卷的内容,主要以近来的富有见地的实证研究文献为主(Duranton,Henderson,and Strange,2015)。相反,来自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成果已经被遗忘,或在不同的条件下重新被发现。还有,现有的空间经济学理论之间是毫无相关的,这需要综合这些不同的理论。我们在这篇综述中要展示的是,当今技术水平已足够先进以至可以勾画出能够吸引更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统一的研究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实证研究。为了突出我们的关注点,我们选择了与我们的讨论直接相关的一些理论。
二、何为空间经济学特有属性?
在这个部分,我们首先在不考虑纯地理因素的情况下讨论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问题,接着我们介绍作为空间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规模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问题。然而,很遗憾的是这种权衡无法纳入到竞争性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就解释了空间异质性、空间外部性以及不完全竞争等一些标准化的假设对该领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最后我们讨论了厂商的战略性区位选择问题,这是空间均衡分析的基础。
(一)地理学是否很重要?
据戴蒙德(Diamond,1997)的研究,可食用植物(富含营养物质)和野生动物(可被驯养帮助人们进行农业耕作或作为交通工具)的空间分布差异可以解释仅有部分区域能成为食物供应中心的原因。尽管贸易和城市的发展与一些地区产生文明的原因有关,但我们还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在工业革命后为什么贸易和城市的发展如此迅速的问题。
一些自然特征确实会导致区位之间的巨大差异,并对空间经济组织产生深远的影响(Gallup,Sachs,and Mellinger,1999;Boske and Buringh,2017)。纽约和洛杉矶是美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两个港口城市,这或许并不是偶然的。然而,莫斯科和巴黎分别是欧洲顶级城市中的第一位和第三位,但在出海通道和其他自然条件方面并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从历史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地理因素来解释这两个城市的重要作用。在这篇综述中,我们将遵循着廖什(Lösch,1940)、胡佛(Hoover,1948)等空间经济学奠基人的研究思路。对于这些作者(或者对我们)而言,在日常研究工作中的首位问题,应是通过分析空间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解释形成不同类型经济聚集区的原因,有些空间经济力量促使经济活动空间聚集,有些促使经济活动空间分散。否则,这些空间是无法通过自然和政治因素区分开来的。以这种方法为基础,我们提出几个基础性问题:经济主体做出的一系列微观决策所带来的宏观空间结果是什么?推动厂商和家庭聚集或分散的主要作用力是什么?交通运输成本和通勤成本等空间障碍是如何影响经济格局的?
这种选择并不能说我们具有某种偏见。我们确实认为自然要素对空间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最近的富有见地的一些研究中,亨德森等(Henderson et al,2019)指出,夜间灯光作为经济活动水平的代表性指标,其区内变化的35%与自然地理相关,而剩下的65%需要由空间经济学存在的原因来解释。而且,我们同时也承认自然要素不能解释像东京、纽约或上海等这种大都市区存在的原因。地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城市会出现在何处的问题,但它不能解释为何存在城市的问题,尽管这两者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解释经济活动的实际区位,那么还得考虑自然要素。据艾伦和阿科莱基斯(Allen & Arkolakis,2014)的研究,2000年美国区际收入变动的20%可以用地理要素来解释。
地理学也通过一些精妙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选择空间尺度。经济学家经常交替使用区位、区域或地点等不同的或很不清晰的词汇,此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词汇通常对应着不同的空间单元的事实。因此,经济学家也将会承担着某种结论对某一空间尺度而言是有效的而对另一种空间尺度而言是无效的风险,因为聚集力或分散力可以在地方层面上发挥作用但不一定在全球层面上同样能发挥作用。
(二)空间经济学的基本均衡
在这一部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基本均衡问题,该均衡在所有空间尺度上都适用(Fujita & Thisse,2013)。该均衡背后的机理是容易理解的。如果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则厂商在不损失任何效率的情况下可以把生产活动扩散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此时运输成本降到零。这种经济被称为“庭院资本主义”,也就是此时星期五无法帮助鲁滨逊克鲁索。如果运输成本为零,则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厂商将把生产活动全部集中在几个大工厂里,从而从高效率中获益。这种反例证实了空间经济学基本均衡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它反复提及许多次,且至少可以追溯到廖什的研究。我们现在简要地讨论在该均衡背后的两个主要观点并把它作为本综述的基本法则。
1.规模经济对经济活动区位具有重要影响
理解规模收益递增的合乎常理的方法是假设工厂运行至少需要最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这就产生管理费用和固定成本,而这些费用和成本通常是与大规模生产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规模收益递增对企业而言是内部的。同样,本地化的公共品通常是通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如消防站和公共医院)或通过建设公路网或地铁网络等形式向消费者提供公共服务的,因此实现收益递增的方式与上面是不相同的,此时规模收益递增对厂商而言是外部的而对厂商所在的当地环境而言是特有的。从一种方式到其他的另一种方式,收益递增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但其基本观点是相同的,即每个厂商都因其他厂商的存在而收益。
收益递增现象的存在对空间经济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即不是所有的物品都能随处生产。从这种意义上讲,区位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许多活动变得很“自由”,但许多国家的很多地区没有经济活动,或者只有少量的经济活动。我们绝不能因为运输成本很低(以货币或非货币形式度量)而得出区位不重要的结论。正好与此相反,因为规模收益递增,低运输成本使得企业对区位间细小的差异相当敏感。似乎所有这些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低廉的运输成本使得企业间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因此企业更加关注的是一些区位优势的细微的变动,而不是因高运输成本壁垒而得到保护的环境。
2.商品流、人流以及信息流的成本仍然很高
大量的个人服务是不可交易的,也就是它们必须在生产地消费。此外,已建成的公路、铁路或住房等都是无法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运输成本是无穷大的。
商品。引力方程的大量估算结果表明,距离是商品区际交换的巨大障碍(Henderson,011;Head & Mayer,2014)。亨德森和冯·温库珀(Henderson & van Wincoop,2004)估计,商品从产地到目的地的平均运输成本占生产者价格的170%,这个数值已经很高了。不过,它还包含零售成本,故价格飞涨了。但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目前连区内贸易品生产也已开始趋向于本地化了。希尔伯里和赫梅尔斯(Hillberry & Hummels,2008)分析美国单个制造业厂商运输数据发现,需要运输的商品数量和工厂—目的地对子数量随距离的增加而急剧减少,离工厂4英里半径范围内的总货物运输价值等于该距离范围外的3倍。
人口。据我们所知,相对于那些在引力方程基础上的贸易研究而言,目前关于人口迁徙的综合性研究还相当滞后,尽管一些文章指出人口迁徙还存在受到引力作用的迁徙障碍(Kennan & Walker,2011)。由于人口流动受经济的、无形的、持续的和特殊因素等众多因素的制约,人口流动研究相对于贸易流研究难度更大。在研究美国各州1950—1990年间经济变动的一篇经典文章中,布兰查德和卡茨(Blanchard & Katz,1992)指出,“主要的调整机制是劳动力流动而不是创造就业机会或就业机会迁移,反过来,劳动力流动似乎是对失业变动所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对消费性工资的反应”。另一方面,博斯奎特和奥弗曼(Bosquet & Overman,2019)根据英国1991—2009年间的家庭面板数据指出,只有43.7%的劳动者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工作。
许多人持续居住在贫困地区,这应该是那种迁移成本是最重要的主张的重要证据。由于家庭纽带、社会关系、缄默信息、语言以及文化的差异,人们对待迁徙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个体间是完全相同且完全可流动的,则根据空间均衡条件,实现均衡时可以实现区际效用的均衡(参见Alonso,1964;Henderson,1974;Roback,1982的开拓性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假设大大地简化了分析,但它并不是没有缺陷的。例如,劳动力完全流动意味着当地劳动力供给是具有无限弹性的,反过来,劳动力不能完全流动就意味着当地劳动力供给具有有限弹性。必须谨慎理解个体劳动力具有完全流动性假设的理论与实证含义,因为劳动力迁徙成本影响福利、住房和工资的空间套利条件。利用离散选择模型描述迁移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信息。令人很惊讶的是,在一些特定经济活动中,信息方面的障碍仍然很大。尽管媒体一直强调经济全球化,但经验证据表明,在解释贷款合同设计时,借贷双方之间的距离仍然是很重要的(Hollander & Verriest,2016)。同样,尽管长途旅行会带来高昂的机会成本,但肯定会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让商务人员远赴海外进行洽谈。吉鲁德(Giroud,2013)证实,新航线的开通减少了总部和工厂之间的旅行时间,这使得美国多元化的厂商的生产力提高7%。坎潘特和亚纳吉扎瓦-德罗特(Campante & Yanagizawa-Drott,2018)的研究表明,通过长途飞行(超过六千英里)而建立起来的乘客之间的良好关系,会给欧洲主要枢纽带来更多的商务联系和资本流,且促进了交通枢纽附近地区的经济发展。
转移成本的存在对空间经济组织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转移成本的存在意味着较近的东西比较远的东西更加重要。在存在经济活动不可分性的情况下,支付转移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需要接近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地点。因此,厂商和消费者都处在由推力和拉力组成的系统中,他们所偏好的区位正好是该系统各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时的位置。
上述讨论使得我们可以解释空间经济学的基本权衡: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是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和由人口、商品转移、信息流产生的成本之间处于均衡状态的结果。
本综述贯穿整篇的核心思想就是均衡。上述均衡是实现聚集力和分散力平衡的关键,且对所有尺度的空间(城市、区域、国家和大洲)而言都有效。波梅兰兹(Pomeranz,2000)考察在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和中国工业革命失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资源的地理分布后指出,上述均衡与发展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西北部的煤炭产地和拥有大量熟练劳动力的长三角地区之间的距离很远,因此运输成本很高以至无法把煤炭运到能够把它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高技能劳动力手中。相对而言,英国的运输距离很短,煤炭产地、技能劳动力和煤炭需求之间相互接近,然而当时煤炭运输成本很高,知识也主要通过口头传播,这些使得英国钢铁和金属制品相关产业从规模经济中获益。
(三)空间和一般均衡
1.空间不可能定理
空间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之间关系的历史既复杂又晦涩难懂。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充斥着类似于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等为简化分析过程而置之不理的许多难题;它之所以晦涩难懂,是因为在过去50年,为澄清这些关系而进行的多次尝试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混乱和困惑。然而,正如下面的例子所指出的那样,直觉的论证过程是非常简单的(Koopmans and Beckmann,1957)。

因此,如果竞争均衡存在,则空间不可能定理意味着每个区位的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如果没有充分理由辨认出那些区位对生产商是不合适的,或者经济活动是完全可分的,那么各种经济活动都可以在任意小的规模上进行,且运输成本减少到零。与此相反,如果生产活动是不可分的,那么一些商品必须在不同区位之间进行交易,此时最佳的生产区位就取决于其他生产商选择的区位。言外之意,价格体系必须同时执行两个不同的任务:(1)支持区际贸易(出清各区位的市场);(2)避免生产商和消费者进行转移。空间不可能定理告诉我们一石二鸟是不可能的。从区位稳定性角度来看,支持贸易的均衡价格传递了错误的信号。因此,价格体系没有传递任何代理人所需的信息。要重视下述的不可分性对上述主张的重要性:劳动力就业或生产商从事活动的土地将集中在一个区位上。也就是说,每个代理人在空间中都有自己的“住址”。
2.空间异质性
可以利用多种方法来解决空间不可能定理带来的影响。一种是像在李嘉图贸易模型中的那种利用外生的空间异质性来处理的方法。在李嘉图的模型中,生产商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条件下以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生产,这就反映了区域的技术比较优势(Eaton and Kortum,2002)。不可否认,诉诸空间异质性来消除这种影响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例如,城市的就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商务区,这使得人们根据一般竞争分析框架研究单核心城市结构(参见四部分(二)),然而此时人们又忽略为何存在这种中心的问题。如果假设一些区位拥有一些特性使得该区位上的生产商的劳动生产率比在其他区位上的生产商高,则这无异于给出了我们想要解释的为什么存在劳动生产率空间差异的问题的答案。但即使有一些合适的区位能够组织特定的生产活动,然而这种仅仅依据比较优势来解释巨大的城市聚集体和大流量贸易流的存在,等于扮演了不是王子的哈姆雷特。
为完善起见,进一步考虑一下上述例子。现在假设区位A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具有优势,而区位B在服务设施方面具有优势。此时,将存在有关区际贸易的竞争均衡,因为生产商和劳动力都偏好多样化的区位属性。这种假设和结果,与我们致力于要辨认的那些使生产商和劳动力聚集在一起的条件是相矛盾的。相比之下,我们承认在实证研究中需要考虑区位优势和自然优势(Diamond,2016;Lee and Lin,2018)。然而,我们还是要注意避免不应发生的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摆脱空间不可能问题的另外两种理论,它们已成了解决空间经济学中许多发展问题的基础理论。在区域经济学领域,该理论以垄断竞争和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它曾在20世纪90年代以“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1991)的标题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巨大关注。在城市经济学领域,空间外部性因格莱泽等(Glaeser et al.,1992)以及亨德森、孔克罗、特纳(Henderson,Kuncoro,and Turner,1995)的杰出的工作,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然而在继续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强调在空间和产业组织文献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观点,即空间将导致特殊类型的寡头垄断竞争。绕行是很重要的,但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后续章节中的模型选择问题。
(四)空间竞争
卡尔多(Kaldor,1935)在评论张伯伦(Chamberlin,1933)的书时指出,消费者在空间中的分散分布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塑造空间竞争,即不管行业内厂商数量如何,每个厂商与靠近自己的厂商的竞争相对于与远离自己的厂商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市场后来描述为空间竞争市场,这种市场已经偏离了完全竞争环境。可以如下论证:消费者在空间上是分散分布的,因此他们是可以选择不同的线路到同一厂商购买消费品的。消费者从该厂商购买时支付的价格是最低的全价,该价格等于标注的价格再加上交通成本。这就意味着每个厂商对居住在附近的消费者具有某种垄断力量,这使得厂商在实施其营销战略范围内可以决定自己的价格。
最早分析这个问题的是维克里(Vickrey,1964)和贝克曼(Beckmann,1972),他们研究了在一维空间中等距离分布的同质厂商是如何为吸引在相同空间中均匀分布的消费者而展开竞争的问题。每个消费者购买一单位商品,交通成本与出行距离成正比。厂商i在其左右两边Δ距离处各有一个相邻厂商。当交通费率t很高时,厂商i是当地的垄断厂商,因为对居住在接近厂商i-1和厂商i之间中间点附近的消费者而言,在其他厂商处购买商品的价格太高了。反过来,当t很低时,每个厂商都与它两个相邻的厂商为吸引位于他们之间的消费者而展开竞争。此时,厂商的市场力被其附近厂商的行为所削弱,换句话说,厂商空间上的分散分布使得厂商只在局部范围内具有垄断权力,因为消费者是否购买该厂商的商品就取决于相邻厂商制定的价格。
如果厂商i降低其价格,则将极大地影响消费者对与它相邻的两个厂商的需求,这样这两个厂商也会降低自己的价格。厂商i-1和厂商i+1的行为通过连锁反应又影响厂商i-2和厂商i+2的行为。这种市场结构,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寡头垄断市场。在这种市场结构中,每个厂商只关注少量竞争者的行为,在本案例中是关注两个厂商的行为。维克里和贝克曼指出,此时的市场结果由唯一的纳什均衡给出,在该均衡中,所有厂商都收取相同的价格p*=c+tΔ,其中c表示共同的边际产出成本。因此,空间分散赋予厂商市场力。具体而言,如果交通费率t或者厂商间的距离Δ变小,或者两者都在变小,则厂商间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故厂商收取的价格较低。如果是交通成本为零的极端情况,则在波特兰模型中那样,厂商根据边际成本来定价。维克里和贝克曼的研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萨洛普(Salop,1979)等学者在产业组织领域展开研究,才开始关注空间竞争模型。
那么在空间竞争情况下,厂商如何选择生产区位?霍特林(Hotelling,1929)在其开创性文章中给出了答案。在霍特林模型中,有两个销售商选择其销售区位,他们首先要确定在主街道的何处设店的问题,霍特林对其进行简单扼要的陈述后讨论了如何确定售给消费者的价格的问题。单个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不连续的,即一个消费者只在一家厂商处购买商品;而厂商总需求对价格而言是连续的,除非一个厂商削减另一个厂商价格的情况。假设可以忽略每个消费者的具体行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不连续的个体需求和连续的总需求之间的矛盾。霍特林认为一个完备的市场环境,要有采取竞争性行为的“侏儒”(消费者)和战略性行为的“巨人”(企业)。
霍特林的结论是,空间竞争导致两家厂商在市场中心背靠背分布。如果该结论成立,则给我们提供了那些向分散化的消费者提供商品的厂商的空间聚集的基本原理。然而,遗憾的是霍特林的分析有一个错误,即当厂商之间足够接近时,厂商之间展开价格博弈,但在纯策略集合中没有这种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使得他的主要结论就不成立。达斯普利蒙特、加布斯泽维茨和蒂斯(D’Aspremont,Gabszewicz & Thisse,1979)通过假设消费者的购物成本为距离二次方的函数,修改了霍特林模型。该假设抓住了时间的边际成本随出行距离的增加而增加的观点。在修改后的模型中,达斯普利蒙特等证明任何价格博弈在纯策略集合中都有唯一的纳什均衡。把这些价格和利润函数结合起来,则厂商选择主街两侧端点处为其生产区位。换句话说,厂商选择彼此分离的区位销售同质商品,因为地理上的分散分布缓解价格竞争。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产业组织的文章重新审视了上述这些议题。但主要信息是比较简单的,即如果双寡头垄断厂商销售的商品在纵向或水平特征上具有明显的差异,那么市场中心区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区位。当出行成本很低时,地理上的分散布局也不能避免厂商之间的竞争。由于厂商间竞争是通过产品差异化而得到缓解的,因此厂商可以布局在市场潜力很大的地方。此外,在人口密度分布为对称和钟状情况下,安德森、戈里和罗默(Anderson,Goeree and Ramer,1997)指出,厂商向人口密度最高的市区中心转移。城市中心人口密度越大,则均衡区位就越接近城市中心,厂商索取价格就越低。因此,厂商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反过来则更加接近众多的消费者。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看到,本地市场效应也是以邻近和竞争之间均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两阶段博弈方法很难处理多家厂商参与博弈时的情况。另外,如果消费者偏好多样化,那么将发生市场区相互重叠的情况。这意味着厂商不再具有天然的腹地,但可以留住来自不同市场的消费者。德帕尔马等(De Palma er al.,1985)认为,通过多项式逻辑回归分析可以构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消费者并没有从最便宜的商店或最近的商店购买,相反,他们个人的需求按照类似于引力法则的规则,平滑地分布在各个企业之中。让α(>0)表示用随机项标准差来表示的消费者偏好的分散程度,且假设标准化后主街道长度为一单位距离。若消费者个人选择是相互独立的,则在此基础上,德帕尔马等给出了如下有关厂商地理集中的结论:如果α≥2t,那么在n(≥2)个厂商同时博弈时的纳什均衡处,同时聚集数量为y*=1/2的厂商,且其索取价格为p*=c+αn/(n-1)。
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者的多元化偏好足够稳定(α足够大),以及出行成本足够低(t足够小),则厂商选择市场区中心布局,索取超出边际成本的价格。
当出行成本没有足够低以至无法满足α≥2t条件时,将发生何种情况?大泽、赤松和高山(Osawa,Akamatsu,and Takayama,2017)最近重新审视了霍特林模型。他们假设在圆周上等距离地分布着有限数量的点,一组销售差异化产品的厂商均匀分布在每个等距划分的点上。当厂商都以同样的价格销售其差异化产品时,如果t很大,则厂商将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区位上。但如果t持续下降,则厂商将聚集在那些数量不断减少而规模不断扩大的商业区里。最终,当t足够小时,所有厂商将聚集在一个区位上。我们将在下一个部分看到区域经济学的一些模型可以推导出类似的主张。
空间竞争模型传递重要的信息,即相邻的竞争者的影响比远距离的竞争者的影响大。这些竞争模型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们非常适合研究空间竞争中多方面的问题。厂商是无法分割的,而且厂商通过尽可能接近消费者进而降低消费者购物成本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因此这些空间竞争模型概括了空间经济学中的基本均衡问题。可惜的是,这些空间竞争模型依赖相当具体的理论假设,并在局部均衡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当这些模型一般化或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中时,就会变得很难处理。尤其,纳什均衡存在性证明是相当棘手的问题。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空间竞争模型①已被证明是在零售业部门进行实证研究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参考阿吉雷拉维里亚和铃木2016年的调查)。
(五)选择何种建模策略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避免空间不可能定理的影响和空间竞争模型的陷阱,那么我们应诉诸垄断竞争框架或具有空间外部性的完全竞争框架。即使没有什么理由阻止我们根据手头上的问题使用任何一种建模方法,然而我们发现根据所考虑的空间尺度大小选择建模策略是比较合理的。空间范围总是有限制的,因此当研究像城市内部问题的那种局域性问题时,交易活动与消费外部性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城市经济学假设完全竞争并遵循技术外部性的原因(第四部分)。外部性的好处是它与完全竞争以及规模收益不变相一致,这意味着均衡时的厂商利润为零。如果所关注的是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则此时不存在溢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学是以内部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相组合为基础,描绘生产要素流动所致的货币外部性(参考第三部分)。在内部规模收益递增背景下,垄断竞争厂商的利润为零,这就意味着厂商所有的收益全部支付给生产要素了。
三、区域问题
人们的福利水平,同样受到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影响。交通运输领域或贸易成本中的冲击会影响厂商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因此,在把握好代理人迁移到其他区位还是留在原地的反应基础上,评估贸易和交通政策的全面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讨论经济活动区际分布是如何随运输成本和那些关注度较少的其他一些作用力的变化而变化的问题,我们还将叙述本地市场效应和核心边缘模型,接着我们以厂商和劳动力的区际转移为基础,分析如何评价区际新的交通运输设施建设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一)何种力量导致区际不平衡
标准理论指出,不论在何处,生产要素都会获得相同的回报。如果每个区域都赋予相同的生产函数,则资本从资本丰饶因而获得较低回报的区域转移到资本稀缺因而可以获得较高回报的地区,资本通过这种方式对市场的非均衡性做出反应。如果消费品价格在各个地方都相同(也许是因为贸易障碍已经被消除),则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以及均衡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和资本回报率在各个地方都相同,因为此时区域间实现了资本劳动比的均等化。
然而,我们离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世界还很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克鲁格曼(Krugman,1980,1991)完全抛弃标准模式,提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厂商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主张。克鲁格曼的这种主张,是把迪克西特和施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97)的以垄断竞争为基础的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和冰山交易成本相结合而提出的。消费者是同质的且都具有多样化偏好,这种偏好可以用CES效用函数来表示。不同于前面讨论的空间竞争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假设了大量的生产差异化产品或可交易的服务业产品的厂商,这就排除了厂商间战略性互动的可能性。每种产品都由单个厂商生产,每个厂商都利用固定的且不变的劳动力边际需求生产一种产品。厂商数量是由厂商自由进出所决定的,且每个厂商都有唯一的生产区位。如果某种产品从区位A输送到区位B,且必须要保证一单位产品到达目的地,那么就必须从区位A起运τ(>1)单位的产品。如果τ=1,则意味着运输成本为零。运输成本是由在运输途中“融化”而损失的τ-1部分,再乘上区位A的该产品的价格所决定的。因此,τ越大,运输成本就越大。这种由萨缪尔森(Samuelson,1954)提出并称为冰山交易成本的巧妙的处理方法,不用直接处理而是把不同运输部门实际的运输成本合并为一种运输成本。尽管如此,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五)中看到,冰山贸易成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1.本地市场效应
假设一下包括A、B两个区域,K单位资本和L单位劳动力的经济体。每个劳动力都拥有一单位劳动力和K/L单位的资本。劳动力在区域之间是不可流动的,区域A的人口份额为θ(>1/2)。资本在区域之间是可以转移的,资本所有者总是寻求最高的回报率,投资在区域A的资本份额λ是内生的。劳动力市场为局域化的市场且很完善。
在这种框架下,厂商的区际分布受到方向相反的两种作用力的影响。聚集力来源于厂商对接近市场的欲望,这使得厂商很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并节省运输成本,分散力来自于厂商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避免竞争的欲望(Krugman,1980;Fujita,Krugman,and Venables,1999;Baldwin et al.,2003)。这给空间经济学的基本均衡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在第二部分讨论过),且前面讨论的基本均衡变为邻近—竞争均衡了。解决这种均衡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资本所有者通过改变投资区位的方式影响每个区域的区内竞争强度,这使得进口商品进入该区域更容易或更难一些,又反过来影响每个市场的营业利润。由于营业利润重新分配给资本所有者,因此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决策进而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影响需求的空间分布,这又影响厂商区位。
当两个区域的资本回报率相同时,这种聚集力和分散力的推拉系统达到均衡,结果是市场规模更大的区域拥有超比例的厂商份额,因为这个区域可以较低的平均成本进行生产且消费群体的规模也很大。但同时规模较大区域的竞争强度也较大,这使得一些厂商仍然留在市场规模较小区域。大区域因其市场规模优势无可争议地比小区域吸引更多的厂商。没有预想到的是,初始的规模优势进一步得到放大,也就是均衡时的资本份额λ超过了人口份额θ。由于(λ-θ)K>0,资本从资本稀缺区域转移到资本丰饶区域。这种效应被称为本地市场效应(HME)。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厂商之间在劳动生产力方面是存在差异的(请参见伯纳德等(Bernard et al.,2007)的综述)。重要的是,本地市场效应可以推广到异质性厂商当中,这些厂商根据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位于相互分离的市场当中;那些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厂商将位于规模较大的区域,但他们承担着很大的竞争压力;那些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厂商将位于规模较小的区域,以此避免那些来自与高生产率水平厂商竞争中的毁灭性打击(Nocke,2006)。厂商的空间选择将导致区域之间在生产率水平方面的差异。此外,本地市场持续发挥效应,就意味着一些生产率较低的厂商也将陆续转移到那些高生产率厂商集中的市场规模较大区域(Okubo,Picard,and Thisse,2010)。赛弗森(Syverson,2004)根据美国混凝土产业的数据发现,低效率的厂商在高竞争性市场中很难生存,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仍存争议(Combes et al.,2012)。
叙述上述这些贡献的目的是要分离出市场规模对厂商区位的影响,尽管相对工资水平差异随运输成本的变化而变化,但可以假设各区域的工资水平是相同的。随着厂商聚集在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该区域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这导致区域A工资水平上升。由于区域A的消费者享受更高水平的收入,因而扩大了对商品的需求,这对位于区域B的厂商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这种工资水平的提升又导致了一种新的分散力,这种分散力就是许多关于发达国家非工业化争论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发达国家很高的劳动力成本问题。高桥、高冢和郑(Takahashi,Takatsuka,and Zeng,2013)在比较成熟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指出,区域A的均衡工资水平要高于区域B的工资水平。此外,本地市场效应仍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即使规模较大区域的工资水平很高,但对厂商区位决策而言,市场准入条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区际运输成本的降低如何影响本地市场效应?乍一看,在运输成本很低时,接近大规模市场的临近性对厂商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但事实恰恰相反,当区际运输成本下降时,许多厂商将选择规模较大区域。这种有点儿似是而非的结果可以这样理解,即运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规模较大区域向规模较小区域出口产品,同时运输成本的下降也减弱了那些空间分割给规模较小区域带来的厂商间竞争较弱的优势。这两种影响导致更多厂商聚集在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这意味着规模较小区域成了有利于规模较大区域的非工业化区域。因此,本地市场效应可能给交通政策带来意想不到的潜在影响,即新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会降低双向的货物运输成本,这可能促使厂商离开规模较小区域。这个结果可能使得那些忘记高速公路是双向的人感到很吃惊。
可惜的是,本地市场效应不能轻易地扩展到多区域体系中,因为没有合理的评价标准对“超比例”的产业份额进行评价(Behrens et al.,2009;Matsuyama,2017)。多区域体系导致的新的基础性要素是进入分散化市场的可能性随着区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仅有两个区域时,只通过区际商品贸易成本的变化可以了解总体的影响,但当存在两个以上区域时,运输网络的全局或局部变化都可能导致极其复杂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随运输网络结构和形状的变化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五)中看到。
有了这种警示,则对有关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证据混在一起的现象不会感到很吃惊(Davis and Weinstein,1999,2003;Head and Mayer,2004;Hanson,2005;Costinot et al.,2019)。然而直觉而言,我们有理由期待本地市场效应所强调的作用力应在现实世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如何对此进行检验?尽管无法观察价格进而无法检验本地市场效应,但大量的证据表明市场准入与经济活动水平密切相关。从雷丁和维纳布尔斯(Redding and Venables,2004)的实证研究开始,大量的实证研究已证实了地区经济绩效与地区市场潜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市场潜力定义为以距离体现的当地GDP总和或就业人口总和。雷丁和斯特姆(Redding and Sturm,2008)把1949—1990年期间东德和西德的分离作为一个自然实验,研究了当离国界很近的西德城市失去市场准入条件时,这些城市的发展受到何种影响的问题。他们发现,在1949—1990年期间,离东德边界很近的西德城市的人口增长远远低于远离东德边界的城市的人口增长,这是市场规模效应很好的例子。在详细的述评后雷丁(2013)指出,“在市场准入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之间不仅存在相关性,还存在因果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实证研究所利用的市场潜力是地区吸引力的近似值(Head and Mayer,2004)。
本地市场效应解释了规模较大的市场吸引厂商的原因。然而,这种效应没有解释某些市场规模为什么比其他市场规模大的原因。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解释。第一,劳动力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导致一些区域的市场规模比其他区域的规模大。第二,每个区域的内部结构决定区域能承载多少厂商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第一种情况,后一种情况将在第五部分进行讨论。
2.核心边缘结构能否成为稳定均衡
研究厂商聚集的合乎常理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对称和稳定状态开始,然后把聚集的形成看成是打破对称机制作用的结果。由此产生的非对称分布将涉及产业聚集的一种峰值,可以视它为产业集群。然而直到克鲁格曼(1991)才提出了一个很成熟的一般均衡机制。更具体地说,克鲁格曼找到了一系列条件,使得在对称世界中,厂商和家庭对称分布在两个区域的格局由稳定状态变成为不稳定状态。
构建核心边缘(CP)模型,同样依赖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框架(D-S)以及冰山交易成本。核心边缘模型与本地市场效应(HME)的区别在于在核心边缘模型中劳动力是在区域间可以进行转移的。资本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结果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就是克鲁格曼货币外部性的起点。劳动者转移到新的地区,则给这些地区带来了生产和消费能力。具体地说,劳动力类似于资本,在其居住的地方从事生产活动,但同时也在此地进行消费,这与资本所有者的情况不同。因此,劳动力的迁移引发了生产和消费的转移,因而改变了迁出区域和迁入区域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相对规模。这些效应受到市场的影响因而具有货币外部性的特征,当然移民做出转移决策时并没有把这些考虑在内,因为每个移民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些效应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尤其重要,因为价格没有真实地反映个人决策的社会价值。因此,研究劳动力迁移的总体影响,需要一般均衡框架,这个框架不仅反映了产品和劳动力市场间的相互作用,还反映了个人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
克鲁格曼(1991)在考虑利用第二种类型劳动力的另一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后,在基本模型中增加了一种分散力。农民在空间上是不能转移的,且均匀地分布在两个区域。因此,他们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依赖于他们居住的地区得到满足。当农业产品的贸易成本为零时,区际收益均衡使得农民对制造业产品有相同的需求函数。这种需求的分散促使厂商选择不同区位进行生产,因为它们在供应当地农民方面享有邻近优势。
乍一看,如果工业劳动力是可流动的,那么以下两种影响可以导致制造业部门聚集在一个区域。首先,如果一个区域的规模更大,则本地市场效应表明该区域能够承载更大比例的制造业厂商,这使名义工资提高。其次,更多厂商的存在意味着本地生产的商品种类更多,因而本地的价格水平较低,这就是生活成本效应。相应地,该区域的实际工资水平较高,这吸引更多的工业劳动力。这两种影响的结合导致了循环累积因果过程,促使厂商和工业劳动力聚集在一个区域,即聚集在核心区,另一个区域将变为边缘区。
虽然这个过程看起来是导致了“滚雪球效应”,但是能否像本文预测的那样持续发展下去是不确定的。上面的讨论忽略了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人口迁入区增加的劳动力供给往往降低人口迁入区域的名义工资水平。此外,当地对可贸易商品的需求增加,导致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但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提高往往降低厂商的利润水平以及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因此很难预测对名义工资的最终影响。除此之外,当厂商聚集在核心区时,在边缘区的销售额也将下降。当然,这些影响的共同作用也可能导致“雪球融化”效应,即导致厂商和劳动力的空间分散。
事情的发生顺序可能如下。首先,劳动力选择他们的就业区位;其次,在人口区际分布已知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生产活动。对于产业聚集或分散的特定条件而言,运输成本证明是关键因素。一方面,如果运输成本很高,那么区际商品运输相当困难,这就强化了分散力。于是,出现生产活动的分散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厂商主要关注本地市场。另一方面,如果运输成本很低,那么厂商会聚集在核心区,厂商在这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区域出售更多商品,但也不会失去规模较小区域的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厂商可以享受规模收益递增带来的好处。劳动力的转移会加大本地市场效应,因为本地市场规模随劳动力的迁入而变大。因此,核心边缘模型就是要研究区际收敛或发散的可能性,尤其是研究那些初始很相似的两个区域为什么最后变成很不相同的区域的问题。克鲁格曼的研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区域差异最终成为一种稳定均衡,而这又是大量的经济代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做出决策的结果。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有关核心边缘结构的结论:假设劳动力是可流动的,如果运输成本足够低,则制造业部门或可交易的服务业生产部门将聚集在某一个区域,否则,将均匀分布在两个区域。
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传递给我们的主要信息是,在规模收益递增情况下,如果降低运输成本,那么一些区域通过扩大自身市场规模大于其他区域市场的方式,建立起自身的比较优势。
如果经济代理人是可以移动的,那么供需计划因劳动力重新选择就业区位而以极为复杂的形式发生变化。因此,核心边缘模型不可能存在完整的解析解,这倒不使人惊讶。这就是克鲁格曼诉诸数字模拟的主要原因。随后的发展证实了克鲁格曼的结论,但是证明这些也花费了很长时间。尽管正规的稳定性分析是从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1999)的研究开始的,但直到罗伯特-尼克德(Robert-Nicoud,2005)才给出了有关空间均衡的详细证明。
克鲁格曼的研究激起了巨大的研究热潮,但这些众多研究的质量是有差异的。接下来,我们简洁地讨论核心边缘模型的一些缺陷。
(1)核心边缘模型阐述了产业聚集的原因,但没有预测出产业聚集在何处的问题。的确,当运输成本很低时,制造业部门会聚集在区域A或区域B。处理这些问题的合乎情理的方法是赋予一个地区比较优势。例如,当区域A的农民数量超过区域B的农民数量时,西多罗夫和泽洛伯德克(Sidorov and Zhelobodko,2013)的研究表明,产业持续聚集在区域 A所需的τ值的取值范围总是大于聚集在区域B所需的取值范围。当区域A的农民数量足够大时,不管运输成本如何,就存在唯一的一种均衡,即所有厂商都聚集在区域A,这就揭示了比较优势如何使得市场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倾斜的基本原理,但它也并没有排除产业聚集在其他区域的可能性。戴维斯和温斯坦(Davis and Weinstein,2002)在他们的一篇论文中记载了日本城市恢复聚集的能力。日本的城市在二战中遭到大规模轰炸,然而战后,一些城市的人口和制造业迅速恢复到二战前的水平,甚至广岛和长崎也在25年后恢复了战前的增长态势。
尽管一些区域的规模优势很小,但核心边缘模型告诉我们,如果滚雪球效应开始发挥作用,那么这些区域也会变成为核心区。但对此种情况而言,历史而不是比较优势成为在不同均衡中选择某种均衡的重要因素。例如,19世纪交通运输技术的应用使得在美国一些特殊的地点,例如船只或货物运输可延续到通航水道之间陆地的地点,形成了“陆上运输城市”。布利克利和林(Bleakley and Lin,2012)发现,尽管这些城市失去了原有的优势,但大都保留了原来的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总之,地理和历史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经济活动区位。
(2)从分散到聚集的突发性且不连续过程,是假设工业劳动力同质且对实际工资边际变化的反应都相同所导致的结果。劳动力对实际工资变化的反应就像劳动力在波特兰寡头垄断模型中对降低边际价格的反应是一样的。如果人们意识到个人对人口转移的非货币属性采取不同的态度,那么这种聚集过程将会得到减缓。此外,劳动力对原地的依赖性也是一种很大的分散力。当市场充分整合使得实际工资差距低于那种乡愁导致的效用损失时,聚集过程将翻转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一体化先促进发散后促进收敛,换句话说,经济是按照“钟状”的空间发展曲线发展的(Tabuchi and Thisse,2002)。这说明劳动力的异质性假设和同质性假设将导致相反的结果。
(3)核心边缘模型的福利分析,尽管它很简单,但它所传达的是含糊不清的信息。由于不完全竞争,均衡并不是最优的。然而,市场结果的低效率并不能告诉我们厂商和人口在规模较大区域的聚集是过度还是不足的问题。聚集或分散两种结构都不是帕累托最优,因为在核心边缘模型下,居住在边缘区的工人总是偏好分散,因为他们是进口所有商品的,然而居住在核心区的人们总是偏好聚集,因为本地生产多样化的产品。换句话说,市场一体化通过经济活动区际重新配置,既提高了福利水平也损失了福利水平。
核心区的工人和农民的福利水平高于边缘区的福利水平。因此,通过利用市场价格和均衡工资计算应支付给因迁徙而获利或损失的人的补偿额度的方式,也就是利用补偿机制来评估有关人口转移的社会价值(Charlot et al.,2006)。当运输成本很低时,获益者可以补偿损失者,使他们能够维持在分散状态下应享有的效用水平,因为此时厂商提高效率而获得的收益高到足以抵消边缘区劳动者的福利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区际差异成了用高效率可以补偿的地表上的对应事情。然而,如果运输成本取中间值,那么无法提出明确的建议。这种甚至在克鲁格曼的简单模型中也没有明确结论的状况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在有充分理由相信基本原则为正确的情况下也存在如此多的相反观点的原因。
(三)区际差异的演变:可选择的方法
如果在其他背景下研究核心边缘模型,则它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启示?
1.投入产出联系
为了很好地解释以低劳动力流动性为主要特征的大型产业区的形成,有必要超出克鲁格曼模型范围以便寻求其他的解释。在这个方面,核心边缘模型的主要缺陷是它忽略了中间投入品的重要性。消费品需求并不能完全解释厂商的高销售额,消费品需求对厂商销售额的影响不如中间投入品需求对销售额的影响。因此,当进行区位决策时,中间投入品生产商关注最终消费品生产商的区位是合乎情理的。同样,最终消费品生产商也密切关注中间投入品生产商的区位。这就是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研究初期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很精炼且富有启示性,即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将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因为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也聚集在该区域,反之亦然。假设大量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聚集在某一区域。该区域对中间投入品的大量需求对中间投入品生产厂商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核心区又以较低的价格供应中间投入品,这又吸引大量的最终商品生产商向核心区转移。这样,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断得到加强,由此而产生的产业聚集完全可以用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来解释,而不用诉诸像克鲁格曼模型中的劳动力流动。
赋予中间投入品生产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区别于核心边缘模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它要求我们要关注现代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其他的作用力。但要关注的是,一旦劳动力不能流动,那么大量聚集某一区域内的厂商将提高该区域工资水平,这就导致方向相反的两种作用力:一方面,核心区消费者高收入水平扩大了核心区最终需求,正如克鲁格曼模型中的情形一样最终需求导致聚集力,但它不是由人口规模扩大而是由收入水平提高所致;另一方面,核心区高收入水平又导致新的分散力,这是很多有关发达国家非工业化争论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这些国家很高的劳动力成本成了一种分散力。在这种情况下,厂商重新选择边缘区,因为边缘区的低工资足以抵消低需求带来的影响。因此,随运输成本的下降,生产活动先聚集后分散。总之,经济一体化导致钟状空间发展曲线,它描述了在发展过程早期阶段区际差距上升,在后期阶段区际差距下降。
2.劳动力技能
在核心边缘模型中,农民无法获得能够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技能。然而,当对无法移动的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一种类似于核心边缘模型中的机制发挥作用。为了揭示该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先考虑一下制造业部门利用资本和熟练劳动力来进行生产的情形。资本可以移动而劳动力不可移动。如果一些厂商转移到新的区位,则居住在该区位的非技能劳动力将具有接受高水平培训的强烈意愿,因此技能劳动力数量增多,这将吸引更多的厂商迁入。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升,又促使最终消费品需求的上升。因此,该区域吸引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反过来又促使新迁入的厂商雇佣更多的熟练劳动力。再有,即使所有劳动力不流动而留在原地,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仍持续着滚雪球效应,它促使所涉及的厂商和技能劳动力逐渐集中起来,这意味着经培训后的部门间流动性取代了要素的空间流动性。正如在核心边缘模型中的情形,如果运输成本很高,则制造业生产部门将分散,如果运输成本很低,则制造业部门将聚集(Toulemonde,2006)。这种结论给出了空间非均衡性存在的主要原因,即人力资本的非均衡分布,这些我们将在第四部分再次进行讨论。
3.制造业技术进步
之前的模型只关注运输成本下降。毫无疑问,交通运输部门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当然,其他部门也经历了劳动生产率的惊人的提升过程。这样,田渕、蒂斯和朱(Tabuchi,Thisse and Zhu,2018)根据制造业的技术进步,重新设定了核心边缘模型。此外,他们承认劳动力是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转移成本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散力发挥作用的。在核心边缘模型中,区际价格和名义工资水平差异随运输成本的下降而缩小,因此实际工资差距将缩小,这就减弱了促使人口迁移的激励作用。当运输成本下降到门槛值以下时实际工资差异将发生变化,这样就可以得出类似于克鲁格曼的结论。相反,在田渕及合作者的文章中,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将降低两个地区的劳动力边际需求(分别是固定的边际需求),如果某一个区域的规模比另一个区域规模较大,那么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和降低当地现有产品的价格(分别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和扩大产品品种数量)的形式,进一步增强规模较大区域的吸引力。当生产率水平提升足够高以至区际效用差距大于劳动力转移成本时,劳动力开始转移到规模较大区域。因此,技术进步趋向于扩大两个区域之间的差距,进而进一步激励劳动力从规模较小区域迁移到规模较大区域。简言之,制造业技术进步导致聚集。
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性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更大。创新需要技能劳动力,因此田渕及合作者的研究表明,核心区可以承载更多的技能劳动力。这使得如下问题显得相当清晰,即是否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是减少区际差距的有效途径?不一定。通常支持劳动力迁移的论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的同质性假设。然而,劳动力并不是同质的,可转移的劳动力通常是具有高技能的劳动力,又是该区域中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当落后地区失去最有技能的劳动力时,那些仍留在落后地区的人们的处境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和福利的区际差距主要由技能和人力资本的区际配置差异所致。例如,法国50%的区际差距可以由人力资本区际差异来解释(Combes,Duranton and Gobillon,2008)。我们将在第四部分(一)和第五部分(一)中再讨论这一问题。
(三)超出两地区框架
1.轨道经济
在本地市场效应研究中提到的维度问题也出现在核心边缘模型中。在两区域框架下的完全聚集并不意味着在多区域框架下也聚集在一个区域。赤松、高山、池田(Akamatsu、Takayama and Ikeda,2012)和池田、赤松、小野(Ikeda、Akamatsu and Kono,2012)研究了轨道经济。假设劳动者和厂商等距离分布在圆周C上的2n个区域中,农民在圆周C上均匀分布。任意两个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随着这些区域在圆周C上的相对位置而发生变化。初始,运输成本足够高以至制造业在2n个区域之间均匀分布为稳定均衡。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将出现劳动力和厂商聚集在2n-1个间隔区域的现象。当运输成本持续下降时,核心边缘模型将出现分叉序列,其中制造业区域的数量将减少一半,且每一对相邻的制造区域之间的间距在每次分叉后都加倍增加,直到制造业部门全部聚集在一个区域为止。因此,在核心边缘模型中所描述的聚集过程对于分布在圆形空间中的一些区域而言仍然有效。然而,完全聚集(完全分散)只有在运输成本很低(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空间经济模式是丰富多彩的,制造业相对聚集在少量的区域,或相对聚集在较多的区域。
同样重要的是,在聚集过程中,一些区域一开始市场一体化进程就开始衰落。相反,其他一些地区,在开始衰落之前通过大量调整运输成本,吸引大量的厂商和劳动力。换句话说,一些区域可能先受益于运输成本的下降,然后持续失去厂商和人口。简单地说,市场一体化的赢家和输家都随经济体内部的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发生变化。
2.连续区位
解决维度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在无缝世界中使用无限多的区位的方法,这是杜能、霍特林或贝克曼所采用过的方法。直线是最简单的同质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可以显示出或多或少专业化和聚集化的空间模式。在两区域、两部门框架下,区域专业化和空间聚集是并行的。然而,利用无限空间是以技术上难以解决的模型为代价的。
据我们所知,罗西-汉斯伯格(Rossi-Hansberg,2005)是第一次尝试把大量的区位、实际运输成本以及聚集力和分散力引入在一体化框架内的学者。区位在区间X=[0,1]内有序排列,区域是X的一个连通子集;有两种生产部门,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和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每一个生产部门都生产同质产品;两种生产部门主要投入土地和劳动力。
罗西-汉斯伯格假设,中间投入品生产商和最终消费品生产商在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以及遵循指数衰减率的产业外部性条件下进行生产。生产最终消费品的厂商需要中间投入品厂商的产品,而中间投入品生产厂商又以最终消费品来支付购买劳动力和土地所需的成本。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和两部门间完全自由流动。厂商需要土地,但消费者不需要土地。这样,分散力将产生于最终消费品生产商和中间投入品生产商之间的土地竞争。
在连续区位的情况下,市场出清条件显得非常重要。商品的运行规则可以描述如下:如果两个区位之间存在贸易,则可以看成是中间投入品生产区位x(x∈X)从[0,x)处输入商品。在区位x,此处的产出量加上输出量或减去输入量,然后把剩余总量从区位x运输到(x,1]处。均衡时,x=0处和x=1处的商品剩余必须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在区位x处的商品价格取决于在整个贸易过程中发生的贸易量和损失量,而这种贸易取决于所有厂商的区位,反过来又取决于运输成本和溢出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运输成本很高时,罗西-汉斯伯格(2005)指出此时没有贸易活动。因此,此时每个地区都是包含两种类型厂商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然而,如果运输成本下降,则更多的区域参与到该贸易体系中来,区域专业化将会得到加强。尤其是当中间投入品的运输成本下降时,这种产品的价格趋近于最终消费品生产商的价格,因而其利润水平较低,然而随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厂商可以从强大的空间外部性中受益。此外,当运输成本趋近于零时,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和(或)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将聚集在一个区域。简单地说,较低的运输成本提高了区域专业化程度和产业的分散化程度。这些结果与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在后者的研究结果中,运输成本的下降先促进产业的聚集和专业化,后导致产业的分散。导致这种相反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厂商间争夺土地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一种强大的分散力(参见第四部分)。
(五)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制造业部门和(或)运输部门的技术进步趋向于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而所有这些过程都诉诸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因此,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似乎是区域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忽略了经济活动空间聚集通常以城市的形式出现的事实,区域经济学忽略了经济活动空间聚集产生的各种成本。然而,解释这些成本可能对从核心边缘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有重大的影响。具体地说,赫尔普曼(Helpman,1998)曾指出,如果分散力来自于住房保有量而不是不可转移的农民,则降低运输成本将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而不是空间聚集。在这种情况下,住房竞争抑制了聚集过程,因而推翻了克鲁格曼的预言。两种结论的区别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劳动者转移到规模较大区域,则该区域的房价上涨,这加强了分散力。同时,低运输成本促进贸易。这两种作用力结合起来,则可以看出运输成本稳步下降时经济活动是如何发生分散的。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看到降低运输成本不利于消费者聚集在同一城市或地区,因为较低的运输成本带来了与城市运行相关的消费者的各种拥堵成本(参见罗西-汉斯伯格(2005)的关于不同但相关的机制的解释)。因此,区内和区际发生的事情是理解区域问题的关键。到目前为止,最稳健的结论是,降低运输成本则会像克鲁格曼主张的那样促进集聚,然后像赫尔普曼主张的那样导致分散(Tabuchi,1998;Puga,1999;Fujita and Thisse,2013)。
(六)交通运输是否对区际经济很重要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供应常常被认为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灵丹妙药。在这一部分,我们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讨论这一问题。在本部分,在阐述交通运输网络在经济活动区位中的重要作用后,我们更加仔细地定义了运输成本,因为运输经济学给区域经济学家带来了一些惊喜。接着,讨论了评价运输基础设施对经济活动影响的方法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将讨论两种方法,由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导出的结构方程方法,以及精简型方法。这两种方法有助于我们验证许多经济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最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经济学问题,即是否有证据表明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很明智的投资策略。
1.运输网络:它们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考虑三种不同但同样稳健的结论。
(1)给定由一组节点和一组连接线所组成的运输网络,我们考虑一下那些通过交通网络节点输入原材料和输出产品的厂商。从参数角度对数量和价格进行处理,则利润最大化的区位问题就变为总运输成本最小化的问题。由于在节点处可以实现装卸费用的最小化,故运费率随距离增加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最佳区位是运输网络的节点处(Hurter and Martinich,1989)。换句话说,那些道路上所有可能的区位集合缩小成节点子集,即一个集镇、一个资源性城镇、一个十字路口等,这种节点子集就是最有区位。如果对交通网络的特定节点赋予不同强度的中心性,那么新的交通连接线有利于一些节点,但不利于其他节点,这使得一些厂商重新选择生产区位。

(3)在东非和西非建立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为前殖民地国家向海外发达国家出口其矿产资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邦法蒂和普尔赫克(Bonfatti & Poelhekke,2017)指出,与拥有矿产资源的内陆国家相比,拥有矿产资源的沿海国家从国外进口的矿产相对较多,而从邻国进口的相对较少,因为从邻国进口矿产品则需要与邻国建立交通联系才能使邻国向该国出口矿产。这表明殖民时期建设的运输网络仍然影响着非洲目前的贸易密度和贸易的基本特征(参见杰德沃布和莫莱迪(Jedwab & Moradi,2016)的论文)。简而言之,早前建立起来的交通运输网络持续对经济活动区位产生影响。
考虑到这些,我们可以相信交通运输网络对空间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交通运输地理学家长期以来所争论的(例如,参见托马斯(Thomas,2002)的论文)那样,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取决于那种通过以最短路径连接各种区位进而能够降低货运成本相对价值的交通运输网络的结构。
空间经济学家感兴趣的主要的交通运输问题有哪些?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区域经济模型都显示出交通运输部门以多种方式影响经济。因此,任何在运输部门发生的事情都会对空间经济产生影响。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空间经济学和交通经济学却以一种毫无相关的方式发展起来的。第二,似乎存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引起无休止的争论的鸡与蛋问题,即新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区域增长,还是区域的快速发展促使该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一个问题与运输成本的含义以及如何建模和计量密切相关。由于存储和运输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此对厂商来说重要的是物流成本水平,物流成本可以解释存储和运输两种成本。目前运输成本受到很大的关注,但我们应该记住,服务贸易占世界出口的1/3,在国内贸易的情况下,服务贸易所占的份额可能更大。服务贸易需要不同的运输方式和通信渠道,它可以以电子方式交货,也包括在大型公司分支机构之间提供的服务。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新的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被认为是对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补救措施,因而这是需要实证检验的问题,但这种经验性问题常常包含着重大的政策性含义。
2.界定区际运输成本
贸易和空间经济学文献都承认存在各种类型的空间摩擦,但通常假设冰山运输成本足以反映这些摩擦。但如果把冰山运输成本纳入到不变替代弹性需求函数中,那么此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需求函数本身而不是替代弹性。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设在建立运输部门影响空间经济模型中的重要性问题。
据我们所知,交通运输经济学至今还没有讨论过冰山运输成本。在相关文献中,处理运输成本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假设给定价值装载量的运输成本由几个仿射成本函数的下包络线给出,其中每个函数表示的是与运输模式相关的运费成本。在这些成本曲线中,截距最小的是汽车运输而最大的是航空运输,而且这些曲线的斜率随运输规模和运输服务频率而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这些成本为内生运输成本。一般来说,交通运输经济学家强调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但至今冰山运输成本没有考虑这些影响。第一,运输方式。要区分不同的运输方式,它们是根据市场结构和技术加以区分的。第二,密度经济。运费率随运输量的增加而下降。第三,距离经济。运费率随运输距离的增加而下降。
那么,为什么空间经济学家不考虑这些影响的重要性呢?第一,各国内部的贸易超过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但大多数贸易和经济地理学文献假定国内运输成本为零。在同一国家内两个区域之间运输货物和在两个国家之间运输货物的成本是不相同的。劳动力和资本在国内的流动性大于国家间的流动性,因此尽管运输成本下降幅度相同,但厂商和劳动力所在的不同区位对这种变化所做出的反应是不相同的。出人意料的是,专门讨论这些题目的文献很少。例如,贝伦斯等(Behrens et al.,2007)重新讨论了一个国家由两个区域组成的核心边缘模型。他们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福利的影响取决于两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布局状况。这可以解释为密度经济促使这两个国家在内部经济活动布局上相互依赖。实际上,每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组织状况影响着贸易量,而贸易量反过来又影响运输成本,进而影响各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布局。尤其,一国政府的运输政策可能对其贸易伙伴的内部布局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为制定交通运输政策时应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依据。
第二,如果结合CES偏好,那么冰山运输成本假设意味着如果把生产商制定的价格减半,那么商品交货价格也降低50%。换句话说,运输成本转嫁效应为100%。这与空间定价理论相冲突,在空间定价理论中,为把市场范围扩张到偏远的地区,是可以允许免收货运费用的,且经验证据也表明不可能把运输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例如,德洛克等(De Loecker et al.,2016)的论文)。因此,冰山运输成本无法完全反映厂商采用的众多的定价模式。然而,在第三部分(一)(二)讨论的主要结论,在具有线性需求函数和附加运输成本的情况下仍然成立,这就意味着货运费用是可以免收的(Ottaviano and Thisse,2004)。
第三,如果视运费率为外生变量,那么交通运输部门是完全竞争的黑箱;如果视运费率为内生变量,那么交通运输内生地影响经济活动区位。反过来,贸易量随厂商区位的变化而变化,这影响垄断承运商设定的运费率。换句话说,经济活动区位取决于承运商的行为,而承运商本身的行为又取决于厂商和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模式(Behrens,Gaigné & Thisse,2009)。库姆斯和拉福凯德(Combes and Lafourcade,2005)对法国的研究以及温斯顿(Winston,2013)对美国的研究都表明,放宽管制是降低运费率的关键。
最后,由于冰山运输成本τij的值在区域i和区域j之间是一个给定的先验常数,因此冰山运输成本函数不能解释密度经济。另一方面,当区域数量有限时,由于τij的值是任意选择的,因此冰山运输成本函数可以用来考虑距离经济。然而,正如藤田、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1999)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一样,在连续区位框架中利用这种函数是相当困难的。当一单位某种产品从区域i运到区域j时,只有exp(-tD)部分到达目的地,其中t(t>0)为度量距离衰减效应强度的指标,D为区域i和j之间的距离。因此,成立τ≡exp(τD)。单位运输成本等于货物在区域i的价格乘以途中损失的数量,也就是等于τ-1=exp(tD)-1。因此,连续冰山成本函数是距离D的递增凸函数。这就给了我们曾没人注意过的新的启示:由于边际运输成本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故把距离D范围内的一段行程划分成相互连接的几个子区间,则运输成本较低。换句话说,上述这种函数就等于假设不存在距离经济。此外,由于运输成本的迅速提升,偏远地区市场的重要性减弱了。因此,像汉森(Hanson,2005)的研究那样,只有在有限范围内模拟影响区域经济活动的外生冲击,并不是很奇怪了。
总而言之,所有因贸易而导致的空间摩擦可以归纳为单一的冰山贸易成本的假设,并不是一个无害的假设,主要原因是单位运输成本由区域经济结构内生决定。具有一些讽刺意义的是,虽然经济地理学强调制造业部门规模收益递增的重要性,但它又忽略了交通运输业也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特征的事实(Mori,2012)。交通运输部门存在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这应放在空间经济学家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上进行考虑。
3.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区域经济活动
雷丁和特纳(Redding and Turner,2015)认为,在方法论上存在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鸡和蛋的问题。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很高的地区很可能会得到基础设施建设,既然这样,那么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内生而不是外生的。其次是要确定基础设施条件良好的区域创造了新的经济活动,还是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吸引了其他区域的经济活动的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那些可能正发挥作用的产业转移机制。当建设以区域A和B之间贸易联系为主要目标的基础设施时,如果该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区域A的经济活动强度,那么可以实现区域A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吸引厂商从区域B转移到区域A,或者从另一个区域C转移到区域A。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要同时评估一条运输线路运输成本的变化对所有区域的影响。
目前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估测,人们也熟悉这些方法的优点和缺点(Holmes,2010)。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考虑到与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例如,那些不受新的交通基础设施直接影响的区位,可以通过重新配置劳动力间接受到影响,而这些重新配置的劳动力主要指原先配置在那些能够降低运输成本的一些最低成本路线上的劳动力。这种方法是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由于它包含区域和城市经济,故在第五部分(二)对此进行讨论。
结构方程方法也是被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中的方法,但它只能估计那些从一般均衡框架中推导出的几个方程。与空间计量方法相比,结构方程法的优点是它是估计而不是测度。行为参数是特定于当前问题的,包括其置信区间,不是从文献中借来的。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相比,结构方程法的缺点是不够详尽遗漏较多。
第三种方法是精简法,它需要较少的数据和资源。然而,有时很难确定因果关系,因此主要的挑战可能来自于在缺乏有计划的运输基础设施情况下能否建立反事实关系。此外,精简法排除了评估福利效应的可能性。
下面我们将讨论通过结构方程和简化法得出的一些结果。此方面的论文多种多样,但很难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因为它们检验了不同运输模式(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高速铁路)在不同时期(19世纪与20世纪)对不同部门(农业和制造业),以及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影响。这是一个不断扩大研究范围的领域,因此我们只选择几篇主要的论文进行了评论(有关更加综合性的评论,请参见雷丁和特纳(2015)的论文)。
在两篇内容丰富而细致的论文中,唐纳森(Donaldson,2018)、唐纳森和霍恩贝克(Donaldson and Hornbeck,2016)分别研究了殖民地时期的印度(1870—1930)和美国(1870—1890)铁路发展带来的影响。印度的铁路建设降低了运输成本,进而与铁路相连接地区的农业产出提高了17%。铁路可以使不同地区从贸易中获益,因此印度总体收入水平也有所提高。通过类似的方式,唐纳森和霍恩贝克(2016)量化了1890年美国铁路对农业部门的总体影响。在1870—1890年期间,铁路建设获得了较快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延伸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县,相应地影响了美国农用土地租金。具体来说,唐纳森和霍恩贝克以伊顿和科特姆(Eaton and Kortum,2002)的研究为基础,建立了市场准入精简型评判标准,并制定了经验策略以评估如何更好地进入那些大幅度提高农业用地租金的各个县。他们发现,1890年拆除所有铁路使美国农业用地总价值下降60.2%,这等于1890年美国GDP的3.2%,再次证明这种投资是具有很高回报率的。与制造业不同,农业是一项分散的、占用大量土地的经济活动。因此,沿着或靠近铁道地区的农业生产受益于铁路建设并不惊奇。
伯杰和恩弗洛(Berger & Enflo,2017)分析了150年间铁路建设对瑞典城市发展的影响。他们发现,在第一个20年间,与铁路连接起来的城市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后来,铁路发展促进与铁路连接起来的城市的人口增长并不显著,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口从没有铁路连接的城镇迁移到连接铁路的城镇。在20世纪,19世纪初铁路发展冲击促进城市发展的效应仍在持续,还有证据表明运输网络对空间发展的影响存在路径依赖。
钱德勒和汤普森(Chandra and Thompson,2000)分析了1969—1993年间州际公路建设对美国农村区域各个县的影响。因为州际公路没有计划连接美国农村区域的各县,所以州际公路建设可以看作是一个外生变量。他们发现,新的州际公路建设提高了公路沿线农村区域各个县的总体收入水平,然而它又导致邻近各县总体收入的下降,这是因为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经济活动转移,而不是促进整体经济活动的高涨。杜兰顿、莫罗和特纳(Duranton,Morrow and Turner,2014)研究了公路对美国城市间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公路建设对厂商选择生产区位有很大的影响,但对产值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公路建设可以转移经济活动到落后地区,但不会导致总体经济的增长效应。
斯托里加德(Storeygard,2016)分析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主要港口城市和289个内陆城市之间道路运输成本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石油价格从2002年的25美元上涨到2008年的97美元,这对运输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外部冲击。斯托里加德发现,道路运输成本水平与城市经济活动之间的弹性为-0.28,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夜间轻型卫星数据反映出来。但这种弹性衡量的只是贸易流的短期效应。
中国的研究富有意思,经济活动快速增长,运输基础设施供应也不断增加。然而,中国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限制,故与其他国家不同。费伯(Faber,2014)和鲍姆-斯诺等(Baum-Snow et al.,即将出版)的研究表明,中国新的公路建设提高了通过公路连接起来的大都市区域的工业产值,但降低了大都市区之间地区的工业产值,未通过公路连接起来的地区所受到的影响较小。换句话说,贸易一体化促进了核心城市的发展,牺牲了城市群之间地区的发展,这与交通运输部门普遍存在距离经济和在制造业部门普遍存在规模经济是相一致的。
降低出行成本也通过厂商组织影响空间均衡。事实上,厂商是由管理、研发、金融和生产等多功能部门所组成的,它们并不需要都聚集在同一个屋檐下。在新的信息和通信设备出现以及航空运输和高速铁路发展之前,厂商向其他地区提供服务主要依靠驻扎在当地的代表,且下属厂商较多的公司总部在当地都设有管理人员,委托他们来执行公司的决策。林(Lin,2017)发现,中国城际高速铁路建设使得在用高铁连接起来的城市中获得就业的数量大幅增加。查诺茨、勒拉奇和特雷维恩(Charnoz,Lelarge and Trevien,2018)以法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为例,研究了总部与下属公司之间出行时间的减少如何促使管理职能集中在总部的问题。布罗尼根和克里斯特(Blonigen and Cristea,2015)根据美国航空业的放松管制讨论了提供航空服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航空服务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服务业和零售业促进经济增长效应最强。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难以在这些论文的结论之间进行比较。这些论文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的评估程序,而且还在于不同时期、在不同技术水平下的不同的运输模式以及不同的部门。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影响提供较为明确的答案之前,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以解释这些差异。尽管有理由相信铁路对19世纪美国和印度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建设新的公路可以减少后工业化国家内部的区际发展差距。不可否认,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或其中一些部分对区域经济活动区位以及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不是所有交通基础设施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那些类似于普及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影响厂商的区位决策。简而言之,提供更有效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能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但我们相信它不是许多决策者所推崇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
4.交通基础设施的政治经济学
运输成本也是对交通运输系统的性质进行政治性决策的结果。在美国,联邦政府主要利用汽油税收入向很大一部分的州际公路提供资金支持。奈特(Knight,2004)发现,国会运输委员会在决定地区之间分配资金时的方式是多数票方式,这是非常低效率的,大约一半的投资资金被浪费掉了。此外,鲍姆-斯诺、杜兰顿和特纳(Baum-Snow,2007;Duranton and Turner,2012)提供的计量经济学证据表明,公路建设往往分配给那些城市发展比任何一个城市都要慢的城市。
格莱泽和庞泽托(Glaeser and Ponzetto,2018)研究了美国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周期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美国在大型城市项目中投资了巨额资金。但后一段时期,对城市项目的投资下降了,因为主要的城市地区盛行了“不能建在我的后院”式的反对呼声。在过去的20年间,城市投资项目必须要证明那些受到项目建设影响的所有社区,通过艰苦的减排努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格莱泽和庞泽托列举了连接剑桥和波士顿的安德森纪念桥的例子,这座桥花了一年的时间于1915年建成,但在一个世纪后重建时花了8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它必须安顿好那些生活在良好的教育以及人口稠密环境中的居民。投资支出的低效是政治效率低下的结果,而这种低效率已超出了交通运输委员会的允诺范围(Knight,2004)。
第一个低效率的原因是,联邦政府为建设那些主要收益由当地享用的公共基础设施而进行融资时的成本,似乎是无法看得见的成本,且每个城市获得的只是其中的1/N份额(N为城市数量),因此常存在过度投资的现象。第二个低效率的原因是地方团体势力的反对,他们直接受到投资项目带来的各种影响。这些投资项目带来的损害是直接的,且收益也都被挥霍,这些反对团体还提出过分的减排要求,迫使投资项目变得过于昂贵。第三个低效率的原因是联邦政府的资金规则,这些规则不足以满足那些人口密集型城市的需要以及那些交通基础设施被外地人密集使用的城市的需要。
在欧盟,用来投资在交通运输领域的联邦基金是欧盟委员会的主要的区域政策工具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欧盟启动了大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其中包括30个优先项目。对这些项目的投资效益事前评估得出了3个主要的结果(Proost et al.,2014)。第一,22个项目中只有12个通过了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测试;第二,大多数项目只有益于投资项目的所在地区,因此主张积极的溢出效应的团体不会认可这种项目;第三,这些项目并非有利于最贫穷地区。普罗斯特等以布洛克、科泽涅维茨和舒尔曼(Bröcker,Korzhenevych and Schürmann,2010)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该模型包括了欧盟236个大陆型地区,每个区域都生产不同的可交易的商品。劳动力在空间上是不可流动的,这一假设与许多论文中提出的自由流动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交通运输网络中的节点表示一个区域,且所有区域都相互连接起来了。该网络包含了欧洲公路、铁路、渡轮和航空运输网络等所有主要环节的数据,包括他们的具体特征,如速度限制、拥挤可能性等。运输成本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运输网络数据库中的最短路径进行计算的,新的或升级的连接线会影响贸易流和当地生产以及商品和要素价格。此外,该模型在评估居民福利水平时还考虑到了投资资金。该模型很好地刻画了交通运输部门的特征,还包含了多个一般均衡效应。我们认为该模型为将在第五部分(二)讨论的空间计量建模方法的先驱。
德鲁斯和诺姆贝拉(De Rus and Nombela,2007)利用成本效应分析法,分析了高铁线路(HSR)具有社会效益所需的乘客数量。他们发现,一条高铁线路每年需要1 000万左右的乘客,而欧盟一些新的高铁线路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如果高速铁路必须自己来支付所有成本,那么大多数高铁项目没有足够数量的乘客以具有经济上可行性。
上述结果说明了政治经济因素在投资项目选择中的作用。许多大型项目挥霍当地的经济收益,因此通过本地用户来定价的方式,可以避免联邦资金的错配。当本地用户定价无法区分本地选民和非当地选民但用户定价收入必须投资到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时,本地用户定价比联邦资金更有效(De Borger and Proost,2016)。总之,利用联邦或欧盟资金来资助当地交通基础设施,至多是好坏参半的做法。
(未完待续,见下期)
注 释:
①空间竞争模型是唐斯(Downs,1957)在霍特林(1929)模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模型。该模型同时也是政治学中有关政党间竞争理论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