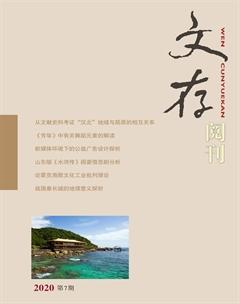归去来兮:从“乡愁乌托邦”角度解读《黑骏马》
摘要:“乡愁乌托邦”是一种以乡愁为主要表征的乌托邦存在形式,是人类汲取超越现实苦难的力量的重要来源。本文即从“乡愁乌托邦”角度对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黑骏马》进行文本细读,提出《黑骏马》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一场将痛苦的现实通过转向美好的过去而实现救赎的全过程。小说的出彩之处在于以乡愁这一普遍人生体验投射出无数个体在怀想过去与面对未来中的生存焦虑。
关键词:黑骏马;草原;乡愁;乌托邦
一、草原上的乡愁烙印:以现代文明之魂扎根草原文化之乡的生存悖论
故事一开始就以细腻的笔触暗示着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再度踏入草原时的沉重心绪。而这种心绪,不仅掺杂着阔别已久的隔阂感,更负荷着来自白音宝力格灵魂深处的苦痛。
白音宝力格本不属于草原,但自从他被父亲送到额吉奶奶的毡包里,草原就成为了他永远的精神故乡。从初见额吉时“使劲挣出她油腻的怀抱”的抗拒到对“草原那么大,那么美和那么使人玩得愉快”的由衷赞美,草原以其辽阔的天地感化少年的淘气、滋养美好的人性。小时候的白音宝力格,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草原。即使长大后面临着去内蒙古农牧学院深造的机遇,他也毅然选择回到草原,回到心爱的索米娅和额吉奶奶身边。因此,非生于斯但却长于斯,在白音宝力格的内心深处,草原是他的心灵圣地。草原所给予的美好是他一生所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这份珍贵。
但是,在白音宝力格的身上,现代主义者的倾向很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十五岁的时候,他就有心钻研畜牧业机械和兽医技术,常常安静地阅读《怎样经营牧业》。他清楚地知道诸如“把拖拉机插进乳牛肛门吹气”等方法没有科学依据,一直向往科学的专业学习。如果说草原上的人们还生活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那么白音宝力格已经走向从原始自然状态向现代文明生活的过渡了。原始和文明的鲜明对照与冲突,一直潜伏在白音宝力格、索米娅和额吉的生活中,直到草原恶霸希拉对索米娅的奸污才爆发出来。面对索米娅对丧失贞节的默默忍受和额吉原始人生观基础下的劝慰,白音寶力格发现了自己原来是草原文化生活中的异类,他不仅心理上忍受煎熬,行为上阻止冲动,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对草原习性和自然法律的强烈否定使得他不得不在痛苦中离开草原,投身于他所向往的“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有事业魅力的人生”。因此,这看似正当的出走并不是简单的亲缘割舍,而是以现代文明之魂扎根草原文化之乡的生存悖论,从此在白音宝力格身上留下了深深的乡愁烙印。
二、“乡愁乌托邦”追寻者:迟到的忏悔与迷茫的救赎
乡愁,是一种怀旧,而怀旧“就是对过去的重构和对历史的再创造。怀旧的真实性不是基于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现实吻合,而是怀旧主体在经历了一定的岁月沧桑之后所能达到的、对过去和现实在意识层面上的心理真实”。
离开从小生长的亲人和草原打破了白音宝力格原本身体、环境、文化相互协调一致的生活状态,最终只能在现代文明的折磨之中痛惜自己对过去的轻易割舍。因此,那被现实肢解得快要烟消云散的理想悄然间又重新勾起了他对美好的田园般的过去的向往。不同于简单的怀旧和怀乡病,白音宝力格的乡愁带有一种将过去的生活乌托邦化的强烈色彩,是在历经现实沧桑后的幡然醒悟。正是这种源自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欲望和冲动指引他回到最初的起点,重新追寻失落的精神家园。但同时白音宝力格也知道是自己曾经抛弃了过去,明白“那深沉而挚切的爱情”不过是“一些依托或想象”,所以他并不是在向过去索要理想,而是以此希冀在曾经的憧憬和期待中治疗千疮百孔的身躯和心灵,汲取向未来挺进的精神力量。他既向后看,同时又向前走,是一个果敢的“乡愁乌托邦”追寻者。
然而,面对山石峥嵘的天葬沟和天人永相隔的铮铮事实,曾经的种种美好与浪漫瞬间化作一种迟到的悔恨与愧疚,深深刺激着他。他那千疮百孔的身躯和心灵也因而变得更加面目全非。他开始幻想赎罪的方式,用几乎痛哭的呼喊寻求道德罪恶的解脱,可索米娅无声的谴责与淡漠的宽容却又一度让他不知所措。他以为自己要去拯救在生活的漩流中挣扎的索米娅,却不知深陷生活漩流之中的正是他自己。
三、苦难过后的精神皈依:逝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待
所幸,一个叫“其其格”的孩子最终开启了白音宝力格的自我拯救之旅。小说中的“其其格”是一个极其精彩的角色设置。白音宝力格先是将这个小生命视为爱情的污迹并狠心唾弃,最后却在她身上重新领悟到了老额吉和索米娅身上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生命韧性和母性意识。而答应索米娅送她一个“吃奶的孩子”,则代表着白音宝力格卸下了背负已久的沉重愧疚,选择与索米娅一起呵护立足草原文化又超越草原文化的精神家园。于是,一场苦难过后的精神皈依,在对生命的崇拜和尊重中悄然完成。虽然城市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对立冲突依然存在,但最终的承诺象征着曾经的美好与现实的落差所造成的缺憾得到了释怀,白音宝力格也因而坦然地走向了未来。
总的来说,《黑骏马》通过乡愁这一普遍人生体验抒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牧歌。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在怀想过去与面对未来中投射出的生存焦虑问题不仅是他个人难以解决的,同时也是每一个社会个体难以摆脱的,其深刻意义在于以心灵的回归完成了对过去的释怀,并从中汲取豁然追求未来的勇气,暗示了在爱与包容的力量下意志战胜苦难的巨大生命力,深刻地揭示出“逝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待”的人类精神走向。而从深层价值上来说,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在苦难中追求理想的人生困境,充满独特的哲理魅力,留给读者的是对于现实和理想的无尽思索。
参考文献:
[1]王杰.乡愁乌托邦: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其审美表达[J].探索与争鸣, 2016(11):4-10+2.
[2]黄筱茜.“乡愁乌托邦”的影像化表达[D].浙江大学,2018.
[3]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105-114.
[4]刘淑莉.《黑骏马》的原始主义解读[J].辽东学院学报,2006(02):110-112.
[5]田德芳.“归乡”模式下现代知识者的精神之旅——张承志《黑骏马》和鲁迅《故乡》的比较[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04):80-82.
[6]奚玉春,马业永.《黑骏马》──超越痛苦的人生牧歌[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06):33-35.
[7]程德培.《黑骏马》的诗学——兼及张承志小说的艺术特色[J].当代作家评论,1984(02):67-72.
作者简介:
何惠丹(1999—),女,汉族,浙江义乌人,浙江师范大学,2017级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