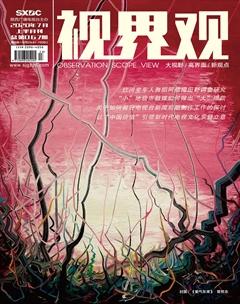“镜像”中暴露无遗的个体私欲
摘 要:“他人即地狱”是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禁闭》这部作品体现了萨特对于个体和他人的深邃思考:人的存在,人的自我认知必须借助他人或者他物才能完成,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所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就会在与他人的交流或者他物接触中暴露无遗。个体欲望的满足必然会与他人产生冲突,因此也诠释了“他人即地狱”这句话的深刻哲理。《禁闭》这部剧以境遇、他人、自我为镜,照射出了潜藏在个体内心中的私欲,借此反思自我存在与生命的价值。
关键词:《禁闭》镜像; 对照; 欲望
《禁闭》是萨特创作的一部独幕剧,也是其创作的三部哲理剧之一。《禁闭》剧中塑造了这样的三个角色:一个残忍的同性爱慕者(伊内丝),一个临阵退缩的逃兵(加尔散),一个视性成瘾的谋杀者(艾斯黛尔)。他们死后在地狱里相遇,同处一室,三人之间互相戒备又相互隐瞒生前的种种罪行。三人自我封闭,却又相互拷问,每个人都需要从他人的注视中寻求肯定。在地狱的密室中,三人急需从各种镜像中找寻对自己生前罪责掩饰的借口,借此寻到慰藉,因此三人以境遇,他人,自我为镜分别加以对照。
一、以境遇为镜
“地狱式”的场景不可逃避,《禁闭》中所设置的场景是一个虚拟的“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是一个极其幽闭的空间。“这儿没有镜子,没有窗户”,按铃也是坏的,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甚至“没有任何容易打碎的东西”。在这样的极限的境遇里,封闭的空间实际上是这个荒诞世界的微缩版,房间之外是走廊,走廊之外又是房间,永远反复,永远循环,没人能清楚的知道这循环之外的景象,也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个封闭的空间。在这座地狱的密室里,灯光永远亮着,三个“死人”永远活在对方的注视中。在这个荒诞的境遇里,任何事件都无法预测,感受不到任何时间的流淌,只能被动的等待着,这也是个人生存境遇的真实写照,个体所从属的众多空间都闭合在一个特定的封闭的境遇里,无法同外界进行对话与交流。所以在这部戏开始时,三人都以境遇为镜,在沉寂的环境里,长时间的无法同外界交流就会对个体产生一种强烈的压迫与压抑之感,进而促使三位主角开始同同样处于封闭空間的其他二人寻求慰藉。
二、以他人为镜
在上文中提到的封闭空间里,没有镜子和永不熄灭的灯,这两处细节在剧中有着强烈的戏剧效果。地狱密室里,永不熄灭的灯就意味着,没有时间的的概念,剧中的人物也没有了睡眠和独自相处的机会,只能在如此亮堂的境遇里,暴露在另外两个人的直勾勾的注视中,难逃别人的审视与评价。“镜子最为特殊: 它从未出场,却一再被找寻。这个不在场的被欲求之物,比舞台上任何可见之物都更为牵动人心。这个倾注了剧作者匠心的结构性细节,有时被称作‘著名的缺席。”1此外,“《禁闭》中反复出现关于镜子的讨论,镜子是重要道具,也是戏剧表现的关键线索。人为什么要照镜子?”2镜子是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工具,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没有镜子就意味着个体的自我认知残缺,进而导致自我怀疑。一旦自我怀疑就会导致个体命运堕入扭曲的境地。同时,个体无法认知自我,就会寻求他人充当认知自我的镜子,也就意味着个体将失去对命运掌控的主动权,只能沦为他人眼中的评价物。
在剧中当三人暴露在彼此的注视中,灯光的永不停息,使得这种注视的不分昼夜,在永恒的注视与被注视中,痛苦自然出现,他们三人不仅想从对方的注视中寻求对自我空洞内心的些许抚慰,还想依靠自己对他人的注视来满足自身的窥探欲,因而形成了三人互相追逐的局面。另外,当第三者看到其他二人有和解的趋势时,也会产生妒忌心,害怕被孤立又会重新挑拨其他二人的关系,彼此折磨又彼此依赖,形成一个难以停下的恶性循环。剧中三人分别以他人为镜,既想肯定自己的美好形象,又想挑出他人掩饰罪行的破绽。以他人为镜无疑成为了剧中三人鞭笞自我与他人的酷刑,个体都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总以为得到了他人的认同才能获得满足感与安全感,进而形成了三人互相追逐又互相排斥的局面,永远无法解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心深处个体私欲的膨胀与无法对自我的释怀。
三、以自我为镜
在以他人为镜的无边痛苦中,三人审视自我的目光开始从他人身上开始转移到自我身上。然而个体内心深处的欲望,是剧中三人痛苦与不自由的根源,他们以自我为镜,更能突显出个体内心私欲的可怕,也使得读者深刻体会到个体内心欲望对于自身命运的毁坏。《禁闭》中的三人不管是生前的罪行,还是死后的掩饰,都是其内心欲望诉求的外在表现。
(1)对欲望的痴迷
艾丝黛尔,生前的谋杀行为只为换的与情人罗歇更长久的欢愉享受,而在罗歇得知艾丝黛尔杀害女儿之际,他无法面对眼前的这个恶魔,而选择了自我了结。艾丝黛尔将男女欢愉的满足和罪恶的减少联系在一起,只要欲望得到了满足,她自身的罪恶感就会大大减少,从而认为为满足欲望的犯罪是理所应当的。在情人死后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才衍生出一种惋惜。在地狱中,加尔散作为唯一的男性,是艾丝黛尔唯一可以发泄欲望的对象,她转而以可怜虫的形象自居,企图博得加尔散的怜悯,并根据加尔散的描述,虚假赞同他是一个英雄,期望获得加尔散的爱情,以此来弥补她生前欲望的“损失”。只要欲望得到满足,任何恶劣的行径都不会受到谴责,可见艾丝黛尔自私自利又极端扭曲的人格。
(2)对虚荣的执着
加尔散生前折磨妻子,沉溺酒色,临阵脱逃,死后却一度营造自己的英雄形象。在地狱的密室中面对艾丝黛尔的诱惑,加尔散选择接受,认为艾丝黛尔对他的求爱是理所应当,因为在加尔散的自我认知中,他是一个极赋魅力的男子。在被伊内丝拆穿生前抛弃妻子的事实时,他还补充说自己是一个“被人钟爱的畜生”。在面临对他临阵脱逃的指责时,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指引下,加尔散绝不认为自己是胆小鬼,叛徒,反而以各种理由来说服身边人承认自己是英雄。其实在加尔散身上可以体现出如今社会下个体的身份认同危机,在他人眼中的胆小鬼形象,与自我认知里的英雄形象产生了强烈的冲突。由此可见加尔散这个角色内心深处对于虚荣的执念以及对自身认知的残缺。当加尔散发现自己没法说服伊内丝时发出了“他人即地狱”的感慨,着实令人震撼!
(3)对同性的极端化倾慕
伊内丝内心深处对于同性的倾慕令其走向了毁灭他人,毁灭自己的道路。她对于异性极度厌恶与排斥,却对同性充满了毫无底线的爱慕。生前厌恶表哥的男性行为,诋毁他肮脏与软弱,诱拐表嫂,直接与间接害死了表哥表嫂。死后在地狱的密室里也依旧认为加尔散是个软骨头。对于同性的极端倾慕与极端的排斥异性,使她的自我认知里产生了对于性别以及情爱伦理认知上的偏见,从而导致了这种混乱极端的性格的出现。伊内丝把对同性的极端化倾慕充当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相比于其他二者,笔者认为这个角色的塑造实在是令人恐惧,她有着自己的想法,她承认害死表哥表嫂有罪,但却依旧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伊内丝这个角色对于是非对错已然认知混乱,以自我欲望的满足为最高点,一次次破坏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她所作出的行为如同恶魔一般,规则与伦理束缚意识在她这里完全不存在,她在占有欲的推动下,将自己与他人一同毁灭。
结论:
“《禁闭》为生与死的戏剧性辩证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框架: 死亡的生命可以被活著的死亡所惩罚。”3《禁闭》这部剧本剧中的三个人物都带着生前的罪行死后在地狱密室里相遇,并且被生前错误的价值观念所引导,开始了“死人”之间的互相折磨。在境遇,他人,与自我为镜的重新审视中,依旧没能逃脱欲望的枷锁。生前因为欲望的驱使杀人犯罪,死后在欲望的相互渴求下选择互相折磨,选择被动而又无能的等待,三人都不敢逾越密室的界限,也不敢走出密室,只敢说出我要走出去的话语。最终落得发出“他人即地狱”的悲叹,其实剧本中塑造的“加尔散”,“伊内丝”,“艾丝黛尔”是如今社会芸芸众生的缩影。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与他人的联系之中,我们也无法逃脱别人的审视与监督,为了不使剧中三人互相折磨的场景再现,我们能做的就是正视自己,正视欲望,正视自身所处的人际关联,降低自我对欲望的渴求,始终以自我,他人,和境遇为对照,了解自我内心,“吾日三省吾身”,探寻人生的真正意义。
注释:
1张颖:《萨特戏剧<禁闭>主题重释——从密室布景谈起》,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年1月,第1期。
2李克:《他人,存在的苦恼之源——<禁闭>对人存在真实境遇的揭示》,法国研究,2013年2月,期刊。
3 Benedict ODonohoe. Sartre's Theatre: Acts forLife. Ed. Peter Collier. Bern: Peter Lang AG,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s,2005.
参考文献:
[1]让 - 保罗·萨特: 《萨特文集·戏剧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2]马志丹:《论萨特戏剧 <禁闭>中的身份之变与伦理选择》,四川戏剧,2019年7月,期刊。
作者简介:叶承乾 ,广西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19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