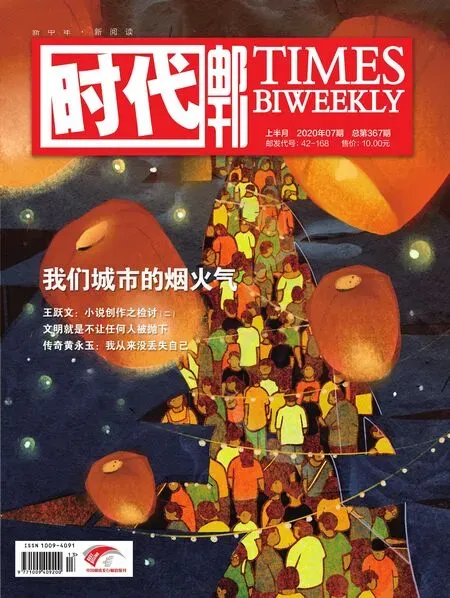传奇黄永玉:我从来没丢失自己
艺术大师黄永玉写过一幅令人莞尔的字——“世界长大了,我他妈的也老了”。96岁的他,可谓一部活着的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史——从一介辍学流浪的湘西少年,到誉满海内外的艺术大师,他这一生历经数次时代动荡,却又机缘不断,与当代最杰出的一批人物为友;他怀着对生活的“爱、怜悯、感恩”,将丰富的生命经历融入到创作中,并以对世事的洞见和豁达的心性,将自己的人生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传奇”。

无师自通的“天纵之才”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父母带他回到了老家凤凰,这里民风悍勇、自由、浪荡,将幻想与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他终生都在追念凤凰,因为它“那么厉辣,那么雄强,那么狠毒,那么讲究文化,那么五脏俱全,又那么妙趣横生”。
黄氏家族是凤凰有名的书香门第。祖父曾开办凤凰第一家邮局和第一家照相馆;父亲不仅是当地男子学校校长,还画得一笔好画;母亲则是当地女校的校长,是一位带着学生跳现代舞的新女性;表叔沈从文,更是享誉中外的大作家……
正是在这方灵秀水土、这种家族家风的滋养下,才走出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大师黄永玉。
黄永玉说:“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1937年,未满13岁的半大伢子黄永玉离开家乡,几经辗转到达厦门,入读集美学校初中。但不久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战火中的教育断断续续,他初中留了五次级,同学们都叫他“黄留级”。几十年后开同学会,他送了画,落款就写“一个1937的留级学生”。
在艰难时世中,这个顽野的少年开始自学木刻,并很快崭露头角,14岁就成了中国东南木刻协会最小的会员。可惜时局动荡,他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了,开始了“人生大学”的历程。他一路流浪到福建的德化、泉州、仙游、长乐和江西的赣州、信丰、安息等地,当过瓷厂小工,干过码头苦力,做过战地服务团团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他漂泊了8年,从13岁到21岁,与抗战八年差不多重叠,一个人的漂泊故事从而与家国的命运起伏紧密联系在一起。
少年流浪世界,用脚板行走几千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其中艰苦自不待言,但在他晚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却只有短短一段话:“一千里?二千里?三千、四千、五千难计算,就靠两只脚板不停地走。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
在这期间,黄永玉迸发了全部创作激情,并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了许多终生的朋友,成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的新锐创作者。有人说他简直就是个无师自通的“天纵之才”,不论国、油、版、雕、书法、篆刻以及诗文之类,他一学就会,一会就精。
从来没有丢失自己的艺术大师
1946年春天,黄永玉与初恋张梅溪在赣南结婚,从此相伴终生。同年他们辗转到了上海,1948年再次漂泊到了香港,直到1952年满怀希望回到北京,才结束了漫长的漂泊。黄永玉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担任讲师教版画,很快晋升为最年轻的教授,并以木刻代表作《春潮》《阿诗玛》轰动中国艺术界。
平静的日子没持续太久,1957年之后的十年,他遭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低谷时期。当妻子忍不住为他哭泣时,他却坚定地说:“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其实他自己也哭过一次,那是他读到巴尔蒙特的“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这句诗时,一向坚强的他忍不住哭得像个孩子。现在人们谈起黄永玉,总是说他“好玩”,但这个词在他身上有着别样意味,这其实是他应对多舛命运的一种人生智慧。
上世纪70年代后,黄永玉先后在国内外举行了数十次个人画展,赢得了空前盛名;他设计的中国首枚生肖邮票《庚申年》金猴邮票成了收藏界的神话,设计的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他还荣获了中国美术最高奖“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意大利最高荣誉奖“司令勋章”,亦是首次获得“奥林匹克艺术奖”的中国人,并于2011年成为中国国家画院首批院士之一。可他除了比以前更勤奋外,看不出别的变化,他说自己“苦的时候能撑得住,好的时侯也不飘飘然”。他的一些学生曾说要成立一个“黄永玉画派”,他写信臭骂了他们一顿:“狼才需要成群结党,但狮子不用。画画就要独立思考,自己创作自己。”有年轻网友在微博上问他:“您一生当中最骄傲和最失意的事情是什么?”他答道:“我一辈子没有什么骄傲和失意的,我从来没有丢失自己。”
初恋女友梅溪74载的丈夫
与艺术相比,黄永玉更“钟情”的是自己的爱人。1942年,18岁的他在江西遇见陪伴一生的爱人张梅溪,“一个广东姑娘,皮肤黑黑的,讲国语带浓重广东腔,人和和气气,穿着打扮按平常标准来说,稍微洋了一点”。他们一起逃难,一起面对人生坎坷,直到死亡才把他们分开。
他们的爱情就像部浪漫小说。梅溪的父亲是位军官,她身边也不乏追求者,而黄永玉只是个流浪的穷小子。黄永玉回忆他的求爱经历,那时他刚学会吹小号,于是每日站在窗口等她上班,“老远看到她我便吹号,像是欢迎她似的。”一天,黄永玉问她:“问你个问题,假如有人爱你了,你怎么办?”梅溪说:“你为什么现在才问?你问,我早答应了。”但梅溪的家人反对,于是她不顾一切偷跑出来找他,那天两人安身的旅馆“就是土炕上堆一堆鸡毛,晚上就靠着鸡毛御寒”。1946年,他们在好友们的见证下成婚了。
结婚50周年时,黄永玉特意买了一把小号,豪气地问梅溪说:“想听什么?”哪怕他已是名满天下的艺术大师,但他最骄傲的身份还是初恋女友梅溪的丈夫。他给梅溪写情诗,“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2020年5月8日,98岁的梅溪去世,96岁的黄永玉为夫人手书讣告——“尊敬的朋友: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于香港港怡医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讣告仅5行,短短57个字,却饱含了他们74载相知相守的深情。
文化大师们的知己
这一生,黄永玉谈得最多的人莫过于表叔沈从文了。他们既是亲戚,又是同道,更是知己。在谈沈从文的文字中,黄永玉写得最鞭辟入里;在论黄永玉的文字中,沈从文写得简直就是夫子自道。1982年,黄永玉曾陪80岁的沈从文重返阔别近60载的故乡。后来沈从文去世前还忆起此事,对他说:“多谢你带我回凤凰。”黄永玉在表叔长眠之地写下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90岁时他出版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卷首手书了一行字“爱,怜悯,感恩”——这是表叔对他说的,他念念不忘,预备作为自己的墓志铭。
沈从文还将得意弟子汪曾祺介绍给他认识。1946年,汪曾祺在见过黄永玉次日就写信给老师,热情称赞对方是个“小天才”,说:“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之后在上海的两年里,两人每到周末必相聚同游。汪曾祺于黄永玉是知己,汪曾祺去世后,他说:“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
当黄永玉1948年漂泊到香港后,他还与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两位传奇人物查良镛(金庸)、陈文统(梁羽生)成了《大公报》的同事。在香港他迎来了艺术丰收期,却也意外遭遇了一些批评。他当时倍感委屈,查良镛和另一位朋友帮他出主意,最后三人合作写了一份辩白。
1953年,黄永玉一家离开香港到了北京,从此与查良镛难得一见。但当查良镛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远在北京的黄永玉热心逐句细评,详加分析,这本书出单行本时还准备附印他的评注。1981年,阔别近三十载的两位老友在北京相见,黄永玉如多年前一样叫查良镛“小查”,查良镛慨叹:“现在香港叫我小查的人没有几个了。”
有诗云,“故人星散尽,我亦等轻尘”。步入老年后,漫谈成了黄永玉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他不哀不怨:“我原来最小,现在成最老的了。”这个96岁的老人的内心深处,总是想着自己的朋友们。
自诩为90后的耄耋老人
黄永玉写过《比我老的老头》,但他本人是不认老的。90多岁又如何?他觉得自己就是90后。
他83岁时曾登上男性时尚杂志《时尚先生》封面,成为最酷的“时尚先生”;86岁时他再展抱负,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并于90岁时出版第一部,92岁时出版第二部。这部近百万字的长卷在上世纪40年代已动笔,历经时代动荡,几次停辍,经过一甲子的磨砺才得以续写。
他说:“一个老头儿要到了90岁,脸上、身上都长了青苔时才来出这部书,是喜剧也是悲剧。”他在写作中朝向故乡,回溯生命的来路,打量着自己是怎么一点儿一点儿长成的。他打趣自己:“看来100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争取活到把自传写完。”
如今,在凤凰老家的木板墙上仍然留有他4岁时写下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回忆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他说:“我没浪费过一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