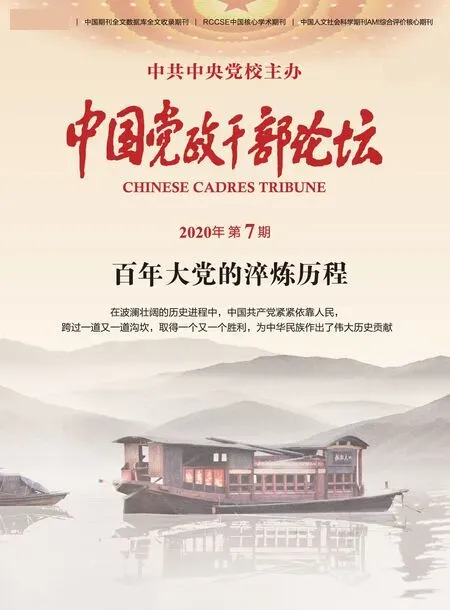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如何一步步化危为机
文_ 邵维正
从1921年成立之日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曾渡过无数激流险滩。由于中国革命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在与凶恶敌人搏斗中,遭遇困局、险境、危机是难以避免的。革命总是伴随着危机。危与机是辩证的统一体,既有危局,也有机遇,革命者应以大无畏的精神,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开拓斗争的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革命史就是一部不断化解危境、抓住机遇、走向胜利的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遭遇过多次危机,其中最为严重的困局险境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正由于成功化解了这一危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留住革命火种,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段历史值得总结和记取。
早在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在此前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四次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各项建设取得重要成就。然而这时,一个新的危机降临了。
这一危机来自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是,1933年10月上旬,蒋介石亲临南昌,自任总司令,具体部署第五次“围剿”战略战术计划,决定以50万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起进攻。主观方面是,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到了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成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本来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可能化作泡影。
一、这次危机持续时间更长,涉及面更广,而且是由多次险情构成的
这一危机的产生和形成不是偶然单一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环节与过程。由于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党中央与中革军委被迫率领红军实行“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在通过湘江封锁线时遭受重创,一步一步走向险境,在遵义会议前后发展成为建党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这次危机包括以下一些重要环节。
一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节节败退,局势无法逆转。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不仅兵力更多、武器精良,而且邀请德国将军担任军事顾问,采取持久战与堡垒战这一新的战略战术,在进攻中沿途构筑稠密的碉堡体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蒋介石妄称,只要采取这种逐渐推进的堡垒战,“匪区纵横不过500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2里,则不至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实施“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与敌人拼消耗,造成红军重大损失。1934年4月中下旬,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敌军分6路向中央苏区腹地步步紧逼,红军也分6路全面防御。战至9月,原中央苏区30多个县,只剩六七个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

遵义会议旧址
二是敌军实施“铁桶计划”,欲彻底围歼中央红军主力。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绝密军事会议,在此前“围剿”的基础上重新调整部署兵力,准备实行德国顾问冯·塞克特上将策划的“铁桶计划”:决定集结150万人、270架飞机和1000辆卡车“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以“赤都”瑞金为最终目标,在距其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每天攻击前进5公里,一个月内消灭中央苏区红军。蒋介石对此次计划寄予厚望,仅会议发给每人的绝密文件就有几斤重,叫嚣“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外,还有一位级别不高却“战功卓越”的赣北行署专员、保安司令莫雄。莫雄早年参加同盟会,与蒋介石颇有交情,之后经常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交往并留在党外工作。会议结束后,他立即把整套绝密文件交给地下党员项与年。为了把文件传递出去,项与年用砖头敲掉自己的门牙,化装成让人讨厌的叫花子,以此通过敌人的重重哨卡,进入中央苏区把情报交给周恩来。这一突发事件使党和红军危在旦夕,党中央决定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加快实施战略转移。
三是血战湘江,红军遭受重创。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出发长征。经过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由于此前与广东地方实力派达成相互借道等协议,中央红军顺利从江西信丰渡河进入广东境内。此后又向西突破了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江一线。敌军经过一段时间调兵遣将,在这里撒开了一个由30个师、40万人组成的大包围圈,对红军进行“湘江会剿”。在广西境内的湘江沿线,中央红军经历了自创建以来受损最重、最为悲壮的一次战役。通过5昼夜苦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红军鲜血染红江水。由于中央纵队带着几乎所有的“家当”,行动迟缓,延误战机,为此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从出发时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担负后卫的第三十四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遭敌重兵包围,包括政委、参谋长在内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途中乘敌不备他将肠子从腹中掏出扯断,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四是渡过湘江后,又遭遇新的险情。中央红军虽已突破湘江防线,但对于遭受严重损失且苦战后未获休整的红军来讲,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此时蒋介石已判定红军欲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立即部署20多万兵力,在红军北上的必经之地布下口袋阵,构筑堡垒堵击。博古、李德一意孤行,仍坚持按在苏区出发时拟订的原计划前进。红军如果北上,必将陷入蒋介石的圈套,与以逸待劳的强敌决战,面临全军覆没之险。
五是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一切重大决策需自主决定。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接受它的领导。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通过设在上海的大功率电台进行的。长征之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破坏,没有了大功率电台,同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就此中断,红军一时陷入孤军奋战。失去与外界的联络,情报、经费、物资均无来源,发生紧急情况也无法请示沟通,对红军的作战指挥和军事行动非常不利。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党与红军又一次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面临严重危机。危与机总是同生并存的,有危就有机,只有克服危难,才能迎来转机。
二、经过前期必要的准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顺利召开,成为转危为安的关键枢纽
转危为机,要有条件,首先是中央领导层要统一认识,包括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同志的觉醒,在此基础上党内健康力量形成共识,团结一致,挺身而出与“左”的错误作斗争。这也和危机形成一样,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次重大危机的克服历时两年,其间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先后经历了多个相互联系的事件。
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和序幕。湘江之战的惨败局面,使人们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由怀疑、不满进而发展到愤怒,一股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积极力量正在形成。长期受“左”倾压制的毛泽东更有切身的感受,无疑是发挥了最重要作用。长征出发时毛泽东提议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军行动,在休息和宿营时,他们经常一起交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较快形成共识,一致认为,应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军事路线问题。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失去发言权多时的毛泽东分析敌情我情,权衡利弊条件,力主放弃北上计划,立即转兵向西摆脱困境和险情,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随后中央政治局分别在黎平、猴场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断然破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口袋阵,在行动方向上取得一致。这三次会议环环相扣,一次比一次深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
遵义会议是解决危机的枢纽和标志。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上旬占领遵义,敌军一时还无法围拢过来,党中央和红军在遵义地区取得了十多天非常难得的休整时机。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等作了重要发言。经过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个阵线:多数与会者尖锐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支持和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报告和发言,形成主导优势;少数坚持“左”倾路线的一方已无招架之力。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委托张闻天起草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样,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已被剥夺。遵义会议所作出的一系列决定,通过会后的贯彻落实,逐步摆脱了危机,成为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伸和完成。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后,进入云南向扎西集结,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几次会议。因为扎西是威信县城,又是会议结束的地点,所以习惯上把这一系列会议称作“扎西会议”。这几次接连举行的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及组织等重要问题。其间中央还向川陕根据地、苏区中央分局和红二、红六军团发出长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对遵义会议相关问题作出完善和发展,对于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军实施一系列迂回机动,调动敌军,摆脱重兵围追堵截。扎西会议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攻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5天里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缴枪2000多支,俘敌3000余人,重振红军雄风,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中央红军进行了一次全军性大佯动,三渡赤水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乘各路敌军纷纷追赶之际,中央红军主力向东四渡赤水,转而向南疾进,在贵阳虚晃一枪,接着迅速西进云南、直逼昆明,急转北上,至5月上旬巧渡金沙江,接着强渡大渡河,这时中央红军才真正摆脱险境,终于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粉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冲破强敌重围北上长征途中,党和红军还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分裂危机。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个人野心膨胀,伸手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违背中央决定,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另立“中央”。党中央对张国焘进行耐心地说服工作,并在原则问题上与之进行了严肃的政治斗争。在南下方针遭到失败面前,特别是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说服下,张国焘的分裂行动以失败告终。
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苏区开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这段不平凡的难忘岁月里,党和红军历经多次磨难,面对数度危境。他们不仅没有被压垮,而且迎难而上,连闯五道险关,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铸成中共党史上化危为机的经典。
三、摆脱危机的启示
党的近百年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重大转变,称得上历史性转折的只有两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带有根本性的转变,成为载入史册的丰碑。
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线,正好可以分为前后两个14年。前14年,我们党犯了一次右的和三次“左”的错误;后14年,党没有再出现大的错误,逐步走向成熟。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一系列危与机的转变,很具回顾总结的价值,给人以诸多的启迪,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5点。
一是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倒,坚信能够在惊涛骇浪里走出困境,摆脱危机,取得胜利。长征途中,红军能超越生理极限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频繁的战斗、高强度行军,尤其是承受重大牺牲,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支撑。在无数个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情节:海拔5000多米的党岭雪山,红军战士发现一只露在雪外、拳头紧握的胳膊,便跑上前去掰开手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正是靠着成千上万像刘志海这样抱着崇高理想信念的红军战士,我们党最终战胜了这次空前的危机。
二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勇气。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共产党很多的支持和帮助,然而,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同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这是建党以来不曾遇到过的。一方面增加了革命斗争中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创造了外部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发扬勇于担当的精神,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和红军的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三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会犯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照搬照抄、墨守成规。渡过湘江和遵义会议后,如果不顾当时条件和环境变化,刻舟求剑,机械执行北上计划,势必造成自投罗网的结局。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情、我情、社情的变化,6次调整改变长征的预定目的地,及时改变行动方向和作战计划,创造机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一步一步走出危机。
四是达成共识的果断决策。长征开始后,广大指战员切身体验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迭次失利,湘江战役后又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为什么导致这一局面呢?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思考争论。通过毛泽东等多方面工作,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红军高级指挥员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共识一经形成,就事不宜迟,抓住时机,果断决策,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等挺身而出,红军将领更是积极行动,一致支持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为摆脱危机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经常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面对数倍乃至十几倍敌人的围追堵截,险情不断,形势十分危急。红军如何以弱小的疲惫之师、在失去根据地依托、没有固定给养保障的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呢?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是红军采取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经典之战。由于土城战役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在不具备北渡长江条件下,出敌意料原路返回二渡赤水,取得重大战果,之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三渡赤水达成战略佯动目的后,迅速调头四渡赤水,以出色的运动战调动敌军。经过一系列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时进时退,避开强敌、保存自己,打乱敌阵、疲惫敌人,于四省边界40万重兵中穿插机动,化被动为主动,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终于跳出包围圈,书写了军事史上的“得意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