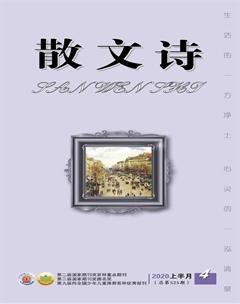城市·他们
杨剑文
裁缝
“裁衣是犁地的演化;缝补是播种、锄草、间苗,或补种秧苗的演绎……”
一枚针脚就是一粒种子。
“各色的丝线,是饿瘦了的山間小路。”他说,顾客送来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他寄存在乡村的山峁、沟梁、清泉、树木、花草、寒露和长势喜人的庄稼。
他自称是移植在城市的一把蒿草。
剪刀是镰刀的“转世”,收割着寒来暑往、吃穿住行、柴米油盐,也收割着这间20平方米小平房的租金,还收割着在远方“漂”着的儿子的房贷……
咔嚓。剪刀复制着泉水的歌谣与内心深隐的叹息。
嗒嗒。缝纫机头奏响着心事的曲调。
针脚扎下庄稼根须的坐标,也扎下他昨夜抹掉的泪痕。
早开张,晚关门,曾被庄稼压弯的脊背,在这间被高楼大厦遮挡住光线的房子里依旧保持着谷子成熟的弧度……他在努力用额头滴落的汗滴缝合住从乡村到城市的那条长长的缝。
做完一个裤缝,裁完一条裤边,伸一下腰,抬一下头,就仿佛举高了一下照亮生活的火把,就仿佛撑高了一下幸福的天空。
偶尔,他会出神地看着窗外,那棵去年才栽的小槐树上有熟悉的喜鹊飞.落下来,他会紧紧地盯上好一会儿,喜鹊小小的脚步,像是一道缝错的针脚……
出租车司机
白天,黑夜,都在以车轮为笔,为城市的指尖描绘着独有的指纹。
一圈。一圈。像是在.NK本上画下一个圆圈,或者打上一个弯钩。对每一个上车的陌生人,都给予十分相熟的问候。
一条付费的路途,方向、里程,全由他人掌控、指挥。城市的地图在脑中描绘,生活的图谱在方向盘上、车轮上绕行……
起步价、计程器、路码表,抽象成为生活的游标卡尺——虚拟靠近真实,距离靠近目标或远方,量来量去,城市的疆域在一脚油门的尽头延伸,给予出一些生活的哲学:
生活有时会在后视镜之后;时光无法倒车。
加油抵达的远方,有时也绕着谎言一般的围巾……夜幕下,出租车是一条钢铁的虫子,循着一种叫生活的光或网前行!
叹息。瞌睡。等待陌生人招手的间隙,指间燃烧的香烟,总会把一些东西烫到无法言说……
环卫工人
黎明悬浮于尘土之上。扫帚计量着街道的宽度,脚印丈量着城市的长度……口罩遮挡着咳嗽的密度。
纸屑和落叶捎来秋风的速度。
瓜果残破的外皮寄存着季节的含量,沉重的乌云抖落早晨的雨丝,细如发丝的雨,闪动针尖的亮度,刺穿反光背心,直抵写满风雨的皱纹……凉意向内,骨骼里居住着四季的风雨,蕴藏为静止的斑斓。
街道上密集的车、人,一再用速度与密度纠正着扫帚的方向与力道,这支笨重的“指挥棒”,总是能为城市多余的东西找到新的高音部。
一年四季都在早起晚归的人,用一声干咳说出生活无声的信念:“把街道当作一页稿纸,我亦是城市乐章的书写者……”
一把扫帚,浸满夜色的墨汁!
三轮车夫
在千万颗汗珠流经、冲刷的日子里,脚蹬三轮车终于换成了机械三轮车,生活安装上了发动机,有了强有力的奔头。
车里运送的物品,每装载一次,每卸载一次,就又获得了半个进入城市楼房的“台阶”……十万零八千级台阶!
“把三轮车开进楼房里……”是你向城市递出的“挑战书”。
嗒嗒鸣响的发动机.,是“进军”的战鼓,你把自己想象为冲锋的战士,三轮车的体内就居住下了一匹马的魂魄——向前,向前!前进,前进!
穿梭于大街小巷,无论是运送笨拙的物品,还是运送轻巧的物品,都有轻拿轻放的心思,如内在深隐的性格,在城市拐角的风中,把自我的影子雕刻成为一些字词的原初之意……
向前,在一个人有限的认知里,三轮车的三个轮子较之汽车的四个轮子,更要用汗滴去拼凑、焊接、打造那些缺失的部分……自信自己的身上有流不完的汗水,它们都有车轮一样的圆润光滑!
汗珠滚动,车轮滚动,城市巨大的钟表之上有马奔跑的蹄音……也有三轮车奔跑的声音。
钉鞋匠
扎入皮子的那根尼龙线,弹拨出心头的絮语;缠绕在机车上的那截尼龙线,栖落、储藏着经年累月的磕睡与骨头中的颤痛……
一把遮阳伞,撑起。几副小马扎,摆开。
摇动机车的手臂,或画着城市虚无的指纹,一圈,一圈;或勾勒着一枚虚无的太阳,安放于目光之中的鞋子,都是搁浅的舟船或者鱼儿……安于心中的信念,抵御着横流的寒。
钉人鞋底之中的钉子,是探人矿藏的锚杆,是埋在皮肤之下的骨头,也是骨头之中钉人的钢针……太阳高悬,露出一枚烧红的铁钉的尖端。
脑袋再次眩晕起来的那一刻,黑色的商务皮鞋,性感的红色高跟鞋,肥胖的蓝色运动鞋,轻巧的粉色拖鞋……都是从矿井中运送出来的煤炭,或是从河水中打捞起来的鱼儿——那年,那时,他用手中的撬棍撬下一块冒顶的煤,他用手中的钓竿拉起一条咬钩的鱼……回过神来,月亮射下来的银色锥子正在扎进城市黑皮鞋的鞋帮……他想起手术台上,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划开他的皮肉,把几枚钢针钉人他的骨头之中,
离开黑色的煤块,拿起黑色的皮鞋,从煤矿工人到钉鞋匠,一根尼龙线缝合住他走过的所有夜色,一枚钢针挑开眼角,放进来一缕光……
厨师
菜肴的味道比他的脚步跑得更远,比他的声音传得更快……
他的脚步大多留在了这方烟熏火燎的四方空间里。曾被愤怒的妻子咒骂为:穿白衣戴白帽的驴子。在他的记忆里,乡村的驴子总是围着磨道在转圈。驴子一直在用它的四蹄画着心中的太阳。
厨房之外,太阳昏沉沉的,雪花为它镀亮一道银边。
灶膛里的火焰就是他心中的太阳,照亮他的脸庞,还照亮他手中铁质的大勺子。上下翻飞的蔬菜是他写给远方的信笺,一把调料,调制出文字与心情中遗失的味道……
呕当。嚓嚓。铁质的勺子碰撞着铁质的锅子,还有瓷质的盘子、碗……在额头的汗珠将要滴落下来的那一刻,他觉得又听到了火车碰撞铁轨的声音……呕当,呕当,呕当。
一列火车驶过,一盘蔬菜炒好,端走,一段旅程结束,他手中紧握的勺子恰似检票的铁钳,明亮、灼热,在闷热的烟雾里,他回忆起一次遥远的旅程……
他的火车票燃烧在了炉灶之中。勺子举起来,他发现铁柄之上已经被时间擦出了月亮的冷光泽。在勺柄之上,他的叹息声随着一滴汗水滴落,在油腻的地板上碰撞出沉闷的回音。
理发师
带水的发丝是海里打捞出来的海带,需要用吹风机烘干海水中的咸涩,一把梳子有挑肥拣瘦的权利,也有指手划脚的喜好……
剪刀是梳子的随行兵,把梳子空谈的理想落实在头发种植出来的麦田里……咔嚓!咔嚓!黑色的头发在剪刀的咔嚓声里,有一亩麦田的意象,剪刀心直口快的性格,总是藏不住多余的秘密,一剪刀下去,剪错的发型要剪掉更多的发丝来遮掩,像一个谎言要用千万个谎言来补救,像一步走错,要用千万步来纠正……
剪刀咔嚓的声音,教会使用剪刀的人许多无声的哲语。
隐于锋芒之中的语言,像他木讷的性格,总会在沉默中喷发出火山的岩浆。恰似在一个电影桥段中,他看到一把剪刀变成了刺杀的利刃。
城市在他絮絮叨叨的语言里,有一片海的深度,他说那些海带似的发丝,在梦里勒住了他的脖颈,还勒住了他的手脚。
那时,他正在追赶着自己被骗的钞票,每一张钞票之上都长出了可以飞奔的双脚,忽然间又长出了可以飞翔的双翼……
疼痛让他从梦中醒来,握着剪刀的手上悬浮着一枚红色的太阳,瞬间滴落为一股红色的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