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园集》旧影
张建智
一
《汉园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是一本布面精装的小巧诗集。橄榄绿色的细布封面,烫银的边框,居中印书名及诗集的三位作者,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右下角则钤一方圆形“商务”印章,封底则是暗纹的“C”“P”两个字母与汉字“商”构成的倒三角形奖杯状标志,另有一袭灰底黑字的薄护封,自有一种肃穆的气象。这一简洁素雅又不失考究的书装是商务印书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经典风格。我所藏的这本《汉园集》是同年八月的再版本,时隔五月,诗集便再版,对当时初出茅庐的三位诗人,应是极大的肯定,之后“汉园三诗人”之名不胫而走。
全书并无序跋,原本有数行题记,但商务印书馆给印丢了。书问世后卞之琳只能自印少量“书签”(正面为题记,背面为勘误表)夹在一部分书中以为补救:

这是广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年来所作诗的结集。我们并不以为这些小玩意儿自成一派,只是平时接触的机会较多,所写的东西彼此感觉亲切,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便起见,所以搁在一起了。我们一块儿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记得自己在南方的时候,在这个名字上着实做过一些梦,哪知道日后来此一访,有名无园,独上高楼,不胜惆怅。可是我们始终对于这个名字有好感,又觉得书名字取得老气横秋一点倒也好玩,于是乎《汉园集》。
汉花园大街如今已不为人所知,但在当时因为毗邻北京大学红楼却是个热闹地界,只要报上“汉花园”,车夫便知是去北京大学。那时,正是京派文化圈活动的鼎盛之期。胡适由上海重回北京大学,把新月诗社的同仁活动也带来北平;朱自清家每周末都举办读诗会;林徽因总布胡同的家中文化沙龙也是不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各类文学社团的同人刊物层出不穷。三位年轻人得以沐浴了古都北平最后的风华。

其中,卞之琳就读于北京大学外文系,李广田比卞之琳年长四岁,但因多读了几年预科,与卞之琳同级,也在外文系求学,而何其芳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比卞之琳低一级,就读于哲学系。在相识之前,三人已在各种杂志、副刊上读过彼此的诗作,何其芳读过卞之琳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上的作品,而卞之琳也对何其芳和李广田在戴望舒主导的《现代》杂志上刊登的诗作有印象。相互报了各自的诗作,便立刻有了熟悉亲近之感,之后三人往来更多,常常作诗谈文,还一起帮臧克家出版《烙印》,帮靳以编辑《文学季刊》和《水星》等,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卞之琳生性内敛拘谨,他自谓何其芳和李广田两位的组织和交际能力都强于自己,但他惜才爱诗,却是闯劲十足,不怕冒失。所以当郑振铎编“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要收他的一本诗集时,卞之琳便挑头将三人之前的诗作,编成一部合集出版。
二

《汉园集》收录了三位诗人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的作品,其中何其芳的《燕泥集》诗十六首,李广田《行云集》诗十七首和卞之琳《数行集》诗三十四首。“汉园三诗人”中,卞之琳和何其芳多被人归为现代派,有象征主义的特征。但两人的诗歌除了遣词造句都极其考究精致之外,从意象到气韵均有很大差异。而李广田的诗,则具有迥异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也正是《汉园集》的魅力所在,薄薄的一本诗集,带给读者的却是极其丰富的心灵体验。如若按诗集顺序依次读来,《燕泥集》让人如步入绮丽绚烂的迷幻宫殿,《行云集》则让人如仰卧秋意苍茫的林间,《数行集》则又带着读者回到北平萧索的街市,饮下一碗苦茶。
《燕泥集》的第一首诗是《预言》,这也是何其芳最为人推崇的诗作。何其芳一生诗作并不多,他后期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散文创作中。但只要读一下《预言》这首诗,还是会让人由衷地佩服,他真是一个天才的诗人!而且何其芳在创作这首诗时只有十九岁。

经典的诗歌常常有几句朗朗上口的句子,令人读之难忘。但《预言》这首诗,却并不是以若干佳句来吸引人,而是整首诗营造出瑰丽又神秘的氛围,牵着你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幻境。
全诗由六小段组成,恰似六幕短剧,讲述了一个唯美而带有神话色彩的爱情故事。开篇描写诗人期待心中女神的来临,“夜的叹息”“渐近的足音”“竹林和夜风的私语”都象征了诗人凝神侧耳倾听,那忐忑又期待的心情。而“麋鹿”这一西方神话中代表纯洁性灵的意象,让人眼前铺展出波提切利筆下的春之画卷。紧接着的第二幕,则是全诗最美的一段,如一首温柔的小夜曲,诗人并不实写女神的美,而是通过月色、日光、百花、绿杨、歌声一连串意象,让读者自然想象她的美好和生机盎然,以及诗人陶醉其中的甜蜜爱意。
第三、第四段,故事有了转折,色调也开始由明亮转为沉郁,“请停下,停下你长途的奔波”“不要前行!前面是无边的森林”,这两句立刻让之前舒缓的节奏陡然变得紧张,表现女神将要飘然离去,而诗人竭力挽留。“野兽身上的斑纹”“半生半死的藤蟒”,也带来了危险和黑暗逼近,相爱的人无法长相厮守的预示。
第五、第六幕,诗人在无法阻止女神离去时,充满深情地呼唤道:“一定要走吗?请等我和你同行!……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你可以不转眼地望着我的眼睛!”让整首诗的情绪推升至了顶点。
而全诗结尾处:“像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啊,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与开篇女神悄然来临时,“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呼应,而“预言”在结尾处的再次出现,又带有宿命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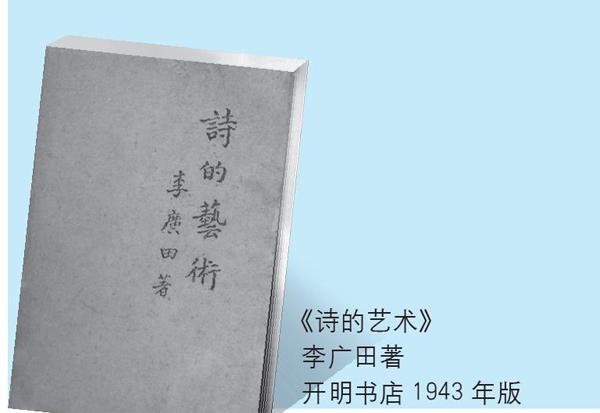
整首诗除了动人的情节,“通感”的运用也很高超,浓丽斑斓的色彩溢于笔端,让读者如入画境。何其芳谈自己的创作时说:“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然后费力用苦涩的推敲用口语去表现那些颜色那些图案。”所以如果说卞之琳的新诗长于音律,何其芳的诗则以色彩见长。这一特质,也贯穿于他的散文中,使他之后的《画梦录》能独步文坛。
何其芳早期诗歌的另一个特色,是浓厚的古典诗词意韵。这一时期,白话新诗的创作,诗人都会从古典诗词中汲取养分,而何其芳的诗歌是最接近南唐北宋花间词气质的。
何其芳出生于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一个富庶的地主家庭,其父何伯稽生財有道,通过做面粉生意和养猪积攒下不少钱。所以何其芳从小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古典文学功底十分扎实。但同时因为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对他极其严厉,母亲姐妹则对他宠溺有加,有一点像红楼梦中的宝玉。这反而让何其芳幼年时精神极其孤独和敏感,唯美的诗词正治愈了他的心灵世界。何其芳曾回想青年时期:“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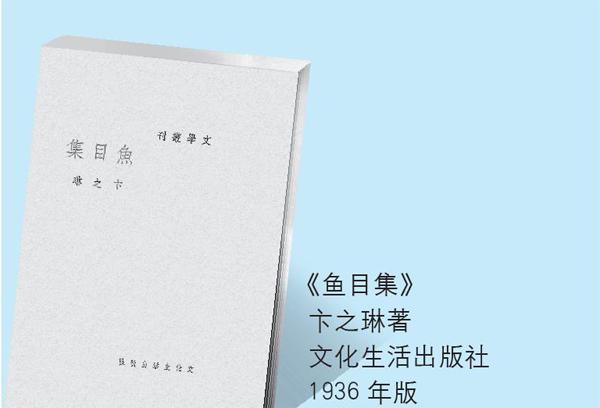
何其芳的诗中常爱借用女性的口吻和视角,来倾吐对恋人的不舍,或对自身命运的悲怜,描写细腻入微、婉转柔美。如《休洗红》一首,诗名本身就取自词牌名,全首以第一人称,模拟了一位罗衣褪色的少妇的哀怨,“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我的影子照得打寒噤了”,宛如一幅温庭筠笔下的弄妆梳洗迟的闺中女子图。
三
有学者总结《汉园集》中三位诗人的风格,认为何其芳是浪漫主义,卞之琳是象征主义,而李广田是现实主义。但细读李广田的《行云集》,与其说他是现实主义,莫若说他的诗歌更偏向于回归自然的现实主义。
读这些李广田写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诗作,总让我想到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惠特曼奉行美国哲学家爱默生提出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认为自然蕴含了个体所追求的人类价值。自然界无所不在的自由、活力和创造力令他身心振奋。李广田的诗歌,在我看来与惠特曼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他笔下出现的植物、动物、山川、清风、流云自有其精神内涵。
李广田的诗作是三人中最具乡土田野气息的,他是真正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他出生在贫苦的农家且从小父母双亡,在亲戚家成长。这让李广田对农村生活有更深入的体验,有更深厚的热爱。所以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他便回到家乡,投身于中学教育,抗战时期他带着学生辗转于大后方,几次撤校复校,却从未放弃办学的理想。
李广田多以天空、大地等自然景物来抒情,并不使用晦涩的意象,真挚而质朴的情感扑面而来。《地之子》一首最具代表性:
我是生自土中,
来自田间的,
这大地,我的母亲,
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
我爱着这地面上的沙壤,湿软软的,
我的襁褓;
更爱着绿绒绒的田禾,野草,
保姆的怀抱。
我愿安息在这土地上,
在这人类的田野里生长,
生长又死亡。
以大地喻母亲,以沙壤为襁褓,田野象征保姆的怀抱,如今读来,比喻和意象显得太过平常而缺乏新意,然而因整首诗开阔的格调、素朴的情绪、深沉的感情,读来仍有直指人心的地方。李健吾在评论《汉园集》时便说:“素朴和煊丽,何其芳先生要的是颜色,凹凸,深致,隽美。然而有一点,李广田先生却更其抓住读者的心弦:亲切之感。”文如其人,“地之子”成了李广田人生和文学的写照。沈从文是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回归自然”“回归乡土”,而李广田则是用诗的形式,让人们理解只有从浮华的都市回归纯净的大自然,才会发现和寻到真我。
李广田的《行云集》中,吟秋之诗占了很大比例。细读李广田的诗,可说秋意无处不在,而且诗人从颜色、气味、声音、温度,从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全方位地描写秋天,可见诗人有多钟情秋天。
秋天的颜色,在李广田笔下是硕果累累的明艳色彩,《旅途》中秋阳余晖下农家墙头挂着收获的瓜果,洋溢着勃勃生机,“不知是谁家的高墙头,/粉白的,映着西斜的秋阳的,/垂挂了红的瓜和绿的瓜”。秋天有气味吗,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气味呢?李广田专门写了一首《秋的味》:“谁曾嗅到了秋的味,/坐在破幔子的窗下,/从远方的池沼里,/水滨腐了的落叶的—/从深深的森林里,/枯枝上熟了的木莓的—/被凉风送来了/秋的气息”。李广田笔下的秋的温度则是温暖怀旧而略带一些悲怜肃杀的,如他在《行云集》第一首《秋灯》里写道:“静夜的秋灯是温暖的,/在孤寂中,我却是有一点寒冷”;秋之音,在李广田笔下是伴着歌者的弹唱而来的,“抱着小小的瑶琴,/弹奏着黄昏曲的,/是秋天的歌者。/……/尽兴地弹唱吧。/当你葬身枯叶时,/世界便觉得寂寞了”。
惠特曼的诗非常接近于散文诗,不受刻板的韵律所约束。在惠特曼看来,写诗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而并非为了形式去强加文字。李广田的诗作也有这一特点,诗的结构习惯于行云流水和朴实自实的语言,使他的诗歌也常流于散文化。李健吾对《行云集》喜爱有加,但也指出:“李广田也在尝试在诗的形式中采用比较自由的文字以配合他那自然朴实的风险,可惜还未达到成熟的境地,所以反而显出松散的缺点来。”这也许使李广田发现,散文更能表达他希望传递的内容和感情。《行云集》几乎要算是他唯一的诗集(其1958年出版的《春城集》风格已完全不同,很难相比),后来他更多转向散文创作,奉献了多部佳作,《行云集》中的十余首诗也是他在现代诗坛上的全部作品了。
盡管不再写诗,李广田对新诗创作理论的探索,并未停止。他在抗战时期出版了《诗的艺术》,成为这一时期新诗诗歌艺术理论的重要著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昆明的李广田还致力于发掘和保护滇中地区流传的民歌,修订了大型叙事抒情长诗《阿诗玛》。
四
实际上,《鱼目集》才是卞之琳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诗集(1933年的《三秋草》为诗人自印)。《汉园集》中的《数行集》虽然在一九三四年便编辑完成,谁知商务印书馆两年后才将诗集出版。而在这两年中,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又希望出版卞之琳的诗集,于是他便选了已编入《数行集》里的若干诗作,加上一九三四年后所作的诗,合起来形成了《鱼目集》。所以《鱼目集》与《数行集》中有不少诗歌有所重合。
《数行集》中,卞之琳更多的是在进行一种新诗的实验,尝试用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诗风,洗练地白描出旧时北平下层人民的生活片断,用诗来凭吊这座古都。卞之琳几十年后回忆起自己写诗的初衷,便是由于北京大学附近那一片充满败落衰飒气息的断垣废井:“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北边一部分以及灰楼那一带当时是松公府的一片断垣废井。那时候在课余或从文学院图书馆阅览室中出来,在红楼上,从北窗瞥见那个景色,我总会起一种惘然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引起了我想写诗的念头……一方面因为那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一方面又因为那里是破旧的故都。”当时他心仪波德莱尔描写巴黎街头流浪汉、艺术家等世井百态的诗,于是也尝试用这一方法来描述北平,那些旧皇权被打破,新旧政府轮流掌权,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人生百态。
于是,人力车夫(《酸梅汤》)、算命瞎子和敲更夫(《古镇的梦》)、守着杂货店打瞌睡的伙计(《古城的心》),这些三教九流的各色小人物,成了这一时期卞之琳诗中的主角。而这些诗的情绪和色调,总是那样荒芜、沉闷、漠然、灰暗,诗人完全采取了旁观者的姿态,笔触冷峻,并不投射自身的感情。最典型的一首便是《几个人》:
叫卖的喊一声“冰糖胡芦”
叫了一口灰像满不在乎;
提鸟笼的望着天上的白鸽,
自在的脚步踩过了沙河,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卖萝卜的空挥着磨亮的小刀,
一担红萝卜在夕阳里傻笑,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矮叫化子痴看着自己的长影子,
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
有些人捧着一碗饭叹气,
有些人半夜里听别人的梦话,
有些人白发上戴一朵红花,
像雪野的边缘上托一轮落日……
这首写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小诗,有如电影中快速切换的镜头,展现北平街市上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但这是一幅缺乏生气的北平风情画,用“空挥”“傻笑”“痴看”“叹气”“满不在乎”等词汇, 一种生命无意义的徒劳弥漫,更加重了寂寞的意味。而整首诗中反复出现的“荒街上沉思的年轻人”这一形象可代表诗人自身,也象征着当时怀抱救国革命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究竟他在沉思什么,诗人并未言明,留给读者悬念和想象的空间,这种“留白”也是卞之琳诗歌的特色。结尾处白发簪红花,雪野映落日,犹如蒙太奇般的叠画,是非常惊人的意象,让人读完久久难忘,意韵绵长。这首诗的音律,看似松散,实际非常讲究,全诗以“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一句形成一种循环往复的效果,又自然地形成场景的分割,同时每两句押尾韵,韵脚自然转换,十分流畅。
这一时期卞之琳在新诗上的另一种实验是,尝试用大白话或方言,以在诗中夹杂着人物对话的方式来写诗。这种尝试可能来源于他新诗道路上的启蒙者徐志摩。在卞之琳之前,徐志摩便已用北京大白话和家乡硖石的方言创作过诗,只是尚未成熟。这一诗歌创作的试验,在卞之琳的《春城》中最为显著,景物描写与各类白话口语对话,交错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起首一段:“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描一只花蝴蝶,描一只鹞鹰/在马德里蔚蓝的天心,/天如海,可惜也望不见您哪/京都!”最后一句老北京话的插入,像一句画外音。而第四段大量使用口语:“好家伙!真吓坏了我,倒不是/一枚炸弹—哈哈哈哈!/真舒服,春梦做得够香了不是?/拉不到人就在车磴上歇午学,/幸亏瓦片儿倒还有眼睛。/‘鸟失儿也有眼睛—哈哈哈哈。”显然这是一个人力车夫,在春日的北京,百无聊赖地闲侃着。尽管这种以方言口语入诗的方式并未在白话诗中成为主流,效仿者也是寥寥,但诗人的这一尝试,无疑丰富和拓展了新诗的可能性。
沈从文在写给卞之琳《群鸦集》的序言中说:“之琳的诗不是热闹的诗,却可以代表北方年轻人一种生活观念,大漠的尘土,寒国的严冬,如何使人眼目凝静,生活沉默,一个从北地风光生活过来的年轻人,那种黄昏袭来的寂寞,那种血欲凝固的镇静,用幽幽的口气,诉说一切,之琳的诗,已从容地与艺术接近了。诗里动人处,由平淡所成就的高点,每一个住过北方,经历过故都公寓生活的年轻人,一定都能理解得到,会觉得所表现的境界技术超拔的。”
五
《汉园集》问世之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三人都已毕业离开北大,各奔东西。卞之琳在青岛埋头译书,李广田回到济南的中学任教,而何其芳则在天津南开中学。其时华北特殊化、《何梅协定》,日军对华北步步紧逼,而国民党和军阀的软弱退让,明眼人皆可看出,华东迟早也将是日本的囊中之物。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自然对这一局势感到忧心,但却无力改变现实,便充满了无力感,陷入自我怀疑的消极之中。
何其芳在《汉园集》出版三个月后所作的《〈燕泥集〉后话》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当时他的心情:
今年春天,之琳来信说我们那本小书不久可以印出,应该在各人的那一部分上题一个名字……之琳乃借我以“燕泥集”三字。我当即回信说,这个名字我很喜爱,因为它使我记起了孩提时的一种欢欣,而且我现在仿佛就是一只燕子,我说不清我飞翔的方向,但早已忘却了我昔日苦心经营的残留在梁上的泥巢。是的,我早已忘却了,一直到现在放它在我面前让我凄凉地凭吊着过去的自己,让我重又咀嚼着那些过去的情感,那些忧郁的黄昏和那些夜晚,我独自踯躅在蓝色的天空下,仿佛拾得了一些温柔的白色小花朵,带回去便是一篇诗。
当时才二十四岁的诗人,文字中却是一片凄凉。那年五月,何其芳目睹了抗日救国游行的学生潮水般地经过南开中学的操场,他却只远远地旁观着,看到了青年人的热血终将白流的无望。之后他离开天津回到万县老家,又辗转至胶东教书。于是一九三七年,“汉园三诗人”在青岛重聚几日,彻夜长谈,共同迎接了“西安事变”和全面抗日。之后,何其芳与卞之琳一起到了成都,并一同奔赴延安,从此改变了诗人的生涯。卞之琳写下了《慰劳信集》,何其芳写下了《夜歌》,诗的风格已与之前大不相同。
《汉园集》记录了三位诗人沉醉在文学中的纯真年华,夜晚重读这些诗篇,抬头恰望见一轮秋月。无论人世多少变迁、悲欣离散,月亮永远皓洁明亮,不染纤尘。忽想起,三人在诗集中都有吟月之诗,怀想着三人在北大汉园时,是否也曾沐浴在这月华之下,思恋、乡愁、忧国,都化为悠悠明笛、数行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