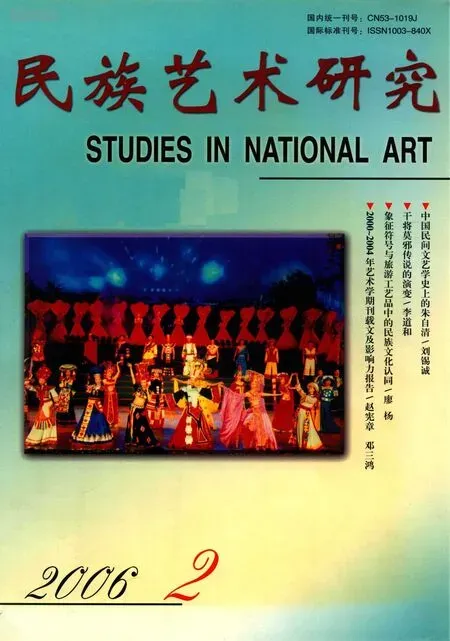在世界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
——以敦煌题材的舞蹈创作为例
慕 羽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先生1992年的这个表述如今已成为国际共识;而他1985年关于敦煌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及其汇流之地的论断①1985年季羡林的文章《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原文是:“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也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敦煌为创作题材的中国舞蹈作品就具有天然的“世界性”。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部以此题材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40年来一直受到文化界的整体关注,此种现象倒是不多见的。其后,敦煌题材的舞剧不胜枚举,其中也有一些舞剧被看作是“再生”的敦煌艺术,但鲜有舞剧作品真正切入敦煌文化的底蕴。
以敦煌为题材的舞蹈创作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面对今日的 “世界语境”,我们需要不断探寻敦煌文化的古与今,以及“本土” (native)与“他者” (the other)、“主体”(subject)与“他者”(the other)的关系,还要总结舞蹈创作的艺术规律,进一步探讨艺术表达的种种可能性,推动当代中国舞蹈从业者对敦煌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敦煌的包容,既有中国古老智慧的回响,也应有现代中国的呼应,敦煌题材艺术作品,未必一定全是古时的传奇或中国人的故事,而应召唤出跨越时空的人类性,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所蕴含的包容精神。期待着能再有敦煌题材的传统舞剧或当代舞蹈剧场,抑或是实验性的 “总体艺术”作品,能引发超越舞蹈界本身的更多有关艺术、文化和社会议题的探讨。
一、《丝路花雨》的划时代意义
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甘肃歌舞团在京成功演出《丝路花雨》①2004年10月《丝路花雨》以“演出时间、场次最多的舞剧”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中国舞剧之最”。,成为当时舞台艺术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从1979年到2019年, 《丝路花雨》盛演不衰,堪称中国舞蹈史上的 “现象级”作品。它改变了样板戏一统舞台的局面,带来了“舞蹈文化意识的苏醒”②冯双白:《新中国舞蹈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温润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在诸多方面,《丝路花雨》是极有历史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
对音乐舞蹈界而言,它带来了整个古代乐舞文化的复兴。越来越多的舞蹈人意识到,虽然我们无法让传统乐舞重现,却可以尽可能地“接近”它,并依据“有文字和形象资料可资稽考”③孙颖:《中国古典舞十论》,载王伟主编:《中国舞蹈高等教育30年学术文集——中国古典舞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的历史文化遗存去创作,这需要舞蹈创作和理论先行,其后才是编制教材。《丝路花雨》在舞蹈界造成轰动的原因还在于其创立了“敦煌舞”——另一种“中国古典舞”本身,尽管这一名词是后来才产生的。1980年,傅兆先预言式地指出:《丝路花雨》“既复兴又创建了一个既古老又新奇的舞蹈语言系统,那就是‘敦煌乐舞学派’”④兆先:《〈丝路花雨〉的舞蹈语言》,《文艺研究》1980年第2期,第98页。,更准确地说,是开启了一个“敦煌舞学派”,与此同时,甘肃艺术学校的高金荣也正创建着“敦煌舞教程”。正如于平所言,《丝路花雨》“对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的扬弃是就一种特殊意义而言的——即《丝路花雨》扬弃了中国古典舞历史遗存之‘独尊’‘唯一’的地位,中国古典舞的‘多元’局面在这种扬弃中出现了。”⑤于平:《“古典”的寻觅与建构》,《舞蹈》1990年第1期,第34页。
值得一提的是,《丝路花雨》对文化界的划时代意义更是我们不应忽视的。“英娘的琵琶为什么要反弹?”就引发了新中国第一代民族音乐学学者毛继增⑥毛继增:《英娘的琵琶为什么要反弹?》,《中国音乐》1983年第2期,第89—89页。和敦煌学专家高德祥⑦高德祥:《敦煌壁画中的反弹琵琶与反弹箜篌》,《音乐爱好者》1989年第5期,第11—12页。等的考证与热议;舞剧的叙事构成和方式非但不是对文学的亦步亦趋 (无论是否有意识),还启发了文学家以敦煌题材进行创作,神秘的敦煌学也走近了普通百姓的视野,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说明该剧“编者对历史素材的运用虽非直接,但也并非随意改铸,而是建立在严肃的分析研究结果之上精心提炼后方进一步想象扩张的。”⑧段文杰:《真实的虚构——谈舞剧〈丝路花雨〉的一些历史依据》,《文艺研究》1980年第2期,第103—108页。可见,以历史资料本身为准绳的古典舞(剧)创作是有文化价值的。难怪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并实际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段文杰先生将其称为有“一些历史依据”的“真实的虚构”。
1978年和1979年舞蹈学者董锡玖分别在《舞蹈》《文艺研究》第一期发表文章,题为《漫谈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和 《从敦煌壁画的乐舞艺术想到的》⑨董锡玖:《从敦煌壁画的乐舞艺术想到的》,《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第101—103页。,这是舞蹈人在跳出“文革”思想禁锢后的一次自觉的文化探寻,文中提及在敦煌文物研究所顶尖专家的帮助下,甘肃歌舞团的舞蹈家们满怀敬畏之心,对敦煌壁画进行了多次观摩、临摹和学习,“创作了大型舞剧《敦煌曲》”⑩舞剧内容包括画工苦、民族恨和光明赞三部分,其中阶级斗争是主旨。(《丝路花雨》初稿名),还细致地描写了初唐220窟北壁《东方药师净土变》的胡旋舞场面……令人欣喜的是,胡旋舞就在同期上演的舞剧《丝路花雨》中得到了再现。而《丝路花雨》中最著名的女主角英娘反弹琵琶舞则取自112窟《无量寿经变图》的伎乐舞姿,跳出了丰富生动的态势。初演时,有人还担心“妩媚”似乎与“阶级性”对立,后来看过演出现场,才放心。①参见张苛:《漫谈人物》,《舞蹈》1980年第4期,第5页。对于佛教石窟中飞天的形象,舞剧也进行了很好的描摹,舞蹈家们逐渐摸索出形成敦煌舞三道弯舞姿的S形行动路线。
在2019年6月北京舞蹈学院举办的首届敦煌舞蹈文化研究论坛上,通过《丝路花雨》的编导之一许琪老师的讲述,我们才获悉,该剧的出台得益于舞蹈史学家董锡玖向时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舜瑶的提议②董锡玖:《敦煌缘》,载《缤纷舞蹈文化之路》,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而《丝路花雨》的命名则归功于吴坚部长的灵感。在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艺术家和领导的推动下,《丝路花雨》终于在改革开放后的神州大地播散出了一路花语。
该剧对于丝绸之路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剧中父亲神笔张的原型是五代画工塑匠赵僧子,女儿英娘一角受《女奴多宝卖身契》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的故事启发,而对英娘卖艺的敦煌集市的呈现则与159窟《宋国夫人出行图》不无关系;波斯商人的形象则取材于45窟《胡商遇盗图》,刻画的是唐代的商贸生活。有意思的是,敦煌壁画的某处角落中一个画工留下的姓名“张思义”,也成了神笔张这个主人公名字的参考。与后来不少“一带一路”题材舞剧不同的是,该剧建立起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的连接,而不是把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硬要放到一个历史大背景下。
《丝路花雨》“没有更多地关注敦煌舞蹈中有多少佛教艺术因素,从舞蹈再回到宗教去发现、钩沉,或者强化舞蹈的宗教色彩表现”③贺燕云:《从敦煌壁画复活的神奇舞蹈—— 〈丝路花雨〉主演谈敦煌舞的编创、表演及教学》,《艺术评论》2008年第5期,第56—62页。,而是从佛教造像审美的角度探求当时的现实性和艺术性,即对当今社会的历史价值,这一题材也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它通过对亲情、友情的赞颂,讴歌了热爱世界和平的中国文化精神,彻底摆脱了“阶级斗争”和盲目排外的痕迹,被视为“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正面塑造外国人的舞剧。④参见傅保珠:《中国民族舞剧的传世精品——经典舞剧〈丝路花雨〉》,《丝绸之路》2010年第1期,第63页。2014年初,《丝路花雨》作为“中华风韵”品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伦敦进行了3场演出,新闻报道引用了英国律师约翰的评价:“舞剧不仅讲述了中国古代的感人故事,更传递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价值观。”⑤新华网:《中国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在伦敦首演》,2014年1月20日。民心相通,以及超越民族、种族的和平向往,对正在经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今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者们认为“在我国世界题材的艺术创作中,像《丝路花雨》这样以中外人民友谊作主题的历史性作品,还并不多见,仅从这一点上说, 《丝路花雨》就是一个新的创造。”⑥谢长余、李文衡:《绚丽多彩的民族舞剧新花——漫谈〈丝路花雨〉的创作和演出》,《飞天》2000年第8期。而且人们并“不曾把它看成那种牵强附会于思想观念的 ‘时代传声筒’式的作品。”对此法国《世界报》曾评价说:“这个舞剧以自己的方式,适度地描绘出人民之间的友谊。”⑦杜琪:《舞剧文学的宏构巨制——对舞剧〈丝路花雨〉评论的思考性回顾之一》, 《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第90—96页。近年来,几乎与改革开放同岁的舞剧《丝路花雨》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其不断巡演、加演,“以仁为本”的人物形象,“以合为美”的艺术呈现,就 “弘扬 ‘一带一路’ 愿景精神而言,是一部难得的力作。”⑧邸含玮:《构建新型“一带一路”文化——从舞剧〈丝路花雨〉看开去》,《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8—23页。
敦煌,原本就是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在15世纪西方人经 “地理大发现”开拓出“早期全球化”道路前,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人就启动了中西方交流而非扩张的国际化路径,敦煌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敦煌”二字,虽然古人从字面上阐释为“大”和“盛”,但越来越被现代学者认为是汉朝以前的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音译,它也承载着文化融合与交流的意义。不过,“地理大发现”后由西方人主导的 “全球化进程”,是由农业交流、科技进步和工业化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也伴随着“殖民化、市场化、资本化、民主化、民族化、国家化、区域化”①何志全,杨琴:《从“三个世界”理论到全球化现实》,《党史文汇》2017年第7期,第51—55页。的延展。遗憾的是,中国有好几个世纪并未真正融入其中,或呈现出极端不平等的“殖民”与“被殖民”的被动关系,敦煌也曾被遗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一退一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主动和积极的姿态重新参与世界新一轮的“全球化”,尤其是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国家,以及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全球化”参与度越来越深入,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相比,则是“一升一降”。②王栋,曹德军:《中国引领世界进入“再全球化”进程》,《人民论坛》2017年第32期,第60—61页。
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却引发了一些“中国威胁论”和 “文明冲突论”的调子。余秋雨先生在其网络文化课程中,提及他曾于2013年在联合国的演讲中用《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里边的话在国际上来反驳“中国威胁论”,给我印象很深。该书第一卷第六章指出,这位明朝时期来中国的老外几十年研究出的一个重要答案:“中国文明(中华文明的主体部分/农耕文化)的非侵略、非扩张的本性。”《丝路花雨》这部在改革开放初期绽放的世界友谊之花,便承载着这一中华文明“协和万邦”③“协和万邦”原出自《尚书·尧典》。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首次提出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基因的“四观”,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的核心精神。恰如法兰克福孔子学院德方院长克里斯汀娜的感慨:“艺术家借用舞蹈,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富有开放、包容等现代意识的中国,一个并未引起西方人足够了解和重视的中国。”④任姗姗:《阔别32年的回归〈丝路花雨〉巡演英法德 讲述独一无二的“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4年2月6日。就这个意义上讲,《丝路花雨》既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
二、讲怎样的“敦煌”好故事
余秋雨另有一句话也说得好,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千年中,谁在建窟,谁在画像造像,还有那窟中的佛像,画中的万物生……这些石窟内外尘封的生命,值得我们书写和表现。而千年石窟在百余年的复苏中,则又带出了新的生命故事——谁在破坏,谁在守护,谁在研究,谁在凝视,也浸透着无数的生命叹息和感怀。敦煌好故事,就应该是有关敦煌文化的生命故事。
(一)有关“千年生命”的敦煌故事
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不能直接成就每一部敦煌题材的艺术作品,艺术创作应该避免浓墨重彩地以 “敦煌”为旗号、为背景、为名义, “表面化地利用敦煌形象的审美价值。”⑤张懿红:《〈日落莫高窟〉:多声部与历史真实》,《文艺评论》官网。敦煌曾是“华戎交汇的都会”,敦煌壁画彩塑是千年中宫廷文化、社会生活、宗教现象的反映,既承载了中国古代千年的社会变迁,也是佛教文化的载体,真实地记录了佛教的东传。的确,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只是一个宗教事件,正如藏经洞内也不只有丰富的各派佛教典籍,也藏有不少官方和私人的档案。而就舞剧创作而言,大部分叙事性舞剧作品都走向了世俗化、套路化,涉及不同种族和民族的联系,以及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交织,我们在戏剧冲突和较量中看到了爱国情怀、远行传奇以及爱情升华,剧中的角色除了有不断被请上舞台的王昭君、马可·波罗、张骞等,还有不少虚构的商人、画师、公主、渔女、歌舞伎人、将军之女,但总体来讲,主流范式叙事性舞剧难以深入表现古代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议题,也较少触及佛教文化的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257窟《佛说九色鹿经》的经变画则有了多个舞剧版本。这个佛教故事受到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本身就具有佛教社会化的特色,体现为“把传统佛教的抽象本体心性化、伦理化”⑥赖永海:《东方文化研究(之佛儒之异同及其相互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0页。,反映了人间世俗的善恶价值标准;而近年无论是张娅姝的独立制作版本《九色鹿》 (2017),还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童话芭蕾版《九色鹿》 (2018),以及史敏更早的舞剧版本 (2009),都未回避“人人皆可成佛”的理念,也是颇让人欣慰的。可以说,在由佛经改编成的讲唱文学的“变文”和绘成画作的 “经变”中,都可以有 “对佛菩萨慈悲精神的重新发现和演绎。”①王建疆:《敦煌艺术:从原生到再生——兼议著名大型乐舞〈丝路花雨〉成功演出30周年》,《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25—30页。
敦煌题材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有不少国外的艺术家曾推出过自己的舞蹈作品,比较特别的是1994年的日本舞剧《大敦煌》,该剧也曾为祝贺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而来华演出。②参见刘峻骧:《日本舞剧〈大敦煌〉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舞蹈》1997年第5期,第30—32页。编导花柳千代以日本传统舞蹈来表现的正是285窟 《五百强盗成佛图》的故事,颇具文化融合以及普度众生的意味。
另外,近年颇具“当代审美”气质的舞蹈剧场作品中,也蕴藏着佛教精神,而这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如舞蹈诗剧 《莲花》(赵小刚/2014)将着眼点放到了造像人的佛心上,一尊敦煌彩塑是如何被刻画出来的呢?“塑匠”不一定就是乐尊,塑造的过程便是修行的过程;莲花的意象既让人想到社会君子人格,也是佛国净土的象征。而 《西游》(赵小刚/2015)和《一梦·如是》(王亚彬、平原慎太郎/2018)的主人公虽然分别是玄奘和鸠摩罗什,却都不同于传统的单线叙事;甚至可以说,“讲故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讲故事。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都探讨了现代人如何审视历史。《西游》重在“重走玄奘之路”,哪怕这条道路需要耗尽我们的精力,也要坚持到底;最后舞者向观众席爬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只是“玄奘”了。在《一梦·如是》中,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王亚彬以第二人称的方式让我们与鸠摩罗什共同对话。最终,我们与舞台上的现代青年一般,仿佛“见证”了微弱的理想之光被点燃,光芒万丈……
在同类作品中,引发热议的是陕西省歌舞剧院的《丝绸之路》 (杨威/2016),该剧以“路”为核心,高度浓缩了时空,提炼出7个符号化的典型人物,没有特定的主角,也不以“演故事”为出发点。这条路上,有“行者”的宗教热忱,有 “市者”的利益追逐,有“游者”的逍遥快活,有“使者”的使命召唤,还有 “护者”的疆场驰骋以及“和者”的家国担当……这几个角色有些抽象,却又是历史人物的隐喻;而颇为巧妙的是,抽象化后的“引者”又被形象化为一位女子,被赋予 “某种”精神制高点③“引者”是一个牵引者的隐喻,对于不同的人,受不同的感召之引。对“行者”而言,其精神制高点就是佛教文化的精神。,与“行者”共舞。作为一部国有文艺院团出品的舞剧作品,有人质疑《丝绸之路》 “既无舞,也无剧”,笔者倒认为这恰是这部作品的独特性所在,“无舞”意味着没有纯粹表演性的舞段,“无剧”就用不着陷入模式化的叙事,不再复现“地方特色+爱情故事”的套路。该剧中所展现的7位象征性人物走出的不同“道路”相互交织的场面,带给人非常强大的视觉震撼,只是少了对核心观念的探讨,以及对角色主体间性内在精神关联的深度关照,稍显遗憾。但该剧叙事手法上的另辟蹊径,仍是非常可贵的创新。
(二)有关当今敦煌“供养人”的故事
敦煌文化的兴衰沉浮,其实并不仅仅属于过去那一千年中的“生命信号”,还有刚过去的这一百年来的生命跃动。20世纪初“藏经洞”的发现犹如被解除了尘封千年的封印,其后的探险与掠夺、抢救与保护让其命运跌宕起伏。莫高窟的遭遇令人扼腕痛惜,还激发了不少文人志士漂洋过海将一些祖先遗言“搬”回来,而莫高窟千年累积的洞窟、壁画、彩塑……也在缄默中等候着能与之生命相伴的有缘人——不同于驻足停留的画家,或是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终于成了为之殚精竭虑的敦煌守护者,当今的敦煌 “供养人”。相对于个体生命,半个世纪的岁月何其漫长,但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常书鸿、向达、段文杰、史苇湘、樊锦诗、欧阳琳、孙儒僩等人的生命早已与敦煌融为一体,他们一生的修为不也属于敦煌文化的一部分吗?令人欣慰的是,在他们的身上写着大大的“尊严”二字,这样的文化觉醒与过往备受欺凌殖民的“耻辱感”划清了界限。
难能可贵的是,中央芭蕾舞团版《敦煌》(费波/2017)将主人公设定为20世纪中叶至今的敦煌守护者,成就了一部表现现代“敦煌人”的作品。如今提及敦煌, “保护”当然是“第一位”的,而那些一生一世都致力于敦煌保护的艺术家、学者当然值得被历史记忆。这一次,芭蕾版《敦煌》为他们而舞!
与《丝路花雨》类似,芭蕾版 《敦煌》也做到了基于“历史依据”的 “虚构”,使“讲好中国故事”有了实现的基础。该剧以念予、吴铭作为爱情主人公,延续了舞剧惯常的双人舞推动剧情的模式。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浪漫而略带忧伤,其中涉及的情感表达不像现实这般沉重,也没有落入三角关系的俗套。念予是一位留法的音乐家,她不正像是那些从浮华都市、高等学府或是亲密爱人身边来到敦煌朝拜的有心人吗?当然他们中有的人只是匆匆过客,就像曹舒慈扮演的念予,一位率真可爱的年轻艺术家,但她的才华和情感抉择最终都没能聚焦于敦煌;有的人则全然为敦煌交付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正如我们的男一号吴铭,在其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身影。常先生与敦煌的不解之缘不正是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偶遇 《敦煌石窟图录》开始的吗?而他与留法雕塑家陈芝秀的姻缘尽散既有人性的脆弱、价值观的差异,也是动荡时代的不幸。而“吴铭”这个称谓,更隐喻了更多默默无闻的敦煌人。剧中的“小乐山”也象征着这些敦煌人的后代,他们几乎就是在“千佛洞”长大的,生活虽清苦,却有斑斓的壁画相伴。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由张剑扮演的水雯,她不仅始终不渝地陪伴在男主身边,更是许多将青春播撒在敦煌的普通人中的一员。对几代敦煌守护人而言,在物质上他们过的都像是修行一样的清苦生活,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富足的,因为敦煌已经几乎充盈了他们的全部心田。当然,这也是三代敦煌守护人秉承的“莫高精神”,体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责任担当。
该剧在舞台呈现上没有浓墨重彩的情感宣泄,也没有着重于表现跌宕起伏的时代变迁,反倒更多地展现了那些平凡的敦煌人真实的生命境界。总体看来,该剧实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想象的融合,编导在素材选择上规避了莫高窟曾经受到的绵延不绝的战火、盗掠与动乱侵蚀,主要将地震带来的洞窟坍塌作为情节发展的一个转折,虽然显得单薄,却也在提示我们,如今莫高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不可逆的自然因素。不过,该剧以 《敦煌》为名,有些 “大题小做”了,改名为《敦煌儿女》或《敦煌人》可能更适合。
三、如何用舞蹈“讲好敦煌故事”
在世界语境中讲敦煌故事,不应是一厢情愿的情感宣泄,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般的分享与对话,最有效的就是文化力①“文化力”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一种温润的巧力,这种柔性力量,其魅力和吸引力终会转化为文化影响力。。我们期待着将来再有敦煌题材的各种与舞蹈相关的作品,能引发超越舞蹈界本身有关艺术和文化议题的探讨。那么,敦煌题材的舞蹈创作如何能在世界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呢?这里的“故事”倒不一定就是具有连贯性情节的故事, “讲好敦煌故事”并非指狭义的“情节叙事”,而是广义的“文化叙事”,涉及话语技巧和叙述行为。体现在舞蹈创作上,则可以涵盖“重建”并探索敦煌乐舞的剧场形态,创作叙事性的民族舞剧,以及进行当代审美的舞蹈剧场或跨界艺术尝试等。
(一)敦煌乐舞的剧场化重建
兰州歌舞剧院的舞剧《大梦敦煌》 (陈维亚/2000)在舞蹈界名声很响,有人称赞它的创新,称颂它的演出业绩,但在文化界、戏剧界却评价不高。这不由得让我又想起《丝路花雨》,余秋雨曾在《莫高窟》一文中写道:“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①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61页。此种说法虽说是文学性表述,却一语中的。如若没有潜心钻研、考证,同时又赋予其艺术的想象,英娘的“反弹琵琶舞”何以能如此传神,且又十分契合人物身份。真正投入了心力的创造才能触动“许多人心底的蕴藏”。当然,敦煌乐舞的剧场化重建有很多途径。
其一,敦煌乐舞剧场化形态“重建”不是“复原”。敦煌乐舞“把人间的东西搬到神奇的佛国”②高德祥:《敦煌壁画中的童子伎》,《中国音乐》1991年第2期,第40—42页。,其中已经充满了画工一样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说,敦煌乐舞本就介于现实描摹和艺术想象之间,立足于现代剧场形态的“敦煌舞”犹如 “身体临摹”,就像是现当代画家对于敦煌壁画的“临摹”一般,对其形态要一丝不苟地“描摹”,但对敦煌乐舞进行剧场化形态重建其实是一种再创作了,它并非“复原式”临摹,音声行为和乐舞空间的表现上有较大的灵活度,不受客观之物束缚。
2019年6月,北京舞蹈学院史敏导师工作坊的《伎乐天》就把我们带入了非复原式临摹的敦煌文化意境,汇集了包括女性和男性比较完整的伎乐天敦煌舞风格。作品以莫高窟112窟中的 “反弹琵琶”、148窟中的“六臂飞天”、220窟药师经变画中的“敦煌健舞”等艺术形象为创作的本源,为了忠实表达原作精髓,必须做到对内容和形式胸有成竹才行,所以做足案头工作是必要的。该作品在前期扎实的田野基础上经由艺术家大胆创新,舞台空间变成了天宫,所以你能看见在地面上“飞翔”的飞天,而且透过倒映在舞台半空中的镜面,也有一种壁画上的“飞天”从佛国降临人间的灵动感。整台演出形态丰富,有单双三人、四人舞,就像是壁画一角的聚焦与放大:三人舞 《闻法飞天》让148窟的“六臂飞天”形象跃然舞台。双人舞《反弹琵琶品》妙在 “品”,串联起了飞天伎乐形象、舞者和观者之间纯粹的心灵沟通,壁画中的琵琶不止于乐器,更像是“法器”;而此舞的高明在于舞者“弹奏”的是虚拟的“琵琶”,“慢而不断,快而不乱”,两位舞者动静高低、张弛有度,犹如玄妙高超的琵琶演奏技艺,更传递出一种自如祥和的意愿。女子群舞《七步生莲》隐喻佛陀诞生时的莲花意象,男子群舞《雷公鼓》则将敦煌壁画上的古乐器“十二音雷公鼓”形象化了,雷公和小鼓都是由舞者扮演的,众“小鼓”环绕着“雷公”,造型和动态各不相同,却又与“雷公”合体,相得益彰,让观众沉浸在艺术的想象中,明明是独奏,却有合奏的效果,而这也体现为一种物我结合、“似与不似”的中国美学。最让人动容的是群舞《心灯》,那是身着中国风现代服饰的史敏老师带领众舞者跳的最后一支舞,舞者们所呈现出来的是当代人从祖先那承袭而来的宁静祥和的神态,这也是整部《伎乐天》的整体基调,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渗透了心意同构的想象力。
其二,敦煌乐舞剧场化“重建”应基于文化重建。拿敦煌壁画中的儿童乐舞来说,敦煌学专家高德祥指出,“童子伎”的画面非常多,共分为三类:分别是佛教极乐世界的“化生伎”,古代民间庆祝活动的“百戏伎”以及宣传佛教教义的 “经变伎”等。③高德祥:《敦煌壁画中的童子伎》,《中国音乐》1991年第2期,第40—42页。通过艺术创作,就像当初的“反弹琵琶舞”一样,复现一些壁画中的舞蹈,或是 “一带一路”历史时空中的舞蹈,使这些舞蹈和文化语境产生共生关系,对观众而言仍是颇有期待视域的。再比如胡腾舞与胡旋舞究竟有什么不同?中亚粟特文化在与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印度文化、西域文化等构成的复合文化话语场域中,乐舞和风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毕竟,这些被汉人所接受的粟特舞蹈被称为“胡舞”正是文化交流的见证。而且,胡乐入华之华化与中原乐舞之胡化也是交相呼应的,余秋雨说两者构成了“双向同体涡旋互生”的交融模式。当然,舞剧中,这些舞蹈的复现还要与民族融合的故事紧密结合起来,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关乎着千年生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文化互渗及兴衰与政权更迭有关联,却还要遵循另一套相对独立的文化逻辑。胡乐舞文化的变迁起伏,以及与中华乐舞的互渗互生早已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见证。
其三,敦煌乐舞剧场化的多模态话语重建。“敦煌舞”并非一个历史称谓,而是今人对源自敦煌莫高窟佛教艺术壁画的乐舞进行创造性“复现”的一个说法,其中饱含了舞蹈人的文化寄托,也有利于敦煌舞学科的创建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以文化重建的心态来审视“敦煌舞”,会发现这个词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谓之“敦煌乐舞”或许更好,这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上自魏晋南北朝经隋唐至宋元千年中,敦煌壁画中所涉及的佛国伎乐和世俗乐舞;同时,也可以看作“多模态话语”。受到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启发①参见朱永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外语学刊》2007年第5期,第82—86页。,敦煌乐舞多模态重建应该基于图像、动作、音声、颜色、材质、技术等复合话语符号系统上,由艺术家们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动觉等模态以及想象力的激发而产生。
2017年7月,中央民族乐团推出了一台创新型作品——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就使观者的听觉与视觉、动觉打通,形成了难得的通感和联觉。因为这是一场你需要“看”的音乐会,也是一台有情节人物角色,有形体动作行为,有对白吟诵歌唱,有灯光布景多媒体的器乐表演,除了传统的已知乐器,还有不少复原的敦煌传统乐器与乐队,渗透着考究的人文历史观。笔者想象未来也有一台创新型的民族敦煌乐舞剧,可以让多模态话语完全构建起一个文化语境:复原的敦煌乐器、复活的敦煌舞蹈、再生的历史人物以及虚实相生的空间行为,从服饰造型、乐队规模、乐器种类,到风格化舞姿,还有丰富的面具、舞具等,都经得起推敲,或许会是一个奇妙的体验,引导我们进入高僧的传奇旅程,或是经变故事现场、世俗生活场景,抑或是去体验极乐世界的神秘氛围,一次次温润并点亮人们的心灵。
借助于音乐人类学家梅利亚姆 (A.P.Merriam)的相关理论和 “信仰 (观念、概念)、行为、音声”三元理论模式分析方法②参见艾伦·帕·梅利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敦煌乐舞的本体重建应聚焦于“敦煌文化中的乐舞重建”,分析其身体行为、音声行为③音乐人类学研究深受梅利亚姆“概念、行为、音声”和“音乐是文化”或“音乐作为文化”观念的影响。学者们突破原来的“音本位”音乐观,把一些文化中的音声当作研究对象,此为“音声论”(人声、乐器、乐曲)表现。和天乐舞、俗乐舞活动空间,还要结合信仰观念和仪式活动进行研究。其中,手印、持莲、披巾、手舞、足蹈、奏乐、爬杆、踢碗、劳动、行船、走马……都是身体行为,可以包括概念行为、演奏行为、舞蹈行为、杂技行为、社会行为等具体行为及仪式过程。这种做法需要各类艺术家和学者共建联盟、协同创新。
(二)敦煌题材的舞剧创作
一般来说,按艺术形式和舞蹈语言风格,舞剧可分为芭蕾舞剧、现代舞剧(广义现代舞的舞剧)、民族舞剧;若按审美定位和舞蹈表现手法,可分为传统舞剧、现代舞剧(现代主义)和当代舞剧(后现代以来)。实际上,上述分类并非一成不变,而时常是交叉共融的。比如芭蕾舞剧除了古典审美,也会有结合现代舞的现当代形态芭蕾舞剧以及融合了民族舞的民族芭蕾等,而民族芭蕾也是民族舞剧的组成部分;另外,虽然民族舞剧以突出表演性民族舞蹈“可舞性”为主要表现手法,但也应该对当代审美突破抱有开放态度,深入探求舞剧艺术的规律,并保持打破规律的勇气和眼光。
首先是舞剧人物性格及其关系的设置上,避免扁平化倾向。戏剧界有专家认为《大梦敦煌》中“莫高和月牙的爱情故事与敦煌壁画的创作没有有机的联系。”④欧阳逸冰:《舞剧与戏剧文学》,《舞蹈》2005年第2期,第1页。而早于它的《丝路花雨》则更为真实鲜活。当然文学理论家们对此的分析也是一分为二的。对于不同于“革命文艺家”的普通民间艺人形象,杜琪的文章指出 《丝路花雨》中英娘的塑造“作为一种人物类型的性格代表,她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然而作为一种‘这一个’……她的性格塑造仍是一种古典派戏剧创作通常采用的‘扁平’方法。”①杜琪:《舞剧文学的宏构巨制——对舞剧〈丝路花雨〉评论的思考性回顾之一》,《甘肃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90-96页。这使得英娘“具有某种理想化色彩”,只 “表现一个单一性格特征,也就是只表现被视为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韦勒克、沃伦语)”,而“弱化了其性格内容的个别性”。相对而言,神笔张已经初步具有“圆形”人物的初步特征。作者用西方文学的“扁形人物论”来分析英娘的形象,还是比较到位的。其实,这不是《丝路花雨》一部剧的问题,如果说当年还只是个别文学家对舞剧文学的苛求,然而其后它几乎成为大量涌现出的中国舞剧的一个“通病”。
其二,民族舞剧可向西方现代心理舞剧汲取养料,也可以借鉴虚实相生的中国古典美学。虽然有学者认为,敦煌乐舞表演或许可以“视为是俗讲的幕间表演”②参见李建隆:《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演出与演出空间》,上海戏剧学院2010届博士论文,第69页。,就是在用通俗的说唱来宣讲经文过程中,插入乐舞演出。但在舞剧创作中,却要避免敦煌乐舞只是作为表演性而非戏剧性的“插舞”。在一篇题为《幻象艺术手法初论》的文章中,文学研究者陆林这样描述并分析了舞剧《丝路花雨》中的一场“神奇幻象”:
主人公神笔张怀念飘零异国的女儿英娘,神游天宫——仙阙瑶池,群星璀璨,金光如柱。十二神女手持箫管琴瑟翩跹而至;英娘伴着十位仙姑婆娑起舞;伊努思乘飞毯飘然来临……这个幻象,生动地再现了神笔张强烈的思女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热烈的憧憬……这就是幻象艺术手法。③陆林:《幻象艺术手法初论》,《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96—99页。
不同于单一型现实主义舞蹈美学,《丝路花雨》已经用到了心理舞蹈创作手法,将想象放大和延伸,既连接起了戏剧人物的父女情,又呈现出“反弹琵琶伎乐天” (莫高窟112号窟《伎乐图》)的灵感来源,还极为符合敦煌艺术美学。敦煌飞天不似西方天使会长出翅膀,恰如宗白华所言:“敦煌人像,全在飞腾的舞姿中(连立像、坐像的躯体也是在扭曲的舞姿中);人像的着重点不在体积而在那克服了地心引力的飞动旋律。”④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244页。
芭蕾版《敦煌》也实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想象的融合,舞者们以中西相融的艺术表达为敦煌保护者们起舞,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对敦煌文化的主动创造、传播和发展吗?给人印象最深的便是该剧对于“时间”的诠释,在舞剧创作技法上不落俗套。三重时空的交织或重叠,使千年莫高窟的岁月累积奇妙而浪漫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分别是现代的敦煌保护者、千年画僧以及壁画中的飞天。第二幕,男主吴铭似乎完全与地震后惊现的重层壁画世界融为了一体,飞天群体曼舞的景象,不辨男女,我们宛若看到了西域风格飞天的意境。而纱幕上飞舞的飘带并无飞天实像,也让人惊喜:不知是飘带地飞舞带动了身体的翻飞,还是身体地飞舞让飘带翩跹。当纱幕上的飘带与排成纵列的飞天重叠时,舞者们有的昂首挥臂,有的悠悠降落,有的凌空回首;虽然都没有被悬吊高举,但色调斑斓高贵,形态变幻万千的飞天构图已跃然台上。穿梭其间的千年画僧更是点睛之笔。遗憾的是,群舞飞天意象的流动性不够,静态的造型感少了些中原飞天风吹云动的灵气。
如果说上述两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还是“以舞演故事”,而赵小刚的《莲花》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情节叙事,整部作品表现的是“塑匠”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的交汇,剧中人具有“超越角色”的魅力,编导更在意自我、角色与他者的关联。如同歌德《浮士德》所言:“他们又走近了,飘摇不定的形影,就像当初在迷茫的眼前现形。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
舞蹈本身的隐喻性、抽象性本就是一种特别的叙事手法,艺术家们可以放飞想象空间来进行舞剧的结构,当然在时空叙事手法上也可以向“超现实性”和“多角度叙事”①程洁:《敦煌变文的叙事时空》,《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95—101页;程洁:《敦煌变文流动变化的叙事视角》,《保定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72—79页。的变文以及“多视觉中心”的经变画借鉴。学者指出,隋朝经变画“从表现形式上分为四类,1.长卷式构图;2.单幅结构;3.对称构图;4.以说法场面为中心的中轴对称构图。其中第四类成为唐代以后最流行的构图形式。”②赵声良:《敦煌隋朝经变画艺术》,《敦煌研究》2018年第3期,第1—8页。舞剧不一定把线性叙事进行到底,或是强调故事的完整性,而是关键性情节得到强调,在叙事时空处理上也可不拘一格。比如用调度的方式实现“聚焦”“倒叙”“散点透视”,壁画叙事的“异时同构”“异空同构”③参见周维平:《试论敦煌壁画的空间结构》,《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2期,第83—87页;冯坤:《从敦煌壁画的构图浅谈叙事的时间与空间》,《文学教育(中)》2014年第5期,第81—82页。与舞台表演中的 “异时异空共舞”相互辉映,让作品获得通向深邃 “心灵空间”和无限“宇宙空间”的途径。
总之,敦煌题材的舞剧创作,无论采用何种审美定位,共通的一点是要把敦煌舞蹈语言变为舞剧语言,变成人物和角色的语言,不能只是晚会式的杂糅化舞蹈展示。就敦煌题材的民族舞剧而言,强调敦煌舞的传统风格与舞剧叙事立场、视角的现当代审美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当代审美中本就可以有对古典美学意境的当代演绎。
(三)舞蹈剧场和“总体艺术”创作
同是创作,与敦煌乐舞剧场化的多模态话语 “重建”不同的是,跨界的 “舞蹈剧场”和 “总体艺术”强调的是复调语言的“探索性”与“实验性”;相通的是,舞蹈不一定成为中心,而是将可听、可视、可感、可体验、可沉浸的多个感知层面打通。舞蹈剧场不是“舞蹈” + “剧场”,它们之间恰如“身体性”和 “剧场性”构成的婚姻关系,相融却又各自独立,不一定要有 “情节”,更倾向于进行观念的表达。舞蹈剧场的环境、身体、音声、装置等各元素并没有等级之分,虽然也有所谓身体性强于剧场性的作品,但“身体性”和“剧场性”元素本身是精神独立的存在,呈现出 “并置”状态,在“对话”中展开联系,互为主体,笔者称其为“复调剧场”。
赵小刚闲舞人工作室的“肥唐瘦宋系列舞剧”已显露出混合型本体质感。比如《莲花》的“剧场性”就体现为服饰、造型、装置营造的圣洁佛境,而非具体的莲花;而舞者“身体性”的隐喻也是莲花的形象化演绎,舞者们或为错落有致、形神各异的群佛像,或为圣洁典雅的一朵蓝莲花,或依偎缠绕的并蒂莲,抑或是虔诚的供养人,或是一位年轻的修行沙弥……该作取材于莫高窟的创始人乐尊的精神感召,但剧中的形象早已穿越时空,也超越了具体的角色,他们的“舞蹈”虽源自敦煌壁画不同朝代的形态,但当代人的身体意识已融入其间;“剧场”也不止于镜框式舞台,当舞者走下舞台,融入观众时,每一次演出空间都构成了一个“特别场域”,就好比万事万物其实都是远近各种关系的偶然组合,这样不也体现了佛性吗?而此种“缘起性空”的清净祥和不也正是当代人所需要的吗?佛心也可是一种人性的日常。闲舞人的《莲花》恰恰以中国式舞蹈剧场的方式,走近了这种“社会性”,非常可贵。
相比于舞蹈剧场,“总体艺术”更强调各艺术参与者的独立性。提及“总体艺术”,我们应追溯到19世纪中叶,德国作曲家、导演、理论家瓦格纳就曾提出过相似的观念“Gesamtkunstwerk”④参见瓦格纳:《瓦格纳论音乐》,廖辅叔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其观点主要体现在1849-1851年间的《艺术与革命》《未来的艺术作品》《歌剧与戏剧》这三篇论文中。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音乐理论范畴,启迪着很多中外艺术家和理论家。艾德里安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总体艺术:环境,偶发与表现》中也承袭了瓦格纳的理念。),中文通常翻译为“整体艺术观”,就像他的“乐剧”一样体现为一种更完整的戏剧观,瓦格纳的 “未来艺术”为今日的“总体艺术观”奠定了基础。只不过瓦格纳的“乐剧”仍然属于音乐范畴,但“总体艺术”不再以某一种艺术形式为核心,而且不会只生成一个艺术品整体,或一个戏剧作品——其音乐不是配乐,而是可独立品鉴的声音;其舞美也非视觉装饰或戏剧氛围的营造,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视觉艺术,或是具有文献价值的文本以及日常生活品;其舞蹈不是悦耳悦目的“插舞”,而是能凸显文化意义的身体语言,也能依据当下语境而不断变化……当然,演出空间也不一定是“镜框式舞台”或“露天舞台”,它可以是适用于特定作品的特别场域,剧场、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都是可能的选择。
可以说,总体艺术是瓦格纳艺术观(Total work of art)的当代发展,各元素之间不再陷入“手段”与“目的”之争,它们各自独立,却彼此成就,相互转化,碰撞激发出一种全新的“互文性”体验,这意味着总体艺术中的各种元素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或者说,“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①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第21—30页。,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融合性本体”。而且,演出空间和观众也应是这个“总体艺术品”不可或缺的部分。当代“总体艺术”不同于瓦格纳的声音(声乐和器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整体艺术”,对每位观众而言,“大脑(诗歌)—心脏 (声音)—肢体 (舞蹈)”②参见瓦格纳:《瓦格纳论音乐》,廖辅叔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页。这个比喻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作用,比如在某个特定场域中,即便是画师塑匠创造艺术的过程和行为也是身心合一的,也可被视为舞蹈,而并非代表“活力”的某个身体部位的运动才谓之以 “舞蹈”。对 “总体艺术”作品中彼此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每个部分,观众都可以有只属于独立个体的体验,可感知整体,也可获得聚焦于局部,甚至观众也能成为表演者被凝视。
李建隆2010年的博士论文中,将敦煌乐舞演出空间总结为 “台、栏、池”等关键字③参见李建隆:《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演出与演出空间》,上海戏剧学院2010届博士论文,第71页。,基本是四周有栏杆、两侧是礼佛 “乐池”的露天舞台,而且大多修筑于水池之上,其实表演者的舞台并非画面构图的核心,诸佛所坐的莲台才是。他认为,敦煌壁画中的观演关系本来就有“两个空间系统,一个是经变图中的观演关系,另一个是进入洞窟中进行佛教活动的佛教信徒与经变图之间的观演关系。”④参见李建隆:《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演出与演出空间》,上海戏剧学院2010届博士论文,第88页。换言之,壁画内外的个体都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观者可以用耳朵听,眼睛看,用身体来感受,由情感生发,还能归入理性。这不由让人设想一种“特别场域”的实景或虚拟场景创作,敦煌乐舞与3D打印的洞窟同处于一个可以拓展的空间里面,或者戴上VR眼镜的你走入一个融入现实人生的数字敦煌的立体世界,视觉艺术仿佛被注入了时间性,它也呈现出了“表演性”。表演艺术则与视觉环境融为一体,你会发现表演者的动静起伏往往关联着你,即便是静止的雕塑壁画,或是司空见惯的生活品也被重新唤醒了生命,能让你沉浸进去感知生死,体验天人合一、渡人渡己。
艺术家和理论家对“总体艺术”都能有创造性的重新诠释。在笔者看来,敦煌艺术是一种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的共生,“总体艺术”强调“场域”,也是一种时空的共生、观演的共生、文化的共生,共建公共话语空间的过程比物理空间和结果都更有意义。近年坚持“总体艺术”实践的艺术家和学者邱志杰认为,“总体艺术就是以文化研究为基础的艺术生产”,体现为“物、人、事的一种状态,我们称之为艺术态”⑤邱志杰:《一个房间里的总体艺术》,雅昌艺术网,2016年9月6日。,而且这个创作行为应该具有社会性,是应该被“编织在日常生活之中”的。
艺术家可以将对敦煌舞蹈的探索纳入舞蹈创作中,将其角色化、人物化,或是概念化、观念化,将历时性、多样化的“敦煌故事”资源转化为共时性的、可对话的舞蹈作品。在舞剧的人物形象塑造上,在以观念探寻为中心的舞蹈剧场和总体艺术上,如何“在追求人的现代化的同时,毋忘保持我们民族性格的‘优根’”,已经成为一个值得中国舞蹈人不断深思的命题。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当代热词“讲好中国故事”,学者王一川说得有道理:
真正的中国好故事,不是来自个人或群体的无病呻吟,也不是来自文化产业的跟风炒作,更不是来自艺术管理部门的行政指令,而应当从我们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处自动流溢而出,正像泉水是从泉眼里涌出来的一样。这种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正在于我们的自由的个体心性对我们所身处于其中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真切体验以及竭力脱困的奋斗过程中。①王一川:《当今中国故事及其文化软实力》,《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24期,第22—26页。
笔者坚信,在世界语境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既是文化的,也是社会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个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