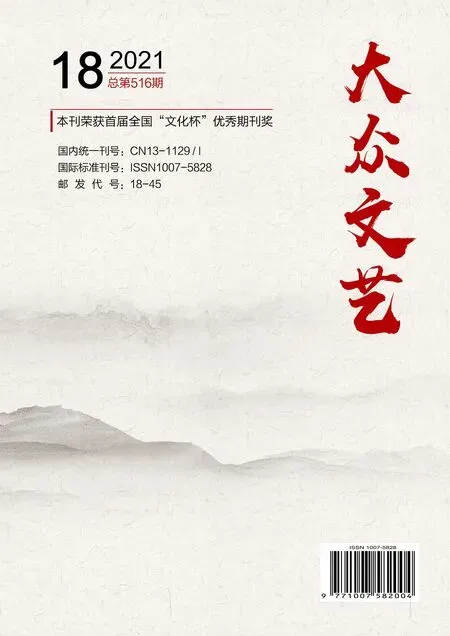仇英《竹院品古图》读解
韦惠欢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00)
文人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对社会极具有影响力和特殊作用,文人间的聚会是具有较高精神追求和深厚文化内涵的一种活动。雅集是文人酬唱聚会的一种形式,包括了文学创作、艺术鉴赏、宴饮赏玩等丰富的内容。文人从来都轻物质重精神,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文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趋向多元化,开始追求自我理想的实现与自我情感的表达,于是成群流连于山水亭阁之中,常以此来寄托超凡脱俗的性情,为雅集提供了客观条件。正是因为艺术本性的相契合,使得产生了以文人雅集活动为主题的作品,用图像的形式去表现文人雅集会事的场面。无论是对前人雅集题材的描绘还是对当代雅集聚会的场景表现,画面中的物象都具有一定所暗含的意义去存在于作品之中,深入分析其所代表的意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以雅集为题材的绘画艺术作品。
一、仇英《竹院品古图》题材及内容
北宋驸马都尉王诜之第西园是当代文人墨客多雅集之地。元丰初,王诜曾邀同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陈景元、王钦臣、郑嘉会、圆通大师(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十六人游西园。文人在此吟诵诗歌、观画赏书、琴阮合奏,相得其欢。参与此次雅集的成员李公麟还为此创作《西园雅集图》来纪念此次活动,之后一再被后世画家所绘制,南宋赵伯驹、马和之、马远、刘松年、元人赵孟頫、钱舜举等皆有摹本,降至明清,唐寅、仇英、王式、尤求、李士达、石涛、华喦、丁观鹏等亦多仿之。
《竹院品古图》描绘的便是苏轼、米芾等文人品赏古玩的情景,出自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中的一幅,绢本设色,纵41.4厘米,横33.8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画中作者以两块屏风为画面分割线,将画面分为前后两个场景,两个场景通过作者对具体细节的刻画描绘与整体意境的把握共同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右侧屏风中绘有山水画,画面中亭台楼阁置于山中,两山之间绘有远帆。画面中心位置有一青铜觚,内有一枝红珊瑚。前景的右侧,两位雅士正在观看桌案上的册页画,右前方有一侍童负挂轴而来,中间一个端着古物的侍童正向左侧的文人走来,这位雅士正放下手中的茶杯准备品古。在文人后方的桌上陈列着卷轴画、青铜器、玉器等古玩,剩下的侍者或手捧乐器,或端器盒,或拿画卷,雅趣盎然。远景竹林间设有棋台,一侍童于竹林空际中正置棋具,摆置棋盒的侍童可能表明三位文士刚刚下完棋或即将要去下棋。在置放棋盘的石桌旁边绘有两犬在嬉闹,一犬伏地举首状,更增加了画面活泼欢悦的气氛,另外还有一侍童在院内生炉摇扇烹茶。屏风后绘有太湖石、丛竹装饰画面,太湖石下半段被屏风遮挡,画面中的鹤隐匿在太湖石后,与两犬的嬉戏形成一动一静的对比,保持了画面平衡感。画面右上端的竹林巷道慢慢消失,引导读者的视线向画外延伸,在有限的空间中使读者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此图以文人雅士聚于竹亭之中品评古玩字画为描绘对象,表达了文人雅士雅集文会这一主题,作者用细腻的笔法将人物情态一一表现,既注意处理画面情节的具体性,又注重环境气氛的烘托,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
二、《竹院品古图》艺术语言
在构图上《竹院品古图》独具匠心,屏风的倾斜放置营造了一种独特的雅逸活动氛围,有一种动态的势,顺着势的方向会给人产生一种画面内部延伸的空间感。前景中围坐在一起品古画、鉴赏古玩的文人以及伫立在旁的侍者,与屏风后的景色形成了一静一动的对比,使画面的审美意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画面的人物安排上,大部分人物被放置在前景部分,屏风后面只绘有两个侍童,这里一散一聚的布置方式使画面富有节奏感。棋桌旁边的侍童与画面左下角仕女呈对角线构图,为画面增加了纵深感,提升了立体感。
屏风一直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巫鸿先生在《重屏》中写道:人们可以把一扇屏风当作一件实物,一种绘画媒材,一个绘画图像或三者兼具。换言之, 屏风是一种准建筑形式,占据着一定的三维空间并对其所处的三维空间进行划分,屏风也是一种绘画媒材, 为绘画提供了理想的平面——实际上它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最古老的绘画形制之一。[2]在仇英《竹院品古图》中,屏风对整体空间起到了分割作用,屏风后面的围栏与台阶同样也有分隔空间的作用,台阶围栏又将屏风后的空间分割,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耐人寻味,准确传达出作品的形式与内涵。
北宋郭熙所言绘画的“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绘画中表现同一时间不同人物活动,或者不同时间的人物活动。强调观者的视角需要用一种“游”的方式“读”画,仇英在《竹院品古图》中便能体现出观察点在画面中灵活移动的特点,人的视点随着画面人物、动物、植物的变幻而移动。《竹院品古图》使我们观画的目光不断随场景的置换而移动,观者随着画面场景活动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思考。画面将人物以叙事性的方式联结成一个整体,并与山水有机结合。
《明画录》有载:“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后寓吴,初执事丹青,周东村(臣)异而教之,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3]由此得知仇英跟随周臣临摹唐宋名画,能做到媲美真迹的地步。周臣主要是对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的院体画传承。拜师周臣,使仇英同样受益于院体画,无论人物、山水都是精描细染,有着扎实的造型和绘制能力。在作品的描绘中,塑造人物形象利用墨线勾勒,并用重彩加以渲染,精描细绘,将文人举止的高雅潇洒,侍女容貌的端庄娟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画中山石轮廓由勾改写,这样的处理使原本刚硬、单一的线条出现了浓淡、干湿等丰富变化。《清河书画舫》中记载:“(仇英)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4]屏风上所绘的山水画用青绿与墨色相辉映,近景中山石用小斧劈皴表现,加以水墨晕染,降低了斧劈皴给人以坚硬的视觉感受,而呈现出圆润的特色。画面远景的丛竹山石用健润的墨线勾出,再以淡墨渲染,整体色调和谐、清雅。左侧屏风中的花鸟画采用唐宋花鸟画中的折枝式画法,运用工笔重彩,兼容写意,背景用丹青和淡墨渲染,更加予以一种清雅幽远之意。
三、《竹院品古图》表达的精神内涵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往往爱好托物言志,通过借植物的一些属性特征以抒发性情,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追求。白居易曾在《养竹记》中归纳总结出竹之“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的崇高品格,第一次将竹子的品性特征人格化[5]。之后,竹便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文人画中的表现亦如此。《礼记·祀器》有载:“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6]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等人纵情山林,逃避现实寻找慰藉,隐世避居,竹林便成为他们的栖息地、托身所,远离尘嚣,与自然相融,找寻解脱。竹子超逸脱俗的资质令风流名士们风驰神往。竹子寓意不屈不挠、宁折不弯的气节,占据画面后景中的大片竹林,从侧面代表作者所要表达的心境。
画面中太湖石后面的孤鹤,作者仅仅描绘了鹤的上半身,顺着仙鹤的目光所望,正是竹林间巷道远去的方向,予一种孤独之感。这与前景中文人围坐在一起品古画、鉴赏古玩的热闹场景形成对比,且屏风中的鸟儿与屏风后的两只小狗都是以成对的形式出现,孤鹤与之对比,更是孤寂与凄凉。鹤在中国文化中有高贵、孤独、超凡的意思,画中的孤鹤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元素,图中的鹤不仅仅象征主人追求高隐超然物外的精神,同时作者将孤鹤掩于石后,隐喻了一种避世退隐的思想,寻求心灵的解放。
屏风在功能上是作为空间隔断物,但作为文本图像,屏风除了单纯是画出来的图像,也在图像内容中隐藏和传递一些思想或意味。在绘画中,“屏”一直被赋予某种精神内蕴,符合古代文人喜好将自然界中的“物”寓以思想情感,使其成为某种精神含义的载体。屏风中的自然景象与屏风外的人物形象融为一体,屏风中云雾缭绕的山水景也是从侧面反应作者向往自然的内心世界。因而,当屏风作为一种具体物象存在于绘画中时,屏风上的艺术表现也并非仅仅是作为装饰而存在,同时隐性地表达了作者的某种人生追求或人格力量。
左侧花鸟屏风描绘了两只喜鹊立梢头,绿意盎然,呈现出和谐安宁之境,刚好与作者所处时代的纷乱形成对比,暗指作者对安定无纷扰生活的憧憬。远景处的林荫道延伸出画外,可理解为是作者想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明显的展示出了其士人气质以及对文人理想的追求。
整体画面描绘具有写实性,而屏风中云遮雾涌,二者形成鲜明对比,虚实相生,相互呼应。屏风后面的大片竹林在画面中属于真实场景,画面后方的竹林、太湖石以及通往远方的小道又将观者引向作者所要表达的理想世界,实中有虚,增加了想象空间,屏风也成为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的表达,为观者传递其思想、感情。作者通过实境的描绘为观者营造了具有深层精神内涵的另一理想世界,将作者自己的主观情思外化于具体物象之中。
四、小结
《竹院品古图》中作者对于自然景物的认知并非单纯地“自然性表现”,它包含了在绘画中作者为表现这一自然景物所思考的结果,即作品中自然物象的人格化,是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一种自我修养的过程。画面中的物象无不体现着作者内心与具体事物无法分割的思想,寄寓了作者的内心写照,流露出了对文人风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