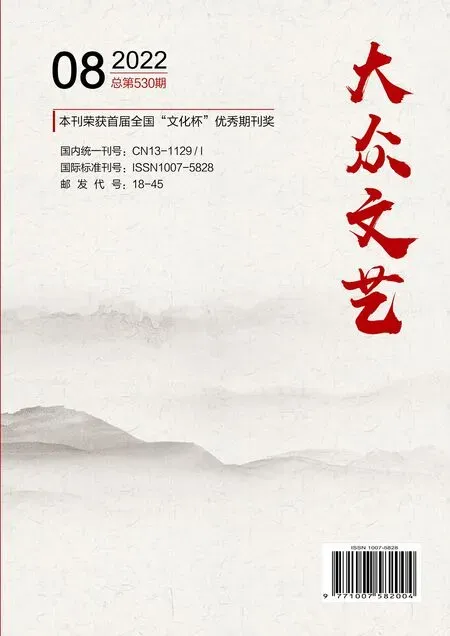悲慨哀婉 淡泊顽艳
——试析仓央嘉措的诗风及其成因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550025)
据《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15期载:“所谓诗风,……不仅是指诗的风格和形式,恐怕应该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中诗歌创作的倾向。”“哀感顽艳”的诗风作为中国诗歌之众多风格的一种,具有表现为真切自然、明艳哀怨及雄浑悲慨等不同层次,而仓央嘉措诗歌的明艳、哀怨、悲慨的风格恰好是这种“哀感顽艳”诗风的典型代表。曾缄在《布达拉宫辞并序》中对仓央嘉措诗歌的评价也是“哀感顽艳”四字,如他的《你见或者不见我》中的诗句:“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默然相爱,寂静欢喜”。其中展现的爱而不得的哀怨感情,以真切自然的表现形式,让读者读之感之。
现实中,仓央嘉措是西藏最大的王,布达拉宫最为人尊敬的神,这样的身份地位是多少世人梦寐以求的。在这样的身份和环境之下,他应该是赞美世间波澜壮阔的活佛。但恰恰相反,他的笔下却有不少诗歌描写的是隐藏着的男女之情,是他内心难以名状的个人哀婉情感。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地位崇高的神如此忧伤而憔悴?本文从仓央嘉措的诗风特征及其成因这一问题切入,从他的现实社会政治因素、个人气质性格、爱情不幸的情感因素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哀而能感:世俗红尘的慨叹者
千百年来,时代不幸诗家幸成为了时代的标记,而仓央嘉措就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西藏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以及等级分明的社会环境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由此,现实社会政治因素成为其“哀感顽艳”诗风的独特影响因素。
仓央嘉措 (1683—1706),全名阿旺洛桑仁青·仓央嘉措,第六世达赖喇嘛。当时,第巴桑结嘉措为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对五世达赖之死秘而不宣。仓央嘉措作为转世灵童也并没有被立即接到布达拉宫。1696年,康熙平定了准噶尔蒙古部落的叛乱,与准噶尔勾结的桑结嘉措密谋败露。桑结嘉措被迫宣布五世达赖己死,选出的转世灵童已经十五岁。1697年仓央嘉措在浪卡子拜五世班禅为师,剃发受戒,取法名为罗桑仁青仓央嘉措,并于十月二十五日进入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正式成为第六世达赖喇嘛。通过仓央嘉措继位的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仓央嘉措所处的时代正当西藏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
然而他的继位并没有使现状发生改变,而是从一开始就陷入政治旋涡。外人的眼中,他是西藏的神,但其实不过是他人的傀儡。本该呼风唤雨,建设一个美丽的西藏,但却只能仰人鼻息、小心翼翼。面对宗教、阶级的矛盾,只能独自叹息抒发内心的愤懑。如仓央嘉措《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
黄边黑心的云彩,是冰雹的成因,非僧非俗的沙弥,是佛教的敌人。
云彩本是世界上最洁白无瑕的存在,但诗人“黑心”一词的使用,让我们体会到的是诗中与此相照应的“黑心”的沙弥的丑陋。佛教本是世间的灵魂圣地,但在现实的污浊中,在利益权力斗争中成为一片混乱。诗人身为宗教领袖却只能对现实无可奈何,只能将内心的哀伤与悲慨形成诗人独特的诗风展现给世人。
当时西藏的宗教已是一片混乱,更别提普通人家的生活。作为最高领袖的仓央嘉措在斗争中被吞噬,甚至流放、搬尸体。而作为社会底层的人民也只能是在压迫与剥削中生活的水深火热。如仓央嘉措《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
心爱的意抄拉茂,是我猎人捕获的,却被有力的权贵,诺桑王子抢去。
诗歌中直白的话语将当时西藏等级分明的现状描述的通俗易懂,上等人可以拥有一切权力,下等人只能在压迫中默默忍受、苟且存活。在诗人本身的性格中,淡泊离世是他的追求。但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有着真性情的活佛,面对着西藏的千疮百孔,怎能不愤怒?怎能不感慨?这些情感迫于现实压力虽然诗人不能直接表达,由此直接促成了仓央嘉措在“哀感顽艳”诗歌中的创作成就。
二、哀而能顽:淡泊自然的叛逆者
除了外在的现实社会政治影响因素外,内在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而仓央嘉措的诗风形成内在原因正是来源于他本人的个性气质和性格。正如顾贞观曾指出:“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诗人的个性气质禀赋是影响诗歌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虽然仓央嘉措在现实中是宗教代表,但其实他的内心是文人才子之心,他本人也是文人才子的典型代表。
仓央嘉措虽然是拥有着权力的王但更是人们心中永远的最有人性美、最具诗性美的活佛、诗人,他的故事流传至今,他的诗歌被人们传诵至今。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仓央嘉措淡泊离世的性格,使他虽然身为活佛却饱含人世间最真挚的深情。如他的《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有如下诗句:
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一个“重”字就可以表现出诗人思绪的惆怅万千,两个“重”字则更是将这种繁杂程度进一步放大,表现出诗人身处俗世内心的无奈,个中感受真乃千头万绪、枷锁重重。这些枷锁或是来自于现实的压力,或是来自于诗人自身内心的不能释放,无论哪种具体所指,都在最后化作了美丽贤淑的佳人,给予他一些心灵安慰。但是真的能逃离命运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终将是诗人一生的悲哀,也是诗歌哀婉的源头。
除了淡泊离世的性情,仓央嘉措骨子里也是一个顽固的叛逆者,甚至说他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职者。正如刘希武曾言“仓央嘉措者,第六代达赖喇嘛而西藏之南唐后主也”,“概其生平,酣醉于文艺而视尊位如敝屣,其与南唐李煜何以异?”仓央嘉措在个人经历上与南唐后主李煜相似,他身为坐在布达拉宫最尊贵位置上的达赖喇嘛,本应以负责西藏政治、宗教事务,维持政局稳定、研习经义、传播佛法、凝聚信徒民心为要务,但他却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公然对抗佛教戒律,追求世俗情爱,他无法对佛法、对虔诚教徒负责,可以说他是一位失职者,是其政治角色不合格的扮演者。
在笔者看来,仓央嘉措却也是一个诚者,他坚持忠于自己的内心,诚实面对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哪怕世人批判也在所不惜。所以他的诗歌哀婉又不失顽艳,让人读来不是一味的“心有戚戚然”。如仓央嘉措《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
结尽同心缔尽缘,此生虽短意缠绵,与卿再世相逢日,玉树临风一少年。
在他心中,虽然这一世作为人们心中的活佛不能拥有自己情爱,看起来似乎是缘分未到,但匆匆一生过后,假如能够再与这位明媚的女子相遇,那个让她念念不忘的“卿”一定会扔掉身份枷锁,变成一个自由恋爱的翩翩少年。通过诗歌,诗人大胆表现自己内心对美好情缘的呼唤,顽强表达出最真实的情感。就世俗的眼光来看,无疑,仓央枷锁是宗教僧佛中的“异类”,但就人的本性而言,这样的他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由此,形成诗风中“顽艳”就尤其令后世读者诵之感之为之无限动容。
进而言之,正是由于仓央嘉措看似矛盾但却又共存的性格,才使他的诗歌风格表现出“哀婉”与“顽艳”两种风格的有机组合。一半淡泊,一半诚实,由此“哀婉顽艳”成为他诗歌风格最好的概括。
三、哀而能艳:唯美感情的失意者
个人方面,除了诗人本身的个性气质、禀赋性格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情感因素对他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其中所产生的的显著作用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仓央嘉措的情诗可以说是诗人所有诗歌作品中最耀眼的明珠,其中有表达对于姑娘的思念之情的;有描写自己与心爱姑娘相会的浪漫瞬间的;有描述自己爱情遇挫后痛苦心情的。其对于藏族人民来说,仓央嘉措是至高无上的神,但对于我们来说,他却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情郎”。仓央嘉措诗歌的汉译者之一曾缄在其《仓央嘉措略传》中有言:“所言多男女之私……流水落花,美人香草,情辞恻丽,余韵欲流。”追求和拥有爱情总是美好的,诚如诗人笔下的情诗,描写着一个心爱的姑娘,点缀着全诗的明艳色彩,如仓央嘉措《那一世》: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一天、一月、一年、一世”时间在流转,但不变的是诗人对心爱姑娘的追求与爱恋。“不为……,只为……”的句式凸显出美丽的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唯一性,其它的权力、职责已经成为外在,重要的是爱情的追求。与此同时,诗中表达的美丽的爱情也传递出诗人的欢快心情与不畏艰难险阻的勇气,读者从全诗中感受到的也是满满的幸福与憧憬,从而直接影响了仓央嘉措诗歌中真切明艳的表现特征。
仓央嘉措隶属于格鲁派。格鲁的意思是善律或善规,因该派倡导僧人严守戒律而得名。格鲁派对僧徒有严格规定,僧人必须受戒,终身不娶,清净禅院,不营事务。很显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残酷的,作为雪海草原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情爱是被禁止的。由此也注定了诗人的爱情将是命途多舛的,这也使得他的诗歌风格由充满希望的明艳风格向希望终将破灭的哀婉风格发展。如仓央嘉措《不负如来不负卿》: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诗歌中的“双全法”三个字将诗人的矛盾心理跃然纸上,一边是自己的职责,传播佛法;一边是自己的情感,心爱的姑娘。诗人的性格和命运终将使他在矛盾的旋涡中不可自拔。而诗歌也不似初期追求和拥有爱情的美好,而是在矛盾中走向哀怨。可以说,这既是诗人情感破灭的既定命运,也是诗歌走向哀婉风格的直接原因。
得失我幸、失之我命的爱情是普通人的自由,但对于仓央嘉措来说,成了最大的奢侈,这样一个内心住着浪漫多情才子的活佛注定是悲哀的。随着爱情希望的一点点破灭,明艳的爱情诗歌也最终显示出哀婉的、内蕴复杂而矛盾的诗歌风格。
综上,不论是客观上的现实社会政治因素,还是主观上的个人气质性格因素、情感因素等,共同成就了仓央嘉措诗作“哀感顽艳”风格的形成。
作为最富才情的诗人文心,仓央嘉措将无法诉说的凄凉与悲愤诉诸于笔端,成就一篇篇顽艳、哀怨、悲慨的风格的诗歌。曾缄对仓央嘉措诗歌有如此评价:“于大雪中高吟一曲,将使万里寒光,融为暖气,芳菲灵异,诚有动魄惊心者。”卢冀野更是将之与后主、道君并称:“南唐后主,北宋道君,得仓央嘉措而三矣。”仓央嘉措作为雪域最高的王,他本身是淡泊离世的性子;面对着现实宗教的束缚,也敢于忠于自己的内心;政治上的失职者又怎知不是情感的诚实者;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他又是那个忧国忧民的仓央嘉措。就是这样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诗人美好的希望一点一点被侵蚀,最终隐没在了悠悠万世的历史长河之中。
同一时期,在西藏上层文人间流传的多是追求典雅,喜用藻饰堆砌,趋向华丽、繁褥,追求唯美主义的诗风。况周颐在评明代屈大均《道援堂词》:“词中哀感顽艳,哀艳者往往有之,独顽以感人,则绝罕觏。道援斯作,沉痛之至,一出以繁艳之音,读之使人涕泗涟洳而不忍释手,此盖真能感人者矣。”故哀感顽艳之作往往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也为诗中不易达到之境。而仓央嘉措开创的“哀感顽艳”诗风,一扫作家诗坛的艳丽浮华。这是他对藏族诗歌风格的一大突破和贡献,推动了藏族民歌的发展和繁荣,在传统的藏族经院晦涩难懂占主导地位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