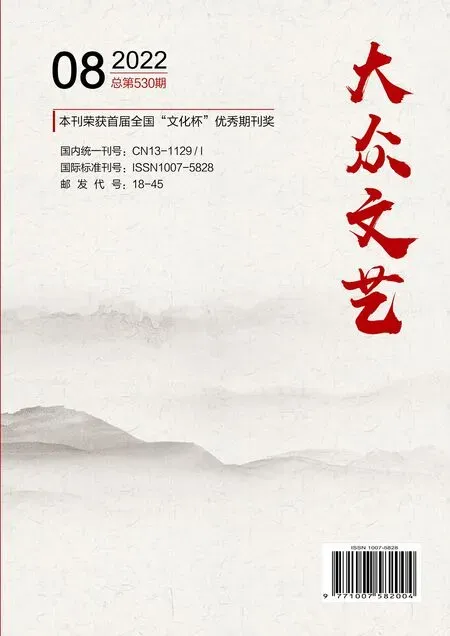故乡已故
(重庆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401331)
一
我不记得我是从多久开始梦见故乡的,像放默片,重叠、交错、缠绕。
可梦境中的故乡,却又是那么的朦胧,像是在拂晓的江边看初日在水雾中缓缓升起,还带着昏昏的晕。可细细品察,却又一日一日地模糊、残缺、消失了。
……
我踏上了回乡的最后一班车,人潮涌动,烟尘漫卷。
十五年前离开江镇的景象还历历在目。父母在车站送我,眼中闪着光,不只是欣喜还是伤心。当时坐在车上,想象未来的景象,不禁从位置上跳起来,周围的人诧异地看着我,像是看一个疯子。
从市区到江镇要两个小时,已近黄昏了。车自顾自开着,陌生的市区渐渐远离,周遭开始熟悉。慢慢稀疏的高矮楼房,忽远忽近的小山,以及一望无际的农田与荒野。太阳抓住地平线散布最后一缕光晖。不知过了多久,车子驶入吞吃人的黑暗,渐起灯光,透过窗玻璃撞击我的瞳孔,一切都熟悉起来。
二
回来的第二天是同学会。
饭店门口稀稀疏疏站着些人。阔别多年,我竟难以将眼前众人的面孔与记忆中故旧的样貌联系起来。
马路上驶来一辆宝马车,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在人群中看见了我,和我打着招呼。我一时间想不起来是谁。他又从后面扶出一位孕妇,我身边一片哗然。
“那不是赵川和肖竹吗?”
“这么些日子没见,这俩人日子过得真好。”
“可不是吗!”
只见那两人向我走来,赵川咧嘴笑了:“江远,你不会真不认识我了吧?”一听声音,的确熟悉,果真是赵川。
赵川是我中学时拜把子的兄弟,一起干过不少坏事,也一起许诺要考复旦。我深知他那哈姆雷特式的性格,没隔几天就看上了班花——肖竹。如今女人倒是追到了,可上海还是没去成。
酒席宴上,众人推杯交盏,已经做了妈妈的女同学们忙聊着养孩子的辛苦,互吐苦水。还有的呢,又抱怨着丈夫或婆婆是有多么的不好,当年真是瞎了眼之类的话。那些体型越发庞大的男同学们,则抱怨着股市下跌、房价上涨。我把目光投向赵川,他正向别人夸耀自己的房地产生意,自己是多么有远见云云。
我开口问赵川:“老赵,当年你他娘的说要考复旦,怎么还窝在这儿呢!”
赵川没料到我会问他这个,露出奇怪的表情,其他人也纷纷转过头来,闭口不语。“唉,这当年不是没考上吗?”
“没考上就来不成?”
“不去上海又怎样?你看你现在又混成什么样?还不如我在老家,娶妻生子,何必去那里呢?物价又高,压力又大!”赵川有些恼怒了,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就低头吃菜,一夜无话。
回到家后,靠在卧室窗边,看着窗外漫不经心的江水和惨淡的月色。我仍记得那年毕业,赵川喝了很多酒,坐在台阶上指着我说:江远,兄弟不义,没有考上复旦,你就自己去吧!不过,将来,将来你哥们我一定会来的,你给我记住了啊!”现在想来,估计是酒后胡话。
原来废墟不在别处,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三
母亲把我的窗帘拉开,强光把我弄醒。母亲对我说:“你爸让你去祖屋看看。”
从家到祖屋要走过重重叠叠的乡道,十几年没来,这里到还是没变。一路跌跌撞撞来到老屋前,屋子长久没人打扫,门上也长了蛛网。轻推开门,屋里一切陈设都和曾祖母去世前无异,只是这些器物上多少有些灰尘。
坐在一把红木椅上,看着窗外几株黄角兰树,自得其乐地开枝散叶。
曾祖母独爱黄角兰。
我的童年是在曾祖母怀抱中度过,每至夏日,睡前时曾祖母总会摘下几朵新鲜的黄角兰,放在我的床头。窗上洒满白月的当儿,我在幽香中沉沉睡去。
曾祖母去世那天,我在上海,母亲来短信。我只记得那田间大笑的老妇人是她,健康少病的老太太是她,慈祥可爱的曾祖母是她。我不敢想象那个瘦小的老妇人,浑身插满管子,孱孱弱弱满嘴胡话,然后撒手而去。
泪把我弄醒,太阳快落山了,屋里也暗趸趸的。我兀自站在曾祖母经常站立的位置,想起了很多事。
母亲跟我说,曾祖母去后,家里的亲戚为争祖产不惜闹翻,渐生怨怼。父亲不愿参与,抱着曾祖母的遗像拂袖而去。如今,这个曾经挤满人的屋子,已经许久没有再升起炊烟。
四
受父亲的影响,我爱听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粤语歌,独衷那语调中金戈铁马之音,仿佛自带着一种江湖肃杀之气。
我生于香港文艺片最后的黄金时代,尔后步入新世纪,逐渐没落。我仍记得,1994年父亲带着母亲和我走进影院,母亲倚在父亲肩头,看着银幕中张曼玉倚窗而叹:“我一直以为我赢了,才发现,其实我输了。”当年不懂,只觉得这红袍女人真美。
此次回家,父亲不只从哪里买来一台95年的电视机,还有一架放在杂物堆里多年的DVD机。
父亲说,这是他的黄金时代,不愿走出来。
五
宫二与叶问的最后一次相见仿佛遗梦一场。在大南,宫二对叶问说:“这些年,我们都是他乡之人。”大感动。
上海的朋友听我讲起故乡,脸上满是惊艳,羡慕我:“你真幸福,到底还有个倚靠。”
的确,故乡于他们只剩下一片被城市包围的废墟,和一个虚幻的名词。幼时的他们跟着父辈几度辗转,开疆扩土,如今系住他们的只剩回忆。
难道我们并非如此吗?
乡愿,一直流淌在人类的血液中。中国人喜欢将情感寄予一个实体,而非虚幻得有些不可靠的记忆。于是,故乡变成了承载着无数人回忆的媒介,丰富我们的情感维度。仿佛我们有了故乡,就不再是水上浮萍,空中飞鸟。
我是有故乡的。十多年来,我的故乡从未有过变迁与荒芜。但即或如此,拴住我的仍是记忆。
曾经爱过的人,发过的疯,流过的泪,做过的蠢事都已像山间的汩汩流水,流向记忆深处。
你说,你何必纠结于过去呢?人总是会变的。
是的,我承认,那么既然人要变,故乡怎么就不变呢?万物皆流,孰能例外?
曾经愤世嫉俗心有大志的同学们早已一一向世俗妥协;曾经和睦的亲戚,如今却纷纷视如仇寇;父亲曾经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曾经。
所以,不是别的,是记忆。将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连接,使我经历时间而不分裂,仍可统一。
所以难免要得出结论,故乡已故,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记忆。
“当初的欲望,已成回忆。”卡尔维诺如是说。
尾声
夜里的江镇依旧热闹。
被日光晒掉漆的车站牌反射着不远处的灯光;路边的老妇人拿着一个口袋,将路上的易拉罐一个一个踩扁丢进袋中;前边的霓虹灯闪着,有几个不亮了,让人以为是“下拉OK”;骑摩托的青年不知死活地奔驰,扬起一路风尘;临街露台上站着一对夫妻,女的凭栏远眺,男的低头抽烟。
“从前的游子一直没有还乡,他被渔火与时光拖住,一生漂流在外。”
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类的命运,从巴别塔崩开始,从我们开始在意时间开始,我们便开始流浪。
宇宙精心地安排这个有始无终的骗局,这个世界就像是场交响乐。
交响乐是个阴谋。
希腊众神看着尘世间不断流浪的人们,可在诸神之上,自有命运,在冷笑。
你说你不信命运。
但是,真的没有命运吗?
无知的人类,自以为在这份剧目中找到了依靠,自以为看穿命运,可是命运早已精心摆布好这一切,它栖于高处,看着在这场荒诞剧目中的无知之人。
我是三天后离开江镇的,一路打点着我的匆匆回忆,往事从我身上一点一点脱落,悄无声息,向空中散去。
或许从来就没有回乡的车,我们也不过行色匆匆各自奔赴下一站。
故乡已故,我们又何尝还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