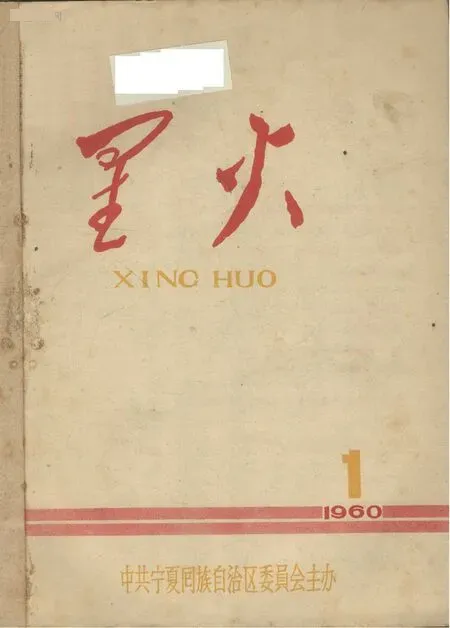隐于辽阔中的呼伦贝尔
○艾平
在旅游盛行的当下,呼伦贝尔已经成为一个热词。再加上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推波助澜,我的家乡已然路人皆知了。
出租车或者滴滴,犹如偌大中国一个民间视窗,我因好奇,经常地触屏一下。在上海,在北京,上了车,和司机师傅近在咫尺,往往要相处一半个小时,不管现场是默片,还是泡沫剧,我总是积极地与司机聊天。每每聊起呼伦贝尔,现场的互动立马升温。司机要么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去过呼伦贝尔,要么告诉我他十分想去呼伦贝尔看草原,更多的是向我倾吐关于草原的种种赞美和种种好奇。我呢,到底掩不住文人的底色,一发而不可收地开讲,直讲到下车,仍然意犹未尽。我甚至鼓动起来一个说走就走的自驾游团队。这几个北京青年,走到大兴安岭山脉脚下的阿尔山,突然给我打电话,接下来一路让我做电话导游。他们先穿越美不胜收的樟子松林地,饮饱一肚子甘泉般的空气,然后继续前行,进入草原腹地,染一身绿野长风。这时,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问过我的问题—草原辽阔无边,一个平坦就是几百平方公里,四野茫茫,不一样的风景在哪里?
呼伦贝尔市位于中国版图最北部,大兴安岭山脉从西南到东北纵贯这片土地,长达七百公里,岭西北是茫茫十万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岭东南连接东北三江平原。大兴安岭山脉逶迤起伏,十二点六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两万平方公里湿地、五百多个湖泊、三千多条河流,散布在山里山外,是北中国最大的生态系统。呼伦贝尔居住着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保持着传统的民俗民风,独具文化特色。亘古以来,这里山林碧透,大地葱茏,素有“绿色净土”“北国碧玉”美称。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演兵练武,然后走出草原,登上人类历史大舞台,因此呼伦贝尔被翦伯赞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后院。
匆匆到此一游的人们,只能看到草原博大的苍穹,看不到风景的细节和深度,看不到天人合一的默契;只能看到地上的马群和天上的白云,看不见大地的呼吸、岁月的足印。事实上,草原茫茫,却不可以用千篇一律来注解。而我,那个在草原上奔走了一辈子的呼伦贝尔人,那个把生命的每一分钟都用于热爱草原的作家,很想告诉你一个隐于辽阔中的呼伦贝尔。当然,对于博大精深的呼伦贝尔,我所说的只能是一些个人经历。
哈吉苏木
苏木为蒙语的音译,是乡镇的意思。在呼伦贝尔地标性景观—百折千回的莫日格勒河两岸的哈吉苏木草原上,居住着通古斯鄂温克牧民。“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民族自称,其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地区的鄂温克人被分别称为“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 ”。 “通古斯”,是指居住在哈吉苏木和锡尼河附近的鄂温克人。他们是来自贝加尔湖畔的古老游牧民族,迁徙到呼伦贝尔已经一百多年了。
夏末,我自驾独行,从海拉尔出发,沿着海拉尔—额尔古纳高速一路向北,过哈达图收费站,下高速向东走草原小公路,行驶不足十公里,到达鄂温克民族乡—哈吉苏木。
远远地就看到了模仿鄂温克族帽子造型建设的民族博物馆,这是一定要像读一本书那样参观的所在。你在此可以走进通古斯鄂温克人的悠久历史,也可以欣赏其鲜活的现实生活展示,你对一个古老民族的了解和敬重,将从这里开始。
我走出博物馆,在苏木政府门前的水泥路上遇到了一个牧马人。他的马群大约有三十多匹,由一匹鬃毛飞扬的儿马子带领着,正在水泥公路上旁若无人地海逛。马蹄原本与有弹性的草地相配,即使上了铁马掌,也不适合在坚硬的水泥路奔跑。随着牧区的城镇化,如今的马儿似乎有了些进化,那纷纭的马蹄声在水泥路上哒哒响着,像是给周边的汽车轮子伴奏。牧马人似乎和他的马群没啥关系,离得挺远。马群任性地徜徉,年轻的母马们不时尥个蹶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寂寞?或者兴奋?小马驹都快一岁了,还紧紧跟着母亲吃奶。路旁正营业的面食店门前有阴影,为了避开针一样尖利的阳光,马很快在那儿扎了堆儿,把面食店的门窗堵住。牧马人一身西装,只有脚上的马靴提醒着他的身份。他朝我一笑,咖啡色的脸上牙齿显得很白,眼仁以外的部分也很白,让我想起巴维尔或者肖洛霍夫的小说。在我上汽车系安全带的工夫,牧马人上了马背,骣骑,没有鞴鞍子。逆光中,我看着他和马群的剪影飞起来了,背景是远天和无垠的大地,脚下是柔软潮湿的草原,那浓黄色的蒲公英花儿,在马蹄下倒了又立起来,竟如一片繁星闪耀。汽车不准下道碾压草场,我停车,目送马群。
出了苏木小村,每一个游客都会去的地方,是著名的阿达盖冰泉。一泓泉水事先不露声色,突然在绿色的花草脚下溢出,直到那翡翠一样的涓流,显现在几十米外的马路边缘,你才会发现它的存在。真真是润物细无声。我摸一下泉流浸润过的泥土,很凉,原来那些花草一直在冰冷的水里长着。我想生就这泉水的大地深处,应该有一个恒久的冻土层,只因为大地缝隙导入的一丝阳光,她便如醉如痴地融化了自己。即使到了冬天,阿达盖冰泉依然汩汩涌流,用冰冷的热度推开满地的冰雪,给这片草原母亲般的恩赐。骄阳如火的此时,人们远道寻觅而来,一杯阿达盖的泉水下肚,自会得到冰冷的慰藉,水中丰富的矿物质簌簌地在血管里流动,人们满身的燥热随汗溢出,冰凉感也一并消失,不会在体内淤积。
阿达盖冰泉,是哈吉人的珍爱,也是哈吉人接待客人的一种礼仪。我身旁,一个皮肤白嫩的鄂温克姑娘,拿着一个玻璃瓶,正弯腰给她的客人接水,她玫红色的袍子铺在绿草上,长发垂在水面上抖动,时而收回被泉水冰麻的手,不停往自己脸上拍着水珠,手上的水珠散落,在阳光中染上金色,仿佛一幅“冰泉冷涩洗凝脂”的画儿……
我接了一桶阿达盖冰泉水上车,选择从东南小路离开哈吉苏木小镇,过阿尔山嘎查,返回海拉尔。嘎查是蒙语音译,意为牧村。呼伦贝尔草原的牧村,说是一个村,由于草场分割,一家家离得很远,往往是几公里、一二十公里 。
放眼望去,草原就像绿色的丝绒地毯,覆盖在平缓起伏的大地上,唯有那间簇新的红砖房,那座洁白的蒙古包,那排天蓝色的铝合金瓦盖青储饲料库房,那给晚霞镀上金色的羊群、马群,是夺目的景点,仿佛一个童话即将在此开始。
我驶入草场的大门,走进蒙古包,达力玛奶奶正在床上摆扑克牌玩。她见到突如其来的我,只是轻轻一笑。见多识广的鄂温克人,不习惯喜形于色。奶奶今年七十五岁了,身子很硬朗,年轻时骑马放牧,现在每天忙着给放牧的儿子做后勤。她褐红的脸上皱纹密集,一双手却柔软细嫩,是个挤了一辈子牛奶,打理了一辈子肉食,手不闲地忙了一辈子的草原母亲。她乐观开朗,说起草原以外的事情头头是道。她告诉我,蒙古包外是太阳能发电机,还有有线电视的接收器,虽然眼下冰箱里的东西,有时因为电力不足冻不透,但是有了这两样设备,过起日子就不怕什么了。她的大孙子在呼和浩特上学,她经常在视频里和他对话。她说大孙子学的是美术,画的画很好看,拿出手机给我看,满脸都是光彩。我看到蒙古包里锅碗瓢盆擦得铮亮,地上的桶里装满油润润的牛奶,看来正预备做奶食。达力玛奶奶的蒙古包里还有一台旧式手动缝纫机,我看最低也用了小五十年了,给人以古朴沧桑的感觉。鄂温克人在重要的场合,是必须穿民族服装的,现在民俗活动多,文化活动多,人们往往必备几套不同季节的民族服装。其中那些传统的棉袍子、皮袍子,城里新兴的设计室、工作坊做不出来;即使做出来了,也把原本的敦厚做没了,到头来就像舞台上的演出服,好看不好穿。牧民还是喜欢靠奶奶这样的老人指点着,使用这老古董配以手针做的袍子。在蒙古包的西墙前,供奉着一个老寿星,案前香火缭绕,水果飘香。古老的鄂温克原是狩猎民族,走出森林后在草原上游牧,他们信萨满,也信喇嘛教。我问达力玛奶奶为何供着老寿星,她说不是—不是—这是土地爷。她带我走出蒙古包,指着四周的草原告诉我,这是为了求其保佑草原好。我觉得老寿星也好,土地爷也罢,终究是草原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个多民族文化融会贯通,又难免浮躁的时代,达力玛奶奶心中时刻想着草原风调雨顺,水草丰美,苍生永续,恰恰体现了人类最朴实最神圣的精神。
告别了达力玛奶奶,我沿百折千回的莫日格勒河向西。呼伦贝尔草原地势开阔,在平坦中缓慢起伏。草原上的河流,大都发源于大兴安岭,在山间时往往静水深流,走入草原,就变得缓慢迂回,九曲十八弯。远看莫日格勒河,就像缠绕在绿色戏袍上的白水袖,只是比那舞台上的水袖更缠绵柔软,更悠长不息。
记得很多文人名家,曾经不辞辛苦地爬上路边的山坡,全画幅俯瞰莫日格勒河,久久不肯离去。老舍先生称莫日格勒河为“天下第一曲水”,端木蕻良先生把所有的赞美之辞给了莫日格勒—“我走过多少河,没有趟过这样的河;我看过多少水,没有见过这样的水。”
“在碧绿的草茵上面,莫日格勒河宛转萦回地流着……有人说,莫尔格勒就是流水的意思。因为它简直是九转回肠,百结相思,水路纠曲,辗转翻折,这段儿向东流,那段儿向西流,这段儿向南流,那段儿又向北流。
“有人说,莫日格勒就是聪明河的意思,因为这条水,含情脉脉,顾盼生辉,流动着一副伶俐巧慧的眼波的缘故。
“也有人说,莫日格勒是交结的意思,因为它曲曲弯弯,缠绵不断互相纠结的缘故。
“莫日格勒河没有多宽,窄窄的像一幅绦带,尽是任情折转,成为全国第一条曲水。历来人们都艳称兰亭曲水,但是兰亭的曲水怎么能比得上莫日格勒河的百转千回!”
二〇一四年,我陪蒋子龙先生来到这里看莫日格勒河,他站在河畔的山上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此后说起来这条河,总是赞叹不已。
前面是莫日格勒河的浅滩,河中的鹅卵石清晰可见。草原上的河流全靠大自然的掌控,有时丰沛,有时干涸,有深流,也有散漫。今年雨水好,浅处河水齐马蹄子。我想过河摘些野韭菜花,回去制作吃羊肉的配料。把车停在河边,等着在河中纳凉的马哥们儿让路,谁知它们一匹匹没事儿人似的,尾巴甩来甩去,扬起水花给身体驱热,也轰赶蚊虫,悠然自得得很。我只好轻轻一按喇叭。它们听懂了,让开几步,回头看看我,又停下了脚步。我前行几米,再按喇叭,它们又温和地让开几步。我就这样一点点地趟过了河。
只有草原人知道,其实马很少躁动,就像草原一样原本是安详不慌的,人们乐于欣赏的是它们生命中最痛苦的壮烈。
莫日格勒河绵延三百余公里,只有向上回溯,越过喧哗的旅游景点,直至静谧的阿尔山嘎查附近,河流的真颜才会渐渐为你打开,草原的非凡才会纷纷涌来。这是隐于辽阔中的风景,也是旷世犹存的地理记忆。
莫日格勒河两岸美到让人落泪—此刻,那水墨线一般抒情的远山,那母体一般温柔的原野,那嫁女一般不愿离去的回环碧水,那绝尘透明的蓝天,全然静默,构成巨大的绝尘之境。我开车不便拍照,又想到,即使拍了,恐怕也拍不出这里隐秘般的气韵,反而将这美的一切扁平化……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到呼伦贝尔首府海拉尔,选一位好司机,按我提供的道路行走,就能看到我笔下的哈吉苏木和莫日格勒河。如果你怀有热爱,草原将永远在你心中。
汗马一夜
大兴安岭山脉北段的七百公里,从西南向东北纵贯呼伦贝尔,是国家巨大的泰加林宝库。一九五一年春天,为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国家邀请苏联工程学院专家和中国林业工作者一起,对大兴安岭林区进行了一次秘密考察,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以后,开始了对大兴安岭森林长达五十年的采伐。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相关部门接受了苏联专家苏晓夫的建议,将位于大兴安岭山脊汗马段的十万余公顷原始森林原样保留了下来。如此,等于为全球亚寒带留下了一份亘古的标本,也让我们在尘嚣滚滚的工业时代,有机会走进一片绝尘的生态秘境。历史上,除了鄂温克猎人和他们饲养的驯鹿群,没有谁曾经在这片原生态林地腐殖层上走过;除了野生飞禽走兽鸣叫,没有别的声音划破过这里的宁静。如果我们看卫星视频,就会发现,汗马自然保护区的形状就像一片树叶,搭在大兴安岭高高的脊背上,而无数的小溪河流湖泊,就像是细若柔丝的叶脉和点点滴滴的露珠,在叶片上轻轻抖动。
一件来自汗马的雄性黑嘴松鸡标本让我眼前一亮。
这大自然的造物实在漂亮。它通身的颜色近似于斑斓的山野,颈羽、脊羽由黑渐蓝再变成绸缎般的绿,翅膀突兀地呈现出两片浓重的琥珀色,在身体的最后端,是黑色带白斑点的尾羽。森林峰固定的食物,滋养了它通身丰厚的羽毛,使之油光铮亮。雄性黑嘴松鸡眼眶上那两抹极鲜亮的大红,将它的双眸衬托得十分明亮,使这大鸟显得精神抖擞,器宇轩昂。这个标本保持着引颈高歌的姿势,嗉囊凸起,置喙大张,尾羽展开到极致;仿佛仍然置身林间的求偶场,好像头顶的松枝上还有目光,那些非王子不嫁的雌松鸡还在注视着它,于是它不惜殚精竭虑,为了赢得爱情一刻不停地叫着……
朋友告诉我,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汗马自然保护区还可以见到这种黑嘴松鸡。我立马萌生了去看看的念头。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上午,我带领《骏马》编辑部编辑王冬海、乌琼和根河市文联主席张红梅、摄影家双柱沿着塔利亚河艰难前行。一路上,寒冷正在和春天的阳光较劲,白天酥软融化,被车辆压成各种凹凸不平,晚上凹凸不平结成冰,上午的道路就成了坎坷起伏的冰场。老司机包虎只能不停扭动方向盘,半踩着刹车前行。山路险峻,塔利亚河一会儿在山崖下奔流,一会儿又出现我们汽车轮子旁边;一会像瀑布一样出现在正前方,一会儿又消失在密林的深处。走得慢,我们得以欣赏了这条多姿多变的河流。塔利亚河是汗马水系的主脉,一路吸纳了十五条小河,奔向山下。蓝天碧透,白桦在天际摇曳,河床里堆满了倒木,给落叶和倒木染成红茶色的河水波浪跌宕,推动白玉般晶莹的大冰块互相冲撞,把个安静的世界弄得有声有色,让人感觉在列维坦的画境里漫游。
走进汗马,地上的腐殖层柔软丰厚,散发着芳香和潮湿,千年的松树、纤细的白桦、矮小的老头树、枯死的站杆、倒下的朽木、丝绒般的苔藓、奇异的云芝山菌、缭乱的灌木、无数草本植物,交织成一个庇护万物的博大母体。汗马有两百九十三种动物,没有谁是主人,只有生物链。比如一只松鸡,它吃虫卵,吃小昆虫,吃桦树芽,吃松树芽,最后可能被大金雕吃掉,化为泥土,去养育虫卵和树种籽,周而复始地永生。然而对于每一个动物来说,活下去是唯一的信念,保留基因是其本能的行动。
黑嘴松鸡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是汗马的明星物种。平日里它们栖息在密林中,每年的四月末五月初,到固定的林间空地相聚,开始求偶交配,其场面轰轰烈烈,像一场壮丽的歌舞剧。主角当然是漂亮的雄松鸡,它们凌晨就开始了几乎不间歇的鸣叫,还打开尾羽和双翅,低飞曼舞,旋转奔跑,极尽作秀示威晒翅膀之能事,只为招徕期待已久的爱情。一只只雌松鸡,千呼万唤始出来,来了也不露声色,蹲在松树枝上不动,像一个员外家的千金小姐,在楼台上久久观望着,存心要把手中的绣球攥出水来。直到雄松鸡们的演出达到淋漓尽致,鲜衣怒马的王子脱颖而出,雌松鸡才梨花带雨般凑到这只雄松鸡跟前,开始娇羞亲热。而那些稍逊风骚的雄松鸡,并不懂什么叫抽身退步早,它们试图横刀夺爱,气昂昂走到母松鸡的旁边作勾引状,显得暧昧又鲁莽。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子冲冠一怒为红颜,不惜与同类大打出手。由于荷尔蒙的驱动,雄性松鸡之间的搏斗惨烈无情,最卓越者,往往在羽毛散乱、眼睑撕裂之后妻妾成群;失败者们落得个灰头土脸,站在一旁傻看胜利者的鱼水之欢,并不知道自己失去了绵延子孙的权力。
据说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一幕—女人们生了孩子,必须经氏族长老们验收,身体发育不佳者,随手抛入大水池浸死。这残酷的习俗,看起来惨不忍睹,却也是对基因进化的一种贡献。生命延续是百代千年的大道,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不可以简单地使用恻隐之心。
到达当天的下午,汗马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主任李晔,陪我们步行参观保护区境内的塔里亚河。李晔不仅通地理,通动植物,更善于将实践经验与先进理念融会贯通,堪称汗马达人。我信手从地上掠来点什么,他立即就能说出此物的学名和用途。诸如塔藓的种类、杜香的药用、木耳和石耳的不同等等,如数家珍,头头是道;路上看到几堆动物粪便,他马上就能告诉我,哪个是紫貂的,哪个是狍子的;遇到一堆散乱的羽毛,他一看就辨认出来了,那是被猞猁吃掉的花尾榛鸡的残骸。他一路向我们传达他的生态保护观念,即除了防火、防盗伐、防盗猎,不要干预大自然,任其保持原始状态就是最好的管护。他非常高兴的事情是,自己使用红外线照相机,拍到了驼鹿群的活动,其中一个镜头里闯进六只驼鹿,显然那是一个幸福的家族,个个营养充足,毛皮油亮…… 说起黑嘴松鸡,李晔也是了如指掌,他说明天早上两点出发,让我们去看松鸡求偶。
夜里,我们一行五人集中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大家和衣而卧,等待凌晨。汗马的地理位置接近北纬五十二度,虽然已近五月,到了夜晚,还是非常冷的。铁炉子里烧着木柈子,散发着温暖,也散发着松油的芳香。已经奔波了一天的三男两女五个伙伴,倒头便发出鼾声。我激动得久久不能入梦,辗转反侧间,发现室内亮如白昼,身边同伴们的睡容清晰可见。原来光亮来自窗外,我想应是管护站不熄的院灯。
我悄悄走出房间。哪有什么灯火,染我一身的原来是千古的星光!这真是—星光如水水如天,一朝都到眼前来!汗马的星空,我该怎样形容你?像巨大的王冠镶嵌着数不清的宝石?像一袭天鹅绒长裙缀满明润的珍珠?像开阔的舞台上闪烁着密密匝匝大大小小的灯光?不对,全都不对。汗马的星空不仅璀璨,还是活生生的、有温度的、熙熙攘攘的、扑朔迷离的。仰望之时,我感觉到那繁星密布的银河,那些光彩夺目的巨星,那勺子一样排列着的北斗七星,就像明亮的雨滴,在徐徐坠落,时刻扑面而来,一点点地逼近我,却又永不相许。
我的眼睛慢慢湿润了。我决定不再睡觉,就坐在外面看星星。
凌晨两点,我们穿上最厚的衣服上车出发。我们的汽车遇到了两只横穿马路的小驼鹿。据我们后来的描述,李晔认定这两只小驼鹿大约在一岁半左右。见到车灯,一只小驼鹿立马消遁于路基下的密林,另一只小驼鹿像静物那样立在雪亮的车灯光线里,支楞着耳朵,瞪着眼睛看我们,让我们看了个清清楚楚。它头顶上长出了小小的鹿茸,脊背的驼峰浑圆凸起,浑身的毛皮金黄油亮,正如一个朝气蓬勃的英俊少年。片刻,它似乎听到了某种召唤,满血复活一般,转身跳下路基,不见了。它的母亲应该就在附近。
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的车停靠在窄窄的砂石路上。一位工作人员打开手电,引领我们走入漆黑的森林。气温在零度左右,脚下的路坚硬又泥泞,还横七竖八地倒着朽木,无数灌木之手,从前后左右拦扯我们的衣服,人们接二连三地陷入泥水,不停地趔趄、摔跟头。不过谁也顾不上满身的泥泞了,因为那雄松鸡“梆、梆、梆……”的求偶叫声,像石头雨一样,很立体地笼罩着森林,没有间歇,紧锣密鼓,一声比一声急迫地催促着我们。我们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再加快。
由于在黑暗中走得艰难,我们在林地里走了不到一公里,感觉像走了很远。当工作人员放低了嗓子:“别说话,快进去!”我们才发现自己眼前有顶迷你帐篷。帐篷很轻,工作人员轻轻一举,便把我和王冬海、乌琼扣在了里面。接着,他又把红梅和双柱扣在了对面的另一顶帐篷里,踩着落叶簌簌地远去了。
看看手机,凌晨两点半,距离松鸡求偶结束还有四个半小时。在这四个半小时中,雄松鸡随时可能开始跳舞,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守候观察。我们蜷坐着,不敢说话,只是从四个小窗口向帐篷外看。林间的空场,依然有树木,只是稍微稀疏一些。明亮的星空被一株株树遮挡无余,到处一片漆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梆、梆、梆”的叫声越来越响。我们三人把眼睛看到酸疼,突然从窗口发现三米距离处有个黑影,果然是一只高大健硕的雄松鸡!我们挤在一个窗口,屏神静气,死盯着它,只盼着它开始舞蹈,让我们留下几张照片和一段珍贵记忆。可是这只松鸡既没有跳舞也没有唱歌,也不展开翅膀,就那么直立着,偶尔踱几步,真不知道它在想什么。
我们的动静,似乎没有惊动松鸡,它离我们如此之近,一动不动地站立了起码十分钟,接着以散步的节奏从我们眼皮底下走过,慢慢隐入夜色。回来后我查了资料,证明我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松鸡的警觉。松鸡平时对风和各种声音很敏感,只是在发情期有些痴呆,求偶时它叫起来会失聪,不叫时也不如平常机敏。
黎明,当天亮到能看清周围的环境时,我们已经快要冻僵了。帐篷矮,地面像冰面一样拔凉,我们不能站直身体,只好不断地在坐和跪两种姿势间转换。这时我们搞清楚了,“梆、梆、梆……”的石头雨,来自四只雄性松鸡,包括刚才躲开我们的那一只。它们各自开辟一块地盘,拼命呼唤着爱情。它们原地转圈的身影,一会儿被树干遮掩,一会儿又出现在树的缝隙间。透过相机镜头可以看到,它们鸣叫时置喙一直不闭合,全靠喉结的振动发出声音。它们足足叫了四个小时,一鼓作气,没有间歇,让我们这些观察者捱得又冷又饿又困又焦躁。
根据事先的功课,松鸡在发情期,是每天都要交配的。雌松鸡一直没有露面,什么原因?
晨曦出现在东方,随后天下大白。看看表,六点半了,就是说如果在七点之前没有雌松鸡出现,我们的汗马之行,将抱憾而归 。
我们把头探出小窗户,环视四只雄松鸡,观察它们头上的树枝以及跟前的林地,确认没有雌松鸡在场。对面帐篷里的红梅用目光问我们,我一招手,大家举起帐篷,走了出来。恰恰就在此刻,我一眼看到一只雄松鸡头顶的树枝上,落下来一只娇小的雌松鸡。雌松鸡看上去和雄松鸡简直不像一个物种,它羽毛如暗淡的秋色,身子小于雄松鸡很多,头颅像没有鸡冠的家鸡,毫无姿色可言。朴素的雌松鸡走向雄松鸡,欲投怀入抱。我们赶紧重新钻进帐篷,准备静观以下的情节,可惜由于我们一时动作慌乱,引起了这对松鸡的警觉。只见雄松鸡迟疑了片刻,亮了一下美丽的翅膀低低地飞走了,随后雌松鸡向另一个方向飞去。其他三只雄松鸡果然痴呆,还在“梆、梆、梆……”
我们分析,飞走的那一只松鸡,应该就是这里的白马王子,它赢得了异性,美梦却未能成真,而我们正是棒打鸳鸯的罪魁。
我们在做什么?不过是对平等生命的惊扰而已。那春天里的爱情,被我们惊扰之后是否还可以重来? 往深里一想,忽然意识到,为了活下去,动物会在它的基因里悄然积攒经验,而我们的惊扰,在松鸡梦魇般的记忆里,将成为抹不去的阴影。如果人类最终成为它们生命本能中的敌人,当它的子子孙孙看见我们的时候,其心理状态会像我们的孩子见到了毒蛇、豺狼一样。
在归途中,我们遇见了一只美丽的雪兔。蓝灰色的脊背,雪白的肚皮,身子颀长,生就一对玲珑的大耳朵。不知什么原因,它表现得很友好,老老实实地蹲坐在路边给我们当模特,对闪光灯和快门毫不惧怕,让我们拍了个够,直到摄影家离它已经很近了,它才不慌不忙地一跃而去。
汗马自然保护区距离根河市金河林业局九十公里,目前没有开发商业旅游,科学考察之外的游人,必须在管护站止步。不过,你能在汗马的外围走走,既不打扰汗马的静谧,又可以感受深山腹地的森林气象,偶遇来自于各种飞禽走兽 ,绝不枉无悔之旅。
基于1 660 mm2大截面碳纤维导线的特点,本文取夹嘴长度为350,325,275 mm三个方案,对导线夹紧状态进行了仿真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伊赫乌拉
伊赫乌拉是蒙语,意思是大山。伊赫乌拉是呼伦贝尔草原上一座非常著名的山,由丘陵和巨石组成。在一马平川的绿色大地上,一组丘陵像凝固的波涛伫立,不知何因,不知何时,每一座丘陵的头顶,都生出巨大的岩石。只见那些岩石,有的像一个伸向天空的拳头,有的像一排小马驹脖梗上的鬃毛,有的一面像跪卧的骆驼,另一面又像一只即将起飞的大鸟,有的像欲动的大龟,有的像一本打开的书。巨石矗立,座座顶天立地,一直将丘陵带到了云端。如此,这片圆润的草原,高出了地平线的格局,有了阳刚之气。来过的人们说,草原的风景都是隐藏在平坦里的,方圆几百里,能够让你眺望到的,只有伊赫乌拉的石头马驹脖子。伊赫乌拉是草原的圣洁之地,不是旅游景区,没有围栏,到这里来看山看天,是很方便的。你驱车沿着G301海拉尔—满洲里高速公路向西,走出一百公里左右,进入新巴尔虎左旗境内,当路边出现一个蒙古驿站时,你向南看,就会看见那条直达伊赫乌拉脚下的便道。沿着这条便道驱车约二十分钟,伊赫乌拉就到了。
你走着走着,眼前突然站起个又高又大的人,那就是伊赫乌拉。他的脚扎根在茫茫的草浪里,岩石像他结实的肩膀,上面轮换栖落艳阳和冷月;风中,他器宇轩昂,大气凛然。岩石的最顶端有一座敖包,是虔诚的草原人用周边的石片垒建的。橘红的、宝蓝的、棕黄的、洁白的绸子缭绕在敖包上,和早晨的霞光在一起,变成了五彩祥云;一簇柳枝,插在敖包的石隙中,生出了根,发出了芽,长成了一棵棵柳树。
伊赫乌拉的天,幽蓝剔透,金光灿烂,像蓝蜻蜓翅膀组成的海洋,在太阳下面舞动。鹰飞过来,用翅膀划开天上的云,落在岩石上,开始巡视四野。它的双眸冷若冰霜,它钩状的长喙紧紧闭合着,呈现出青铜造物的气质。它以君临天下的心态,准备获取想要的一切。
婀娜婉转的海拉尔河,在伊赫乌拉的视野里流过。河畔,零散着石板砌成的墓葬,那是一千多年前鲜卑人的遗迹。他们从大兴安岭的密林走出,沿着河水徘徊了一百多年,终于南下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他们面对金戈铁马和烽火硝烟愈战愈勇,到头来却被柔软的农耕文化消融,变成了大海里无法追寻的一滴滴水。
在伊赫乌拉丘陵的阳坡上,可见一处四方形的断壁残垣,虽然历经风雨剥蚀,已经看不出原有的模样,但是轮廓还在,大门的位置还能看出来。它也是鲜卑人的遗迹吗?是一座城堡,还是一座庄园?一切都不得而知,但足以证明,寂静伊赫乌拉,曾经有过人马喧闹的岁月。
草原上的人们认为,登上了伊赫乌拉,你就在天上了,你的目光因此变得很远大,你能从一百里看到二百里,能看到大地升腾,云朵飞落,天地吻合,整个儿苍穹犹如银盆一样浑圆。敬拜了伊赫乌拉的敖包,你的双手就能摸到远来的春风,你的耳朵就可以听到明天的福音。所以人们总是在接完羊羔的六月来,把酒香留在冰茅草的须子上,把长调挂在银丹花的蓓蕾上,然后把喜悦揣在蒙古袍的胸襟里,带到风调雨顺的下一年。
记得十五年前七月的一天,我一个人坐在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岩石上,聆听草原的风声,和自己的心长谈,万没有想到河边的那个牧羊人会向我走来。我就这样结识了孟和沙老哥哥,他的名字含有久远的意思。
牧羊人孟和沙老哥哥说:我的腿不好了,下马容易上马难,只能坐在马背上和您说话,我这是在远方的客人面前失礼了。
孟和沙老哥哥说,一年里除了祭山的那三天,剩下的三百六十二天,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在马背上看天,看鹰,恍然之间就过去了一个人的六十年。
于是,我写下了孟和沙老哥哥和鹰的故事。
“不知哪年哪月的那一天,鹰从巢穴里飞出来,在伊赫乌拉的天上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儿,孟和沙感到套马杆的尖头开始动,像白枕鹤的羽毛那样轻飘飘地晃起来,他知道那是鹰俯冲时的气流。孟和沙将身子仰在鞍鞒上,看见了盘旋在自己头顶的鹰,看见了鹰腹部黄褐色的绒毛,看见了鹰肩胛骨铁色的光泽,还有那一双粗壮的螺旋爪,甚至看见了鹰屁股上灰色的屎渍……眼看那鹰直往下落,孟和沙一个鲤鱼打挺儿站起来,两腿木桩一样立在了马镫上,说话间他手里的套马杆已经甩出一个来回。原来鹰是瞄准了孟和沙身边的那只马驹。小马驹刚刚诞生,身上的羊水还没有干,血腥味吸引了饥饿的鹰。鹰被套马杆一击,立刻像爆炸的烟花一样弹起来,但是那双爪子比闪电还快,瞬间抓走了孟和沙头上的皮帽子。鹰很快发现那顶帽子没有血肉,就把它抛在了云朵上。帽子滚下来,像一只狐狸跌倒在孟和沙的马蹄前。
“孟和沙怒了,他一夹马肚子,就冲上了山顶,随后他的马群也跟着上了山顶。他掏出马鞭子直抽在岩石上,发出哐哐的回声。孟和沙相信鹰巢里的鹰听了之后一定魂飞胆散,那褐红色的眼皮一定会突突地跳。孟和沙是一个放牧过一千匹马的牧马人,那时候他多么年轻。
“当年轻的孟和沙变成了孟和沙大叔的时候,那只鹰也到了中年。一只中年的鹰不再孟浪,虽然它看见牧人的马群已经变成了比棉花还听话的羊群,但是没有忽略牧人手里的套马杆。曾经桀骜不驯的鹰,低下高贵的头。它飞过伊赫乌拉敖包,到远方寻觅银鸥、沙燕和田鼠。鹰把这些美食,垂吊在鹰爪上,高高地从孟和沙老哥哥的头顶飞过。孟和沙老哥哥久久端详鹰在天上飞翔的样子,细细琢磨鹰留在地上的影子。他知道每年都有两三只雏鹰,走出岩缝中的那个家。它们探出小脑袋,像一颗颗松果那样滚出来,或者落在岩石上摔得粉身碎骨,或者像一把伞似的撑开身子,两翅飘摇蹁跹,片刻后猛然高扬而起,从此一去不回头。孟和沙发现,留在伊赫乌拉的鹰是一对悲伤的父母,它们一遍遍地围绕着空巢滑翔,不时发出凄凄的鸣叫。后来,它们忘记了心中的创伤,恢复了以往的坚强。那只雄鹰一如既往,像牧马人般勤奋,每天远飞觅食,它的身姿永远那么硕壮,它的气势永远那么凌厉。或许磨难对于鹰来说,就像蒙古刀淬火那样,让自己更坚硬,更锋利。在孟和沙的心里,满是对鹰的敬意。
“鹰的疆域没有百灵鸟,没有旱獭子,即使霸气十足的狼也不敢轻易露头。马站立在自己的影子上睡着了,伊赫乌拉静极了。孟和沙从鹰巢里隐隐约约听到雏鹰细嫩的叫声,一声声愈发殷切,不由想起蒙古包里开饭时的情景,孩子们急吼吼地要吃肉,要喝茶…… 孟和沙的心变成了柔软的河水。
“羊群里的一只母羊流产了,羊羔在草窠里慢慢风干着。孟和沙抱起渐渐僵冷的小羊羔,摩挲着那柔软的羔皮,想着用这张羔皮做一双马蹄袖,放牧的时候戴在手上……到了牧归的那一刻,他看看伊赫乌拉上面的岩石,看看落日辉煌的草原,便把那只羊羔子从马鞍子上卸了下来,留在鹰的眼皮下……”
十五年间,我到过伊赫乌拉多次,再没有见到孟和沙老哥哥。我久久地仰望天空,有的时候耳边会出现若有若无的长调,那断断续续的歌声,你若集中了心思刻意聆听,反而就消失了。伊赫乌拉这座大山,让我深感人生不过是它脚下那一朵朵转瞬即逝的小花。
一年春天,我带着几位可尊敬的朋友来看孟和沙老哥哥的伊赫乌拉。在最高处朝南的岩石缝中,我们看见一缕缕苔藓样的污渍,那是鹰的粪便。鹰在这里坐窝孵卵,是因为这里险峻又有阳光。岩石南北两面的温差很大,一块面包,在南可以晒干,在北可以雪藏好久。我和朋友面南背靠岩石,果然感到一片温热。我拨开脚下的草丛,让朋友看—一抹嫩嫩的绿,已经在泥土里洇出。
谁说季节还在沉睡?西来的风撒下一把冰冷的钢针,为海拉尔河除了身上的积雪,掀开了盖头,看那河床吧—长长的蓝冰在雪原上闪耀光泽,犹如蓝宝石串起来的项链。向山下走去,我们远远就闻到了河水的气味,听到河底微微的水声。
我在这里找到一朵小花儿。这朵学名叫细裂白头翁的小花,已然凌寒开放!她从雪窠里长出来,体现出一种渺小的优雅。她是那么低矮,几乎是贴在地皮上长着;她是那么素淡,浑身是毛茸茸的灰,只有花蕾上一抹幽幽的蓝。我告诉朋友,这小小的蓝花,是草原春天的第一声呐喊,也是季节赐予牛羊的头道美食。
鹰在岩石上起飞,刚健的双翼从云间滑过。那是孟和沙老哥哥年轻时见过的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