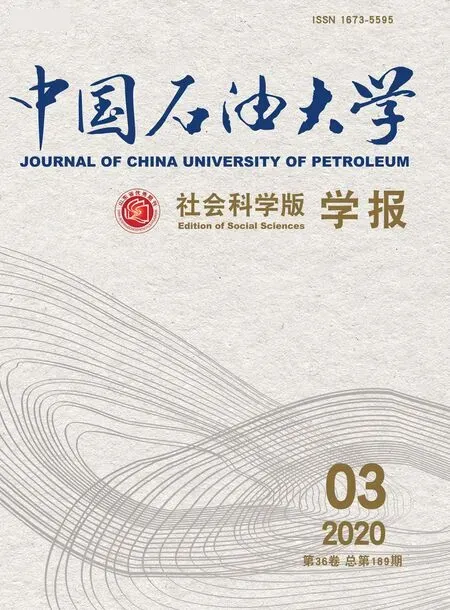宋代杜诗学文献地理分布可视化及成因
黄 一 玫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在唐代颇受冷遇,其受关注的程度远不及同期的李白和稍后的白居易、韩愈等人,唐人所辑唐诗选本中大多不录杜诗即为力证,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未载杜甫诗,姚合《极玄集》也未收杜诗。杜甫生前亦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然而到了宋代,杜甫及其诗歌却寻得诸多“知音”,顺利完成了经典化的历程。仇兆鳌在唐人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后注曰:“樊氏初求遗稿,仅得二百九十篇。经宋人搜辑,渐次集为完编。诸家采录之功,诚不可没。”[1]后世称宋代为杜诗学发展史上“千家注杜”的时代,从不为时人所重到文坛典范,宋代杜诗文献的整理和传播是尊杜风尚历史演进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奠定杜甫“诗圣”地位至关重要的一步。梳理宋代杜诗学文献地理分布的情况,借助QGIS(Quantum GIS)等数据手段将其可视化,通过对图像的阐释,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影响,对考察古代杜诗学的演变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宋代杜诗文献繁荣的原因
与唐朝盛世气象和文化的开放兼容不同,宋代一直以来的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使得文人似乎天生就具有忧国忧民的精神气质,杜甫“致君尧舜”的理想成为宋代文人的共同追求。宋代文人对杜甫的诗歌进行重新注解与阐释,不仅是学习其“沉郁顿挫”的风格,更是对杜甫作品中“忠君”“仁爱”的儒家文化内核加以肯定。宋代的文坛大家都极为推崇杜甫。苏轼评价杜甫:“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2]这不仅指明了文人士子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也成功塑造了杜甫爱国忠君的形象。此外,王安石、杨万里等人皆有集杜诗的作品,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更是以老杜为宗。文坛领袖的喜好往往成为文坛的风向标,引其余文人纷纷附和。周裕楷先生总结道:“宋人取杜甫的忠君思想,在两宋外患频仍的特殊背景下,起到了维系民族文化、挺立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忠节相望,班班可考,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联系到北宋中叶形成的‘学诗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的盛况,便可知道宋诗学弘扬杜诗忠义精神在御侮斗争中的特殊意义。”[3]在强烈的忧患意识氛围下,杜甫不仅仅是在诗歌艺术上兼采数家、众体兼备的“集大成”者,更是宋代文人规范人格操守的楷模,尤其是南宋以来爱国人士的精神支柱。宋人按照自己的理解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重新塑造了杜甫,成功提炼出杜甫身上能引起宋代社会共鸣的精神因素,使得杜甫在宋代得以成功走出冷落,成为集诗人与忠臣于一身的完美形象。
唐代文献流传的主要媒介是写本,而宋代印刷术的升级,则标志着文学结束了手抄,进入了刻本时代。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加之宋仁宗时期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刻书所需的时间和费用都大大减少,效率的提升使得刻本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刻印技术成熟、刻书行业遍布各地,并形成了官府、私家、书坊三个层次的刻本体系。除此之外,造纸业、制墨业和图书销售等相关联产业的发展也为刻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刻书业在北宋中期初步成为一项独立的产业。[4]传播载体的改变对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刻本在印刷的速度和质量上都远胜于写本,雕版一旦刻成可以多次反复利用,降低了书籍的价格,且极大改进了写本讹误多、难保存的缺点,使得文学典籍能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生产、传播和消费。钱存训先生指出:“纸的应用,使得书籍的成本大大降低,并且更易携带。但书籍的大量生产和广泛流通,则有赖于印刷术的发明。”[5]宋人不仅大量印刻当代的别集与总集,也注重对前代文学典籍的整理和刊刻,尤以唐代诗人的作品集为多,“今存传世的隋唐五代别集,如陈子昂、李白、杜甫、韦应物、韩愈……的别集,无不经过宋人的整理刊刻。有的别集,或重编,或校勘,或辑佚补遗,或注释编年,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多次整理,出现了一个兴旺繁荣的局面”[6]。而杜甫作为宋代树立的典范诗人,文坛上下学杜的风气颇盛,读者对相关书籍的需求量必然十分大。据考证,当时优质的杜诗典籍被争相购买,竟为文人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7]文人和书商都从杜甫身上获得了可观的商业利益,在文学商品化浪潮的影响下,杜诗学典籍自然格外受到印刷行业和文化市场的青睐。
二、宋代杜诗文献的地理分布情况
今有学者认为,杜甫在唐代的默默无闻,除了诗坛风尚的影响之外,杜诗流布面狭小、流传数量不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8]这种情况在宋代得到了明显扭转,宋代杜诗文献的大量刊印是宋人宗杜的直接体现,而大量杜诗文献的刻印和传播,又为文人学习杜诗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进一步普及了杜诗,提升了学杜的文化氛围,助推了文学重心的下移,使得更多中、下层文人得以更方便直接地研习杜诗。苏永强曾总结:“以宋刻本在社会的普及传播和接受效果来看,印本文学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显然要高于写本文学。”[9]张忠纲先生等人编写的《杜集叙录》是近年来杜诗目录学、文献学方面的扛鼎之作,在编写时尽可能地网罗了有记载的杜诗学文献,虽未必能全面覆盖,但在版本和作者考证等方面用力颇深,是了解杜诗文献的重要参考;笔者参照书中收录的宋代杜诗学文献数据,就其编者籍贯、地域进行分析统计:书中所辑宋代杜诗学文献共124条,其中阙名者12条,已证实系伪题苏轼、黄庭坚等名家者5条,得到确切可考者共86条,见表1。[10]

表1 宋代杜诗学文献编刻者空间分布表
以表1为数据,通过QGIS可得到清晰明了的空间分布情况,见图1。

图1 宋代杜诗学文献编刻者空间分布图
虽因宋代年代久远且留存下的文献较少,已不能完全恢复“千家注杜”的盛况,但由这尚存的86条数据,依然可以以小窥大,略作探索。表1所罗列的宋代杜诗学文献中的“时代”为编著者生活的时代。从时间上看,第一本《手写杜诗》编纂者王著逝于公元990年,以此推算,他生活的年代大致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而最后一本《注杜诗》的作者吴渭是宋末元初人,曾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创办著名的月泉吟社,二者之间跨越了三百余年。若以南宋、北宋划分,年号“建炎”为南宋起点,则北宋时期的杜诗学文献有30本,南宋时期的杜诗学文献有56种,杜诗学文献在南宋的数量明显多于北宋。其原因不外乎是由“靖康之变”所带来的家国之痛,让有着相似经历的文人墨客在阅读杜诗的过程中更容易从杜甫身上获得精神共鸣,他们也和“安史之乱”时期的杜甫一样渴望明君出现,实现收复中原的愿景。陆游的诗作中就常常有他对杜甫的追思和凭吊,如“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尘到两京。扈跸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11]。南宋诗人作品中最常出现的爱国主题,也正是对杜甫精神内核的弘扬。加上南宋虽在政治上节节败退,但偏安江南后,经济和文化依旧不断发展,从编刻者籍贯在现行行政区划下的空间分布情况可见,宋代的杜诗学文献分布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中原地区除河南外,其余地区都与南方相差较大。
以地域籍贯(省份)为基础对宋代杜诗文献分布进行统计,则可以得到各地区分布的数量,见表2。

表2 宋代杜诗文献地域分布数据表
通过QGIS可直观地了解宋代杜诗学文献的密度分布,见图2。
图2中各省份的填充颜色随着数量的增多而依次加深。由经过渲染的图2可知:从总体上看,宋代杜诗学研究和刻印的主要区域集中在南方地区,86本杜诗文献中,南方地区占71本,北方地区15本;从地域上看,福建、浙江两地遥遥领先,之后便是江西、四川,而北方的15本中,其中有8本在河南。
正如周采泉所言:“从宋代直到近代,每一个时代各有不同的研究风尚:宋代重在辑佚和编年,元明重在选隽解律,清代重在集注批点,近代则重在论述分析。”[12]宋代是离杜甫最近的时代,系统而全面地收录杜甫作品、考订杜甫生平对宋人来说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依据表1中编刻者确定的86本,再加上阙名的12本,若以这98本宋代杜诗学文献为样本进行探讨会发现,宋代杜诗学文献中共有年谱6部,即吕大防《杜工部年谱》、赵子栎《杜工部草堂诗年谱》、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鲁訔《杜工部诗年谱》、吴仁杰《杜子美年谱》、梁权道《杜工部年谱》,宋人擅以唐史为参照考证杜甫生平并为其作品系年,无疑为后世研杜、习杜提供了重要参考,闻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即采纳蔡兴宗《重编杜工部年谱》颇多。而明代的171本杜诗学文献中竟无一本年谱,这一是因为明人更注重对杜诗的理解而非杜甫生平的考证,二是因为明代前、后七子皆推崇复古思潮,他们更注重杜甫作品中格式严整的杜律。

图2 宋代杜诗学文献的地域分布情况
三、宋代杜诗学文献地理分布的成因
北宋原有四大刻书中心,即浙江、四川、福建和汴梁。汴梁作为都城,是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南来北往进京赶考的学子无疑是汴梁图书市场的重要客户。但宋朝政权南渡后,汴梁的刻印从业人员也随之迁至临安,沦陷后的汴梁刻书业从此衰落,而浙江、四川和福建三地却不断壮大和发展,形成了历史上俗称的浙刻、蜀刻和建刻三大刊刻中心。在表1的数据统计中河南的杜诗学文献,北宋占6本,南宋仅有2本,也与河南刻书业在政权南渡后衰落的史实相吻合。浙江、四川和福建三地皆处江南一带,山林植被充足,普遍种植桑、楮等植物,是纸张制造的主要原料,其中福建又盛产竹子,故闽刻本多用竹纸。三地刻书行业就地取材,既减少了制造、运输方面的成本,又缩短了刻印时间,这也是闽刻本数量众多的主要原因。三个地区的刻书业各有侧重,浙江自古是富饶的江南水乡,关于雕版印刷最早的记载要追溯到唐代诗人元稹所言“扬、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13]。北宋时期的首都虽是汴梁,但国子监的书籍大多在杭州刻印,史称“浙刻监本”。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中称:“嗣后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书》,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板。北宋监本刊于杭州者,殆居泰半。”[14]足见当时的浙江刻印技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政权迁都临安后,临安政治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当地商业和文化的繁荣,使得临安以及周边如绍兴、台州等地的刻书业蒸蒸日上。四川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之一,从五代蜀国时期起便有刻印的记载,蜀刻多以大字本印行,史称“宋蜀大字本”,其中又以唐代诗文集最具代表性,除杜甫外,李白、王维等人也有蜀刻集。闽刻以建阳书坊最为盛行,如建安余氏就世代以经营书坊为业。宋代藏书家叶梦得曾评价:“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15]
从表2和图2可以看出,在三大刻书业中心之外的江西,在宋代杜诗学文献中却排在第三,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抚州本就是宋代的造纸中心之一,生产的萆纸十分精贵,清人叶德辉曾云“南宋时则以抚州捭钞纸为有名”[16],加之赵宋政权迁都临安后,原本北方的刻工相继南下,江西境内抚州、吉州的刻书业逐渐发展起来;二是两宋时期的南北交通要道“江州—大庾岭”和东西交通要道“信州—袁州”都经过江西境内,其中“鄱阳湖—赣州”航道是连接南北交通的关键水路,九江驿、浔阳驿是当时重要的交通驿站,水陆交通的发达为书籍的运输提供了便利,从江西印刻、生产的书籍得以以较快的速度运送到各地,也促进了文学的交流与传播。
除了刻印产业发达、交通便利等原因,南方的杜诗学文献繁荣与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样密不可分。宋代以来,江南一带文化发达,读书风气浓厚,人才辈出,洪迈曾说“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17]。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位文人以及黄庭坚、朱熹和陆游等人皆出于江南,即是此地文化昌盛的有力证明。同时,作为地方最高学府的书院,在宋代的浙江、福建、江西和江苏等地比比皆是,不仅培养了许多科举人才,也刻印了大量典籍,如当时十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等都有藏书、刻书的传统,对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人据龚延明、祖慧所编《宋代登科录》统计,两宋时期有记载可考的登科进士,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成都府路的数量最多。[18]这四地即今天的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和四川,也是杜诗学文献分布数量最多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地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文化典籍的需求也越大,加之杜甫在宋代的崇高地位,作为“商品”在文化市场的需求和作为“书籍”在文人阅读中的需求一道刺激了杜诗学文献的刻印数量,是杜诗学在宋代得以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
四、小结
杜甫“诗圣”的至高无上形象在宋代得以确立并影响深远,当代学者在总结宋代杜诗学的三大成因时,将其归结为文献流传、文化转型和文学嬗变。[19]现今学界对后两者的研究用力颇深,已有许多掷地有声的论述,但对文献生产和传播所带来的影响却缺少关注和探讨。唐代的杜诗文献不仅少且单调,仅有14本杜甫诗集流传于世;到了宋代,杜甫的年谱、注本、评本、诗集和各类选本才正式出现,并奠定了元、明、清杜诗文献的基本模式。曾枣庄先生在谈论宋代在杜诗史上的关键地位时也总结道:“杜甫的诗,不仅在他生前不受重视,而且在他死后,在樊晃、元稹、白居易、韩愈高度评价杜诗后,仍不甚被唐人重视。真正普及重视杜诗的是宋代。从北宋中叶到南宋中叶,宋人对杜诗进行了广泛的搜集、研究和整理。”[20]杜甫的名声在宋代一跃超越李白,并从此牢牢占据诗坛至高地位,这其中杜诗文献及其传播所起的作用是研究者无法忽视的,杜诗文献也为考察古代杜诗学发展演变提供了一条鲜明路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文学作品靠了媒体才能在读者中起作用。”[21]文学要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阅读,必须以文本作为载体,不重视媒体这一介质在文学传播中的作用,恐怕难以厘清文学作品和作家被接受过程的脉络。刻本作为宋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传播的主要媒介,大大提高了文学的传播速度,降低了文学传播的成本,并扩展了文学传播的范围,使得更多平民知识分子也能够阅读、研习典籍,是研究杜诗在宋代传播和被接受的重要参考。“‘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文学地图则更倾向于从群体性、全面化的地理数据中去挖掘信息。”[22]笔者依托QGIS等数字人文软件绘制图表来考察宋代杜诗学文献的地理分布,能够清晰直观地展现其分布情况,从传播学和文学地理学的视角为杜诗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