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人物
◎矫寿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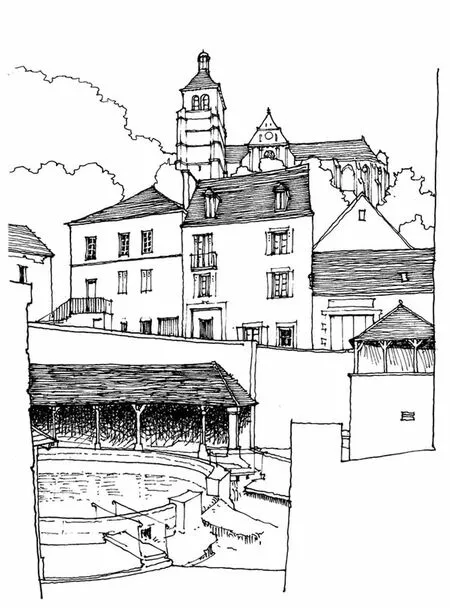
小村不大,满打满算不足二百户人家。可小村风水好,有灵气,竟出了十几位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大到省部级,在这里我不想对他们说三道四,只想唠唠身边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尽管他们在村人心目中占不上多大的份量,却各具特色。
伯 父
伯父姓徐,说话带腔。听父亲讲他是山西洪洞人,解放前扛活来到我们村。我亲伯父去世后,他被招为 “驸马”。
徐伯的大半生是在村里护山,大概是职业的关系,他整天板着黑树皮般的脸,好像谁都欠他二百吊钱似的。平时,也很少与人拉扯国事、家事,村里人都叫他“老阴天”。
我童年最恨的就是这位“老阴天”,他好像跟我们结下了几代怨仇,处处让我们这帮“野小子”过不去。放学拾草是我们童年的天职,我们常常提着蓝子边拾草边到柿树下捡柿子红吃 (已成熟蒂落的柿子),有些挂在树上还没蒂落的柿子红,我们便急不可待地用石头打,往往能打掉许多生柿子。对打下的生柿子我们最怕的就是护山徐伯伯,他硬逼我们啃生柿子,不啃就用护山棍敲我们。啃一口涩得张不开嘴,吞在嗓子里塞得直打嗝,以此达到他惩罚我们的目的。
徐伯不愧是护山高手,村里年年瓜果树木都很少丢失,特别是对付我们这些“野小子”很有一套。放学之前,他在柿树旁的松树墩里隐藏好,当我们热火朝天打柿子红时,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像老鹰捉小鸡似的将我们逮住。有时我们偷吃个甜瓜梨枣之类的东西,也蒙骗不过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你若不承认的话,他有办法治你,领你到沟下喝水漱口,一漱口便一清二楚了,若有怠慢,他那护山棍会麻利地敲在你的屁股上。
徐伯对工作一丝不苟,遇事总爱叫真。那年大队长小儿子上山砍柴,为检验镰刀是不是锋利,将队里的玉米砍倒一大片。徐伯就把他带到了大队办公室,当时大队长不在,会计说:“小孩子不懂事,批评几句就算了。”徐伯说:“那不行,要是摘个甜瓜梨枣的也就算了,那玉米正在长果实的时候,糟蹋了怪可惜的。如果用上纲上线的话说,这不是明摆着在破坏农业生产吗?不处理还了得。”会计再没吱声,心里想真是打铁不认火候,人家是大队长的儿子,我看你能咋处理?
过了不大一会儿,大队长就回来了,嘴里哼着小调,见儿子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心里就琢磨,十有八九是惹祸了。这时徐伯就说:“你看咋办吧大队长,你儿子砍倒了队里一片玉米,数了数整整50棵。”大队长寻思了会说:“这事交给我了,你该去干啥干啥,等支部开会商量一下,一定会处理的。”
大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社员打仗斗殴、偷盗罚款什么的,都写在大队中心大黑板上。没过几天,徐伯就去看大黑板,没有罚款。再过几天去看,仍不见处理。徐伯就去了大队办公室,正好大队长、会计都在。徐伯就问:“大队长,你儿子那事不处理啦?”大队长本来在埋头看报纸,听徐伯这么一问,说了句“没倒出空来商量”,就放下报纸走了。大队会计就说:“老徐头啊老徐头,你咋老是一根筋呢?你没考虑这事有点棘手吗?假如这次处理了大队长的儿子,你让大队长在社员面前多没有面子,以后还怎么去管别人?再说啦,这事处理不处理那是当官的事,你着的什么急?罚款也不是装进你兜里。”徐伯一听这话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怎么能洪胡子打官司一面理呢?前几天“破抬筐”他儿子偷刨了队里两顿地瓜都被罚了10块钱。人家偷刨队里地瓜,填到肚子里可充饥,而大队长儿子砍那片玉米是糟蹋在地里,谁都没得。这两码事虽说都是过错,但完全是两种性质,如果这事不处理,往后我这护山活还有法干吗?”大队会计不紧不慢地试探着说:“假如这次真不处理了呢?”“那我就不干了。”徐伯转身就气冲冲地往外走,后手在带门时用力过大,只听门“哐”的一声卡上了。
大队长必定是精明人,他知道遇上徐伯这样的一根筋,没有个明确的结果他是不会罢休的。大队长也怕这事越搞越大,会小口撕成大窟窿,就对儿子做了处理,但没上黑板,这事也就了结了。
因为徐伯护山不论亲朋,敢唱黑脸,自然在村里就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年冬天,大队里仓库玉米被盗,人家却把道“卖”到徐伯的家门口。(把玉米随道撒到他家门口,当地人把这种行为叫着卖道)大队的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把徐伯关在一间小黑屋里,说他执法犯法,看着别人自己偷,便昼夜逼供,免不了也吃了些“刑法”。但他始终没承认偷玉米这件事,最终因证据不足把徐伯放出了小屋,调换了护山工种。后来他人犯事了,交待了盗仓库玉米之事,他的冤假错案才得以澄清。
我高中毕业后就进城参加了工作,平日无事难得回家一趟。听村里来人讲,徐伯不知得了一种什么病,手脚瘛疭,两腿走路像搓草绳,大脑反应迟钝,说话困难,时间不长便去世了。每年清明节回老家上坟,我总忘不了到徐伯坟前祭奠一番。看着那袅袅的纸火,徐伯那高大魁梧的身躯,还有那整天板着的“老阴天”脸以及他那铁铸的一身正气,便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心想,如今建设新农村,多么需要徐伯这样的人啊!
吹二叔
崔文兴在村里辈份属中等偏上,不少人称他叫崔二叔。因他说话离谱、水分太多,可以说十句话七句是泡的,所以村里人就改称他吹二叔。
那天吹二叔喝了点酒、满脸红扑扑的,青筋蹦得老高。刚走进老人场(老人扎堆闲聊的地方)便和“扛子头”较上了劲,相互吹了起来。“扛子头”说:“俺妹夫种那片谷子,长得绝门了,谷粒有鸡蛋大。”吹二叔说:“那算啥,俺表弟家养那只羊,前几天下了头驴,秤秤足足五百斤。”“扛子头”说:“下头驴五百斤,那羊多少斤?”吹二叔说:“羊才百十斤,要是羊重就不为奇了。”“扛子头”不服气,说:“俺外甥养了头猪,你猜有多大?头在南海喝水,腚在北海拉屎。”吹二叔哪肯服输,本来吹牛皮就是他的强项。便说:“俺二姑家那个儿子,长得上顶着天,下柱着地,你说有多高吧?”两人一个能吹牛,一个能抬扛,越说越离谱,是谁也不服谁,最终不欢而散。
不过,多数人吹牛是为了逗笑、取乐、开心。而吹二叔吹牛却不仅仅是为了这些,还凭着那张善说会辩的嘴为四个儿子娶上了媳妇,过着儿孙满堂的日子。
吹二叔家只有一栋房子,那房子可不是吹二叔吹,在村里是最上档次的房子。四间舞岭小瓦房,南厅北正,外加东西厢房,跟北京的四合院差不多,是土改时期分得的“果实”。吹二叔就凭着这套老房子,先后忽悠了四个儿媳妇上门。
起初,大儿媳妇韩影来看家时,吹二叔领着媒人和媳妇在院里转了一圈,他指着南厅说:“这是磨房,碾谷磨面不用出门,下雨刮风也不怕,方便得很。四周的邻居都来用。”媒人站在那里直点头。“不错,不错”。走进东厢房,屋里摆布的相当讲究。中间是一张八仙桌,上面铺着台布,四面摆着太师椅,显得小屋很是雅致。“这是我的客厅,专门用来招待客人。你们先坐下休息会,我去泡茶。”吹二叔说完便出门向正房走去。
这时媒人就问韩影:“怎么样?满意吧!”韩影笑了笑,并没表态。媒人又问:“这样的条件还不满意啊?我跟你说吧,能找着这么个人家算你烧高香了,以后就等着享福吧”!韩影寻思了会说:“这房子是挺好的,可他们毕竟是兄弟四个,这房敢保能给我们吗?”“能给。我提媒时说过这房子,吹二叔一口答应了,说谁先蹬门就给谁。你若不信等他过来我当面问问”。说话当中,吹二叔左手拿着几个杯子,右手提着茶壶就进了客厅。“来来,大热的天,喝点水解解渴。”“我说大兄弟,人家韩影可看中了这栋房子,你家四个儿子,能确定给她吗?”吹二叔忙说:“行,这事我说就算了,他们兄弟以后我给盖新的。”看家告成,婚事确定。
韩影结婚刚一个月,吹二叔就找到她说:“你们出去租个房子住吧,这些人住在一起太拥挤。”“哎爹,当初看家时你亲口答应这栋房子给俺,怎么现在又撵俺出去租房呢?”吹二叔就解释说:“当初我是答应这房子给你。可你兄弟们还没结婚,我能叫他们出去租房子住吗?你尽管放心,等他们都结了婚,这房子马上就倒给你。”韩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既然公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到外面租房住去了。
轮到老二、老三、老四成亲时,吹二叔都是用这个法子,把三房媳妇忽悠到家,一栋新房也没盖,这可不是吹牛,谁有这两下子呢?
纸终究包不住火,疮长到一定程度是要破头的。待吹二叔四个儿子都结婚后,韩影就提出了要房子的事,妯娌们一听都瞪了眼。这个说答应给她,那个说答应给她,乱成了一团。吹二叔摆摆手说:“别争啦,这栋房子我是都答应过给你们。可现在就这一栋房子,也没钱再盖新房子。大家面对现实吧,这栋房子都是你们的,大伙都搬进来住。南厅一户,北正一户,西厢一户,东厢一户。这房子有好有赖,谁都想住正房,不愿住厢房。我看这样吧,你们兄弟四个抓阄,凭头皮子来,抓着好的住好的,抓着赖的住赖的,这样公平合理。你们看这个法子怎么样?”四个儿媳妇都愣了神,你这老头子咋这么耍人,你知道我们现在都生米做成熟饭,不能抱着孩子回娘家,就来这一套,真岂有此理。可反过来又想,事到这般田地闹也无济于事,即便把这老东西告到法庭上,他拿不出钱来盖房子,你还能扛着他去填海吗?自认倒霉吧。
有人说吹二叔不是把媳妇吹到家里的,而是骗到家的,此话不无道理。但仔细回头想一想,吹二叔当初曾答应这栋房子给每个儿媳妇,他给了吗?没给就是说大话。吹二叔还说过给后面的儿子盖新房,他盖了吗?没盖就是吹牛皮,说骗也不过分。
现在吹二叔是想开了,我就这把老骨头,你们随便说去,反正我的使命完成了。闲着没事还去吹牛。
梁满坡
定的是晚上七点演出,这都七点二十了梁满坡还没露面。大冬天的露天演出,台下的观众冻得搓手跺脚,俱乐部的领导更是急得挠耳抓腮,曾两次派人到家里催,现在仍不见个影儿。没办法,他是拉上手的,不来就开不了台。梁满坡这人哪里都好,就是有点艮,他不是一般的艮,而是相当的艮,可以说是火上房子也撵不出他个小跑来。
梁满坡在村里算是个聪明人,年轻时干过多年小队会计,中年时自学中医当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经他看病的人都说脉试挺好,下药也到位,周边村庄的人都来找他治病。美中不足的是,找梁满坡看病得耐得住性子,靠得起时间,因为他太艮了,就像性急人吃不得热豆腐似的。那年梁大囤的小儿子患了重感冒,严重时抽风瞪白眼儿,吓得夫妻俩不知所措,以为是患了重病症,危在旦夕。
梁大囤就吩咐老婆海风快去找梁满坡来给孩子看病。当海风急三火四来到村医疗室时,梁满坡正在院里与人下棋,海风就说:“满坡叔,俺家孩子病得不轻,梁大囤让俺请你去看看。”
“知道啦。”梁满坡头不抬脸不转,仍在聚精会神地下棋。
梁满坡下棋不像别人,三下五除二,快刀斩乱麻。而是对着棋盘看来看去,很长时间动不了子儿,有时瞅了半天,找准了步,拿起子还要端详一番,在确保万无一失时才肯撒手,年轻人一般都不愿与他对弈。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棋下得仍不见胜负,梁满坡也丝毫没有起身告辞的意思。
站在一边的海风却急得心如火燎,心想,看走个子那么难,又不输房子输地的,浪费那么些精力干啥?出门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儿子的病咋样。一想到儿子的病,海风的火就冲到了头顶。孩子病成那样,耽搁时间长了有个闪失咋办?她真想说你这老艮呀,快去给俺儿子看看病吧!可转念又想,求着人家办事哪能失礼呢?一旦得罪了满坡,他不正经给孩子看病咋办?还是耐着性子等一回吧,说不准再有五分钟就决定胜负了。
可眼前的梁满坡显得异常沉稳,似乎就没有给孩子看病那回事。他拿起马本想往前跳,下步卧槽吃炮。可刚要放子时又看到对方的车不但可以过来别腿,还威胁到马的安全,于是将马又放回了原位。又过了十分钟,双方仍势均力敌,胜负难见分晓。海风就有些待不住了,她忍着急躁笑着说:“满坡叔,先去给儿子看看病吧!”梁满坡全神观着棋,嘴里不紧不慢地哼了声,“好,侄媳妇”,却不见动身。
儿子的病仍不见好转,闹腾厉害。梁大囤就抱着孩子从这屋走到那屋,又许愿给儿子买什么什么好吃的,什么什么好玩的,但都无济于事,儿子仍哭闹不止。梁大囤心里就上火,嘴里不停地骂老婆。这个臭娘们,叫她去找医生,不知又跑到哪儿串门去了,半个多小时了还不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骂完了又自己嘱咐自己,再坚持一会吧,说不定正走在路上呢。
又过了几分钟,外门终于“吱”的一声开了,梁大囤心里立刻亮堂了许多,他忙抱着孩子向外迎去,一看是自家的大黄狗进了院子,并无他人,心就一下子凉了下来。梁大囤想,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还是我抱着去吧!他不顾锁门,抱着孩子就急步向医疗室走去。刚要拐弯时正好撞见海风和梁满坡。
此时的梁大囤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忘记给孩子看病的首任,而是朝着老婆瞪眼吼道:“你这臭娘们能干点啥?叫你去请医生能请半天,好像这孩子不是你生的,一点不知焦急。”海风听了这话很窝火,脸立刻扭曲起来。凭良心讲,孩子病成那样,她心里能不着急吗?可海风是干着急不出汗。问题不是出在她身上,可当着梁满坡的面她又不好将事情挑明,只能忍气吞声。
有人说梁满坡艮有两种原因:一种是他太好下棋了,棋子一摆啥事也不顾了。另一种说艮是与他的岁数有关,年龄大的人偏行动迟缓。这两个原因说得似乎有些道理,但对梁满坡来说绝对不是道理,他年轻时就艮得出名。那时梁满坡还在生产队干会计。有次往山里运粪,整劳力推小车,小学生和青年妇女负责拉车。从身体状况看,梁满坡在队里最棒,他一米九的大个儿、身材也魁梧。摊了个拉绳的更棒,是下乡知识青年。运粪途中有个小下坡,接着又是一个挺陡的大上坡。一般人都是下坡时带点小跑,利用缓冲的力量拱上坡。而梁满坡不是这样,下坡时仍慢悠悠的,上坡时自然就没有冲力,尽管拉绳的青年累弯了腰,车子还是推不上去,大家就笑,趟趟这样。没办法,这是他的本性。
滚刀肉
啥叫滚刀肉?翻了几本词典没找到答案,后查阅网上,说滚刀肉是猪身上的一种肉,既不是瘦肉也不是脂肪肉,正确地说是一种“囊肉”,是品位最低下的一种肉,用刀切起来很费劲,容易打滚儿。而老百姓把滚刀肉则比喻成是难斗、遇到事很缠身的人。我们村就有这么一个,实名叫王德岚,外号叫滚刀肉。
照理说在农村凡是脸皮厚的,或者说拿着不是当理说的人大都是些男爷们。因为女同志脸皮薄,爱面子。可我这里要说的恰恰就是个女同志,确切地说是个中老年家庭妇女。
王德岚在村里辈分挺大,相貌长得也不错,可在村里却很少有人与她交往,多数是见了面躲着走。你“百刺毛”再厉害,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你还真说错了,那是没遇到事,遇到了你躲都来不及,跑也跑不掉。
七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大集体企业像雨后春笋般的涌出,上面就经常到各公社招工,公社再把指标分给下面个各村队。大村队能摊两三个,小村队一般是一个名额,几乎年年都是这样。那时能脱离农村,到城里端个铁饭碗,那是庄稼人期盼已久的事。
七六年春天,王德岚就找到村长说,“村长啊,听说上面又来了招工指标,这次给俺家当意吧。孩子今年二十五岁,再不那个岁数就过岗了。”
“你听谁胡说,根本没有的事。”
王德岚就笑着说:“算了吧村长,你认为我没长耳朵啊?你说咱村啥事能瞒过我王德岚。人家说了,这回咱村摊了一个指标,是去县化肥厂的。怎么样?消息确切吧!”
村长见骗不过滚刀肉,就说,“上边来了个指标,等村委研究再说吧!”
王德岚不听他的忽悠:“算了吧村长,你就别卖关子了,咱村啥事不是你说了算,还研究个啥?”
村长说,“这是村里的规定,走过程也得走。”
“那好村长,我回去就听你的准信了!”
滚刀肉说的确实不假,指标给谁完全是村长的一句话,这是他的权利。不过,你认为村长这句话好说吗?前几天 “赵大嘴子”为给儿子争取这个指标,送去一百元的东西。村长的儿子初中毕业大半年了,至今还在队里割牛草。再说村委干部那些子女也都老大不少了,都在大眼瞪小眼的看着,就是上面下来十个指标也轮不到你滚刀肉身上,想去那不是在做美梦吗?
最终名额确定在村长儿子大成身上。滚刀肉听说后像疯了似的去找村长评理,正好村长从家里赶着车向外走。“哎村长,前几天你答应这次招工让俺儿子当意去,怎么又改成你家大成了呢?”村长知道滚刀肉难斗,就忙跨上自行车说;“我去公社开会,没工夫跟你谈,等回来再说吧!”村长自认为这样能甩掉滚刀肉的纠缠,等过几天儿子上了班,就是她再滚刀也无济于事了。哪知村长想错了,如果这么轻易能摆脱王德岚的话,她那滚刀肉称号不是徒有虚名了吗?村长前脚去了,滚刀肉回家赶出车后脚就追去了。
滚刀肉来到公社时,干部们正在开会,她就坐在会议室门前的台阶上,寻思着怎么让村长丢丢丑。在台上讲话的是刚调来的刘书记,她不熟悉滚刀肉的情况,就问王德岚,“坐在门口的女同志在等谁?我们在开会呢。”
这不问不打紧,这一问滚刀肉起身进了会议室。“正好各位领导都在场,我有个事向你们反映一下。前些日子俺村摊了个招工指标,村长答应给俺儿子当意,可后来又改为他儿子大成,这不是明摆着耍人吗?再说俺儿子是高中生,他儿子是初中生,说话又结巴,前些日子去‘地不平’家偷人家的小媳妇挨了一顿揍,难道这样的人也配当工人吗?”开会的干部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刘书记用力拍了一下桌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快给我轰出去。”高秘书和村长就把滚刀肉推出了会议室。
村长说王德岚,“你咋胡说八道也不分个场所?”
“我胡说什么了?你前天亲口答应回去研究,让我回家听信,结果呢,指标给了你儿子,耍戏人咋的?”
村长忙解释说,“我啥时答应给你儿子了?要是答应了,还用开会研究吗?你当着那么多干部的面把我糟蹋得狗血喷头,以后还让我怎么在领导面前为人?”
“为人?你的为人谁还不清楚,要是我陪你睡上一觉,我儿子早进城当工人了。”会议室里又传出一阵大笑。
高秘书就板着脸说滚刀肉,“有事说事,咋唱着唱着就跑调儿了呢?”他又转头对村长说,“你看这事闹成啥样子?快拿个解决的章程吧?”
村长寻思了会儿对滚刀肉说,“回去叫儿子准备吧,后天到厂里报道。”
“这还差不多。”滚刀肉甩手走了,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都知道滚刀肉缠身难斗,可村里就有个别人不知深浅,总爱往枪口上撞,你想想能有好果子吃嘛?那天王麻子喝点猫尿,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他在与滚刀肉迎面打招呼时,顺手摸了一下人家的乳房。这下可捅翻了马蜂窝。像滚刀肉这样的人,平日无事都想找茬,你主动去招惹她,那不是兔子撞门把肉送进家了吗?滚刀肉把脸一横说,“王麻子,你活腻歪了咋的,竟敢占老娘的便宜,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啥样子。你说吧,摸一下给多少钱?”王麻子喝得有些站不稳,他晃动着身子说:“你那破玩意跟老母猪奶子差不多,还要什么钱,想诈骗吗?”滚刀肉上去就从王麻子上兜掏出几百块钱走了,王麻子追去,被滚刀肉狠狠地推倒在地。
王麻子清醒后,就琢磨这事,那天到底喝那些酒干啥,摸了一下奶子丢了几百块钱,太亏本了。可转念又想,谁让自己犯贱呢?也罢,破财宁人,买个教训吧,以后这样的傻事再也不干了。王麻子想得太简单了,你想摸就摸,你想洗手就洗手,这不是你能掌控的事。没停两天,滚刀肉就找上门了。“王麻子,你看咱那事儿咋办吧?”王麻子不解,“啥事?”“你别揣着聪明当糊涂,摸老娘的奶子,两天就忘了,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王麻子忙说:“你不是从兜里掏钱了吗?怎么还找茬呢?”滚刀肉阴沉着脸说:“那才几个臭钱,你想打发要饭的呀?我告诉你明白,没那么容易!”“不就是摸了一下奶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想干啥?”滚刀肉不紧不慢地说,“不想干啥,给五百块钱吧。”“五百?没有。”“好,你没有,我跟你老婆要去。”王麻子一听坏事了,他忙从兜里掏出一叠钱,点出五百给了滚刀肉。
过了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滚刀肉手头有些紧巴,就又想起王麻子,就找到他说,“王麻子,给几个钱花花。”王麻子一听这话头就老大。前几年攒的私房钱被滚刀肉一把拿去了。上次那五百块是准备买化肥的钱,为这钱跟老婆打了个翻江倒海,再给就只好跟别人偷借了。王麻子就与滚刀肉交了底,“我现在兜里没钱,等过几天我倒借几个给你,中不?”“那行,我再等你两天。不过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想坐蜡可是没门的。”
从那以后,王麻子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滚刀肉简直就是个无底洞,啥时才能填满这个窟窿呢?不给吧,她就会把问题捅到我老婆那里,这个人啥事都能做得出来,不计后果。真到那时,破了财丢了人,还要跟老婆论持久战。你说这日子还有法过吗?思来想去,最终王麻子选择了上吊。王麻子死也是白死,别人又没逼你,按活该倒霉处理。怎么样?滚刀肉厉害吧,不服都不行。
王德岚还有许多滚刀肉的事,细分析也不全怪她王德岚。就说招工吧,凭什么就该干部子女去,老百姓的孩子靠边站。再说王麻子。你喝了点酒蒙着脸就去摸人家老婆的奶子,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只是王德岚做得有些过分罢了。
根 儿
根儿是村里出名的老实人,老实到什么程度呢?恐怕说出来大家有些不可思议,不信我就拉段给你们听听。前年春上,别人睡他的老婆被根儿当场捉了个现行。按理说这号事搁在谁头上也咽不下这口气。可根儿,扭头走了。怎么样?老实的够“级别”了吧?有人不信,说我在编瞎话,这不可能的事,别人给他戴绿帽子撞见了都不管,除非他脑子长疤吧。别的事可以让步,这号事没人会让步的,全是胡扯。你不信吧?后面写着呢,自己去瞧瞧吧。
根儿从小命苦,3岁那年爹就去世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大概是家境贫寒和根儿过于老实的缘故,他40岁了仍是光棍一条,为这事老母亲的双眼都盼瞎了。根儿42岁那年却意外交了桃花运。提媒的找上门说:“有个18岁的云南姑娘,想在咱这找个婆家,只要出两千元中介费就行。”根儿听了忙摆手说:“不行不行,人家小姑娘才18岁,陪伴我这个半拉老头差齐大了。”媒人就说:“你出钱她出人,公平合理。再说,婚姻法上也没规定岁数小的不能跟岁数大的结婚呀,你没看报纸上登的,一个55岁的副局长还说了个24岁的大学生做老婆呢。”根妈也说:“别整天傻乎乎的,人家闺女不挑剔你还唠叨啥?出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依我看还是应下吧。”根儿再没吱声。当天夜里,媒人就把一个哭啼啼的云南姑娘带到根儿家里,点完钱便对那姑娘说:在这里好好过日子,要是东跑西颠的,我打断你的腿。接着就大步流星地走了。根儿见姑娘老哭,就说:“睡吧,别哭坏了身子,我不会难为你的。”姑娘仍哭不语,根儿就自顾自地睡了。
又过了几天,云南姑娘老是整天哭哭啼啼的,也不吃饭。根儿就去找媒人说:“快把她退回去吧,万一弄出个人命案子来,我可担当不起。”媒人说:“你是个木头人,甜的不行不会换点辣的?回去吧,今晚我去。”
当天晚上,媒人来到根儿家,上去没鼻子带脸的扇了姑娘两个耳光子,厉声喝道:“把衣服脱下!”云南姑娘在武力的威胁下,忍气吞声地脱下了外衣。媒人上去一把将姑娘的内衣撕碎,雪白的胸脯立刻露了出来。姑娘慌忙拉被捂住,哭声渐大。媒人说:“睡吧,再不顺从看我怎么收拾你。”接着就拉灭了电灯,出屋时将门反锁上了。
根的婚事很快透了风,几个小青年都逗扯他:“老根儿,和云南姑娘睡得怎么样?”根儿说:”还没登记睡啥觉啊。”张玉刚就说:”你和云南姑娘在一铺炕上过夜,谁信猫儿不吃腥。”根儿说:”没睡就是没睡,撒谎是个驴。”还嘴硬,张玉刚上去就抱住根儿用力捏他的鼻子,”睡没睡?”根儿痛得扭曲着脸,反抗了几下仍没挣脱,痛得实在没办法了,就说:“睡了”。“云南姑娘的大腿白不白?”“白。”小伙子们都笑弯了腰。张玉刚又说:”走,去小店喝几盅,为老棍庆贺庆贺。”
来到小店,小伙子们点了几个上档次的菜,又要了几瓶好酒,一会的工夫个个喝得脸像猴儿腚。张玉刚说:“老板娘,今儿老根请客,把账记在他身上。”根儿忙说:“我穷唧唧的,哪有钱……还没等根儿把话说完,小伙子们就把他拥出了小店,凭白无故地挨了一刀。
根儿由于饮酒过量,晚上睡得很死,半夜醒来时却发现云南姑娘不见了。邻居们纷纷出动四处寻找,根儿妈边摸着墙出门嘴里边喊着:“快帮着找找吧,两千块跑了呀!”根儿却坐在屋里不动。心想,走就走吧,留住人留不住心有啥用,这是早晚的事。再说,姑娘出来这些天了,恐怕爹妈早着急了,处事都要将心比心。
转眼间到了中秋节,各家各户都在忙着杀鸡宰羊,准备过个丰盛的八月十五。根儿没有那条件,就做了几个家常菜,就在他正准备喝上几盅时,云南姑娘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根儿愣了,瞪着大眼说不出话来。姑娘说:“你这人挺老实的,上次在这里过了七夜未碰我一下。这边的生活比俺那边也好,我想回来应这个亲。”根儿忙问:“你不嫌我年龄大?”姑娘摇摇头说:“不”。从此根儿有了婚姻生活,结束了他的单身生涯。
从此,村里人就开始羡慕起根儿来。“你看人家老根,都四十多的人了,还说了个葱俊的小媳妇,真是熊人有个熊福啊!”也有些人有事无事往根儿家里钻,没话找话的逗小媳妇开开心。大约过了半年的时间,村里就风言风语传出小媳妇不正派,跟几个男人睡过觉的说法。对这事根儿也有所察觉,也曾喝过闷酒。后来有人就背后给根儿出主意,让他暗中监视抓个现行杀杀风。根儿也确实这么做了,就是开头说的“凶手”捉到了,却连个屁都没放。出主意的人就问他为什么视而不管?根说:“关系都怪不错的,哪好意思。”出主意的人就说:“他好意思睡你的老婆,你不好意思整治他,这是熊到家了。”
根儿寻思了半天才说:“顺其自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