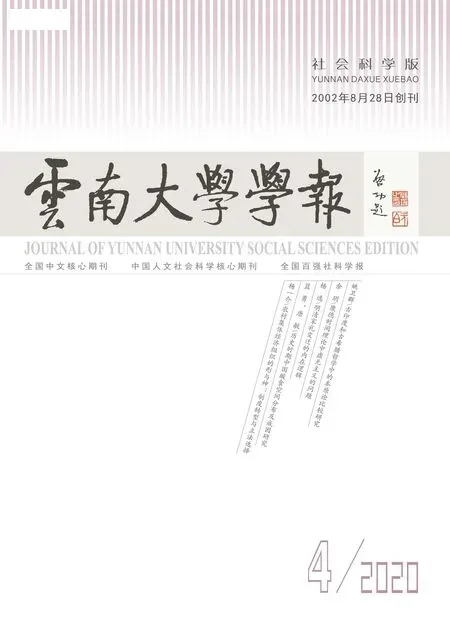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
——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杨 逸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严复(1854—1921)曾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严复 :《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8页。学者素来乐于援引这段名言,用以证明宋代对于中华帝国晚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不过,如果追问严复所谓“人心政俗”究竟何指,我们更可能将眼光从政治家、思想家身上移开,转而关注基层社会的普通民众。众所周知,宋代社会出现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私撰家礼著作的大量出现。据统计,宋代家礼著述约有40种,超过《新唐书·艺文志》相关著述数量3倍多。(2)杨逸 :《宋代四礼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这些著作绝大部分出自道学家之手,体现了宋儒通过考礼、编礼、行礼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卓越努力。(3)陆敏珍 :《宋代家礼与儒家日常生活的重构》,《文史》2012年第4期。其中,朱熹(1130—1200)《家礼》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从时间来看,《家礼》对士庶礼仪的影响绵宕元明清三代,以致今天还在不断激发着人们规范礼仪的热望;(4)近年来,朱杰人对于《朱子家礼》在婚礼上的实践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与讨论,如:田浩《儒学与时代精神笔谈》(《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朱杰人《朱子家礼之婚礼的现代实验》(《博览群书》2012年第12期),彭月肖《朱子〈家礼〉的现代实践——以朱氏婚礼为例》(《中华文化》2013年第6期)。从空间上看,《家礼》的影响力及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使得东亚民众至今维持着相似的生活方式。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催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如果这种提法成立,那么,这门学问的首要议题便是《家礼》如何在宋代之后的长时段中被导入基层社会,进而影响元明清时期的人心政俗与日常生活。对此,学界围绕《家礼》的版本与传播、《家礼》在明代社会的实践情况、家族构建与《家礼》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成果颇丰。但是,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泛论明清社会对于《家礼》的依违,忽视明清家礼中具体问题的讨论;第二,偏重政治(如大礼议)、文化因素(如阳明学)对家礼编纂的外在影响,忽视对家礼学变迁内在逻辑的思辨;第三,专注某部著作的独立研究,少有对明清家礼学历史变迁的完整论述。有鉴于此,家礼学研究亟须突破“外史”的研究思路,着眼于具体问题的分析与讨论,力求摸清明清家礼历史变迁的一般规律。本文以《家礼·昏礼》(以下简称《昏礼》)为中心,试图通过对明清家礼中婚礼仪文的细读与比较,揭示朱熹《家礼》婚礼仪文中蕴涵的问题与矛盾,以及明清家礼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与解决方式,庶希为明清家礼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一、朱熹《昏礼》中的问题与矛盾
朱熹《家礼》始撰于淳熙二年(1175),后在前往婺源展墓途中被行童所窃。(5)束景南 :《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75-686页。此后,朱熹就再也未曾修订过《家礼》一书,只是在平日行礼、书信往来以及与弟子交谈中零散论及对于冠、昏、丧、祭的新认识。所以,《家礼》是朱熹“早年未定之本”,其中多有不成熟的议论。陈淳(1484—1543)《代陈宪跋家礼》曰:
嘉定辛未,自南宫回,过温陵,值敬之倅郡,出示《家礼》一编,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即就传而归。……大概如临漳所传。但降神在参神之前,不若临漳传本降神在参神之后为得之。……恨不得及面订于先生耳。……惜其书既亡而复出,不于先生无恙之前,而出于先生既没之后;不及先生为一定之成仪,以幸万世,而反为未究之缺典,至贻后学千古无穷之恨。(6)陈淳 :《代陈宪跋家礼》,《北溪大全集》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9页。
可见,在朱熹殁后刊刻、流传的各种《家礼》版本互有差异,与朱熹晚年所论颇为不同,引起普遍困惑。陈淳认为,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家礼》在失窃后未及再修。因此,采用朱子晚年议论来订正《家礼》便成为朱门弟子的普遍思路。一种做法以后来刊刻的余杭本为代表,特点是将五羊本《家礼》进行删修成为合乎朱熹晚年观点的新本。(7)陈淳《家礼跋》曰:“先生……别为是书……方尔草定,即为僧童窃去。至先生没,而后遗编始出,不及先生一修,其间犹有未定之说。五羊本先出,最多讹舛……余杭本再就五羊本为之考订,所谓《时祭》一章,乃取先生家岁时常用之仪入之,惟此为定说,并移其诸参神在降神之前。今按余杭本复加精校。至如冬至、立春二仪,向尝亲闻先生语,以为似禘、祫而不举,今本先生意删去。”吾妻重二据此指出,现存各版本《家礼》并非余杭本系统,而是大体蹈袭了五羊本(吾妻重二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而现存诸本《家礼》受到的改动应十分有限,或可作为朱熹早年原本来研究。另一种做法以杨复的《家礼》注为代表,特点是在保留原本的基础上作详细注解,以说明朱子晚年定论。(8)杨复《家礼》注:“窃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发明《家礼》之意者……有后来议论始定……凡此悉附于逐条之下云。”(胡广编 :《性理大全》卷十九《家礼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6页)这些努力一方面极大推进了宋代家礼的研究,使《家礼》成为一个能够吸聚讨论的学术领域,另一方面则揭示了《家礼》作为“未究之缺典”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弥散于冠、昏、丧、祭各个部分的仪文之中,蕴藏有巨大的继续讨论的空间。
以《昏礼》为例。该部分主要取材于司马光(1019-1086)《书仪》与程颐(1033-1107)的《婚礼》。从杨复小注及陈淳跋文来看,《昏礼》在广州刊刻后未作大幅修订,相对完整地保留在后来《家礼》诸本中。不过,这不代表《昏礼》礼文完美无瑕、无可聚讼。如果将其与程颐《婚礼》、司马光《书仪》、吕祖谦《家范》等礼书对比便可发现,《家礼·昏礼》的仪式过程既非对前人的简单重复,亦非对于民俗的广泛吸收,而是以《仪礼》为尺度,将古礼经义融贯于礼文之中,试图建构一套可以“以礼化俗”的新时代礼仪系统。(9)杨逸:《“复礼”抑或“从俗”:论宋代家礼中的婚礼》,《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
(一)删“六礼”为“三礼”
程颐《婚礼》、司马光《书仪》都具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而朱熹《家礼》则去掉问名、纳吉、请期,只留纳采、纳币、亲迎三礼。对此,后来学者存在争论,有人认为朱熹《家礼》实际上具备六礼,只不过是将问名、纳吉、请期三礼并入纳采、纳币之中而已。为了附会此说,不少学者调整了告庙的祝辞与若干婚书,以凑成“六礼”之名(详见下文)。不过,《家礼》正文明确说:“古礼有问名、纳采、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币,以从简便。”(10)朱熹 :《家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3页。可见,朱熹本意就是要删减六礼,以建构三礼的婚礼仪式模型。不过,为何朱熹要删掉三礼,而不是合并六礼以存古礼之目?其根本原因在于朱熹对于六礼名义的理解与他人不同。《家礼·昏礼》纳采条小注曰:
纳其采择之礼,即今俗所谓言定也。(11)朱熹 :《家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2册,第543页。
纳采是“纳其采择之礼”,这种说法来自《仪礼》郑注,与程颐、司马光所说并无不同。关键在于,朱熹将纳采比附为当时婚俗中的定聘之礼。这便激发了六礼体系中的内在矛盾。如果纳采时两家便已订婚,那么,在订婚之后行问名礼以加卜筮,便难免会遭遇不吉的结果。一旦卜筮非吉,是否意味着已经定下的婚礼便宣告中止?如果中止,纳采所谓“定”的涵义又如何体现?因此,《家礼·昏礼》选择了删掉问名、纳吉的卜筮环节,以成就礼仪系统的圆融贯通。《家礼》的这一理解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走向,导致明清学者对“六礼”的误读与辨正。
(二)亲迎礼“从下做上”
从亲迎仪式来看,《家礼》以《仪礼》裁断小程、司马,形成了一个男先女后、由下向上、由卑到尊的仪式次第。受当时婚俗影响,宋代家礼的亲迎仪式或多或少都有纳俗入礼的情况。当时有所谓“拜先灵”婚俗,即在亲迎新妇至家后,由主人引导婿、妇在影堂告拜祖先。司马光《书仪》吸纳了这一仪节,并解释说:“古无此礼,今谓之‘拜先灵’,亦不可废也。”(12)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第104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36页。程颐《婚礼》在新郎至女家亲迎时增加了“见庙”等仪式,仪节为:“主人肃宾而先,宾从之见于庙。见女氏之先祖。至于中堂,见女之尊者,遍见女之党于东序。……主人请入戒女氏,奉女辞于庙,至于中堂。”(13)程颢、程颐 :《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22页。这种仪文设计恰是《书仪》针砭之事,所谓“亲迎之夕,不当见妇母及诸亲,亦不当行私礼、设酒馔,以妇未见舅姑故也”(14)司马光 :《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第1040册,第41页。。
对两家礼书改动《仪礼·士昏礼》的做法,朱熹《家礼》不以为然:
人著书,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马与伊川定昏礼,都是依《仪礼》,只是各改了一处,便不是古人意。司马礼云:“亲迎,奠雁,见主昏者即出。”不先见妻父母者,以妇未见舅姑也。是古礼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这不是。伊川云:“婿迎妇既至,即揖入内,次日见舅姑,三月而庙见。”是古礼。司马礼却说,妇入门即拜影堂,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妇,次日方见舅姑。盖先得于夫,方可见舅姑,到两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见祖庙。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须第二日见舅姑,第三日庙见,乃安。(15)黎靖德 :《礼六·冠昏丧》,《朱子语类》卷八十九,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4页。
从朱熹对两家的批判看,他所理解的婚礼大义有两方面内容:第一,“男先女后”,即新妇应先拜见舅姑及男家诸亲,之后再由新郎再拜见新妇之母及女家诸亲,程颐《婚礼》的问题即在于此。第二,“从下做上”(16)郑玄注、贾公彦疏 :《礼六·冠昏丧》,《仪礼注疏》卷八十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73页。,即先行合卺同牢之礼,以成夫妇之义;再见舅姑,盥馈奉饮食,以成子妇之义;最后才可见祖庙,行祭祀,成为男家正式成员。这种从卑至尊、由人到神的次第彰显了“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的庄严意义。不过,这种遵行古礼的做法不但与婚俗有龃龉处,还有违人情常理。例如,《仪礼》《家礼》在亲迎至家后都未提及舅姑,那么,是否意味着舅姑应该避免在当晚与新妇会面?若是,何以体现舅作为婚礼主人的主导地位,又何以寄寓新妇尊敬舅姑乃至男家先祖的情谊?这些问题都成为明清家礼学中的重要问题。
(三)改行三日庙见
从成妇的终结界限看,《家礼》将庙见的时间由三月改为三日,有与“拜祖先”混淆的倾向。庙见又称“奠菜”,是为舅姑殁者所设的变礼。《仪礼·士昏礼》曰:“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17)郑玄注、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页。《礼记·曾子问》曰:“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18)郑玄注、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郑注曰:“谓舅姑没者也。必祭,成妇义者,妇有供养之礼,犹舅姑存时,盥馈特豚于室。”(19)丘濬 :《文公家礼仪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584页。可见,庙见礼后当择日祭祢,成全“成妇之义”,婚礼于此时宣告完结。
在《书仪》中,司马光将“拜先灵”之俗比附为古礼中的庙见,并说:“古有三月庙见之礼,今已拜先灵,更不行。”(20)司马光 :《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第104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页。则是以拜先灵取代庙见,将行礼时间前调至新妇至家时。朱熹虽然不主张删掉庙见礼,却在批判《书仪》时流露出对司马光观点的赞许。所谓庙见、拜先灵两者不可得兼的评论,实质上正是在“庙见即拜先灵”前提下提出的。于是,《家礼》三日庙见之礼便被偷换为主人以妇见于祠堂的具文:
庙见。三日,主人以妇见于祠堂。古者三月而庙见,今以其太远,改用三日。如冠而见之仪,但告辞曰:“子某之妇某氏敢见。”余并同。
这个庙见仪式与古礼差异巨大,根本回避了舅姑存殁的问题,从而将“庙见”彻底改造为“见庙”,失去了“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的意义。
二、明清家礼对《昏礼》 的补充与改造
《家礼·昏礼》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不但反映了宋儒在重构婚礼仪文时所遭遇的复杂现状,更体现出朱熹在礼书编纂过程中对于古礼、时俗的独特理解。虽然朱熹真诚地认为自己坚持了古礼大义,实际上却既未避免对于古礼的曲解与误读,又未必能够安置沛然如水的人情。因此,当《家礼》从文本转向实践,尤其是明代官方使用强制力在民间推广时,《家礼》中的问题与矛盾日益暴露,对它的反思与改造随之开始。
(一)补完六礼的尝试
经过汉唐经学的总结与注说,“六礼”已经成为一般常识,进入士大夫一般知识、信仰与思想的世界。朱熹删“六礼”为“三礼”的做法不但与古礼相依违,更冲击了人们对于婚礼的一般理解。于是,将问名、纳吉、请期重新补入《家礼》,重构婚姻六礼体系便成为宋代之后家礼学者关注的问题。
在明代家礼著作中最早试图补完“六礼”的是丘濬(1421—1495)的《家礼仪节》。该书在《昏礼》卷首写有按语一则:
濬按:古有六礼,《家礼》略去问名、纳吉、请期,止用纳采、纳币、亲迎,以从简便。今拟以问名并入纳采,而以纳吉、请期并入纳币,以备六礼之目。然唯于书辞之间略及其名而已,其实无所增益也。(21)丘濬 :《文公家礼仪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卷三《昏礼》第479页。
诚如所言,《家礼仪节》对书信内容作了些许调整。所谓在纳采中并入问名,便是在纳采书式中补称:“谨专人纳采,因以问名,敢请令爱为谁氏出,及其所生月日,将以加诸卜筮。”(22)张汝诚 :《家礼会通》,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集新堂藏板刻本,卷三《昏礼》第479页。所谓在纳币中并入纳吉、请期,便是在纳币书式中补入:“加之卜占,已叶吉兆,兹有先人之礼,敬遣使者行纳征礼,谨淯告日以请。”(23)张汝诚 :《家礼会通》,卷三《昏礼》第479页。由于没有涉及任何关于卜筮的仪节,《家礼仪节》中补入的问名、纳吉并不具有行礼的实际意义。(24)按《仪礼》郑注纳吉:“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于是定。”以《文公家礼仪节》的著述体例,凡是仪式都设有详尽仪节,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不设卜筮,则是丘濬并无实际行礼之意愿,徒具虚文以成六礼而已。更加重要的是,丘濬赞同朱熹以纳采为“定”的观点,补入问名、纳吉将会导致礼文内部的冲突——不卜筮则流于虚伪,卜筮则有不叶吉的可能。不论何种,都将极大削弱“六礼”之间的内在圆融,导致礼文的前后龃龉。
对此,明清家礼中出现了两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一种是在保全“六礼”的前提下,调整各个礼仪之间的次序。如吕坤的《四礼疑》指出:
纳采而后问名,名无当也,采如之何?问名而后纳吉,吉不叶也,名如之何?六礼之次,汉人失考矣。……纳采既奠雁用币矣,尚不知其何名而后问乎?问名既相宜矣,尚疑其不吉而后卜乎?倘若不相宜,将废采乎?不是不同吉,将停昏乎?先王不如是之疏也。恐古礼有错简,汉儒失考耳。《家礼》纳采即问名,而纳吉、纳征、请期合而为一,极为简便,稍涉造次。若问名而后纳吉,次纳采定礼也,次纳征即纳币,次请期,次亲迎,于义为近。(25)吕坤 :《昏礼》,《四礼疑》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54页。
所谓《家礼》“纳采即问名,而纳吉、纳征、请期合而为一”云云,显然是就丘濬《家礼仪节》而言,并非朱熹《家礼》本意。不过,吕坤认定纳采即定礼,却的确是朱熹《家礼》所传达的观念。由于认同这种观点,吕坤才会感觉汉儒关于“六礼”的排序有颠倒错略、疏于考证之处。他的解释是,《仪礼》可能存在错简,而汉儒未及发现,于是主张重新厘定“六礼”次第:先问名、纳吉,之后再行纳采、纳征、请期、亲迎之礼。吕坤的这种观点极具批判性,是将朱熹《家礼》主张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清代亦有采用此说者,如张汝诚的《家礼会通》。(26)张汝诚:《家礼会通》。
第二种是删掉纳吉之礼,重新界定问名礼的意义。如毛奇龄(1623—1716)《家礼辨说》云:
昏礼五六原无成数,《公羊》称五礼,《谷梁》鉴定称四者,以亲逆非通接之礼,而纳采、问名后不当又纳吉也。婚姻卜吉当在行媒之后、纳采之前,假使采择既讫,女名已通,《曲礼》所谓相知名者,而然后命卜,则万一不吉,其可以吾子贶命加卜不良致辞也乎?且卜何必告也。谷梁说是也。(27)《婚礼辨正》,《毛奇龄家礼辨说》卷十六,《丛书集成续编》,第6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436-437页。
与吕坤相似,毛奇龄也意识到纳采之后将女方姓名加诸卜筮所带来的难题。不过,他并未试图通过改动六礼次序来消解矛盾,而是站在反思“六礼”之说的高度上,指出“六礼”本身具有瑕疵。他对比《谷梁传》的“四礼”之说(纳采、问名、纳征、告期)与《公羊传》的“五礼”之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后指出,《谷梁》的说法更加符合逻辑。不过,如果涉于卜筮的纳吉可以依据经典删去,那么,如何处理以“归卜其吉凶”(28)郑玄注、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3页。为直接目的的问名?毛奇龄的做法是推翻问名郑注的说法,代之以他说:
昏礼问名必问年月日,而后及于名。《周官》所谓“媒氏先书年月日名”是也。盖年较名为尤重。男女伉俪须先计年时,以辨长幼,其但称问名,而不及于年月日者,举一以该二也。(29)宋纁 :《婚礼辨正》,《四礼初稿》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437页。
可见,毛奇龄将问名礼的意义理解为计算年时以辨定长幼,绝口不言《仪礼》郑注所说的卜筮意义。通过这种诠释方法,问名之礼得以保留,而原本缺略的《谷梁》“四礼”之说竟奇迹般地复活。吊诡的是,虽然吕坤和毛奇龄都对朱熹《家礼》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却都默认朱熹以纳采为定礼的观点,在此前提下发现、反思、解决问题。所以,无论是厘正《仪礼》错简,还是考镜“六礼”源流,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颠覆原有经说对“六礼”的解读,从而带有几份强辩的色彩。
真正推翻朱熹《昏礼》,重建《仪礼》郑注的“六礼”框架的是清人曹庭栋(1700—1785)的《昏礼通考》(30)四库馆臣对此书评价不高,认为它涉及太多关于俗礼的内容,并未具备“自天子达于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以及“自先王以讫后世,通乎古今者也”的“通礼”编纂次第。不过这恰好说明,该书不是专门的礼学研究著作,而是以考据学方式写就的家礼著作。。其论纳采曰:
纳采者,始相采择,即今之求亲。问名者,问女之生年、行次,即今之请帖。此时昏姻犹未定。古人重视此大礼,宾必执雁以见。雁特贽物,并非聘物。问名后,若卜之不吉,则便休耳。其辞曰“将加诸卜者”,正以示昏事未定之意。后世相见无贽,并略拜迎致命之文,竟以纳采为言定。言定犹纳吉也,谓得吉以定昏姻之约也。是卜反在纳采之前矣。实则其初仍有求亲请帖之礼,即古之所谓纳采、问名耳。但今既以纳采为言定,则纳吉之礼更何所施哉!(31)曹庭栋 :《卜昏》,《昏礼通考》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454页。
曹庭栋切中肯綮地指出,朱熹对婚礼的理解的确存在错误,这种错误由“参用《书仪》” 引发,直接导致《家礼》变“六礼”为“三礼”的做法。(32)中川忠英 :《卜昏》,《清俗纪闻》卷七,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4页。从家礼学史的角度看,这一见解在理论上终结了《家礼》以来因混淆纳采与定礼所造成的误会与争论,重新树立了“六礼”的典范意义。
(二)亲迎礼序的反转
明代婚礼立制,从皇帝、诸王至于品官、庶人各有仪文,形成了一个从尊到卑、由上到下的婚礼等差体系。从《大明会典》记载看,虽然“礼下庶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庶人婚礼的礼文来源却与皇族、品官明显不同。前者来源于朱熹《家礼》为渊源的《孝慈录》,保留了《家礼》次日见舅姑、三日庙见的礼仪次第;后者取材自《政和五礼新仪》以来的官修礼典,以庙见为妇至男家的第一礼。这种内在矛盾促使明儒反思《家礼·昏礼》仪文。在明清家礼中,比较常见的观点是以《会典》之制调整《家礼》亲迎礼序。如宋纁(1522—1591)《四礼初稿》“庙见”条曰:
《家礼》妇至之次日见舅姑,三日见祠堂。盖以得于夫,乃可见舅姑;得于舅姑,乃可见庙。不为无见。但未见庙,先见舅姑,于礼未妥。今遵照《大明会典》改。拟于妇至之次日先见庙,后见舅姑,不惟妇之谒见,不失先后之序。其于舅姑之心,亦庶乎其相安矣。(33)宋纁 :《昏礼》,《四礼初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681-682页。
宋纁指出,《家礼》“从下做上”的礼序虽然很有见地,却并不能展现新妇对于男家祖先、舅姑的充分尊重,将导致舅姑与新妇之间心理上的两不相安。所以,《四礼初稿》将庙见前置到亲迎第二日夙兴,先由主婚者主导新妇见于祠堂,再行见舅姑与盥馈之礼。当然,宋纁所说“于礼未妥”中的“礼”并非指《仪礼·士昏礼》为代表的古礼,而是当时士庶所普遍认同的作为一般生活常识的“礼”。因此,宋氏并未试图通过考礼的形式对新礼做出说明,这或许就是“家礼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礼学”不同的重要原因。
同样是从尊重祖先、舅姑的理念出发,吕坤的《四礼疑》比宋纁走得更远。他说:
三月庙见,始执妇功,古人之迂也。朱元晦云三月以前恐有去事。礼有七出,非庙见之后乎?今也入门而庙见,情礼胥宜矣。(34)《毛奇龄家礼辨说》,《丛书集成续编》,第66册,第55页。
入门即庙见,这是吕坤为亲迎礼指出的一条情理相安的路径,旨在通过礼文调整实现对礼义的追求。实际上,大部分明清家礼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修订《家礼》仪文的。比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刊刻的《重修邱公家礼仪节》中对丘濬原本有作了较大改动,其妇至之后仪式次序为:庙见、合卺、妇见舅姑、舅姑礼妇、遍见尊长、同房、礼宾;明日回门,婿见妇之父母、庙见、见尊长诸亲。在此,历时三日的男家婚礼仪式被浓缩为一晚,新妇惟有庙见、见舅姑之后方能与行合卺之礼。同时期的不少家礼著作也普遍认同妇至先见庙的观点(见表二)。此外,据《清俗纪闻》记载,入门“先拜天地,次拜家庙,然后拜父母”(35)中川忠英 :《清俗纪闻》,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70页。是清人通行的婚俗。至此,朱熹《家礼》“从下做上”、先卑后尊的礼序被彻底反转为从上到下、先尊后卑。
(三)三日庙见的反思
在调整亲迎礼次序时,明儒继续朱熹的误解,将庙见与拜祖先混为一谈。于是,行至家庙见之礼则不再行三日庙见之礼,设定三日庙见之礼则不能再设至家拜祖之文。不过,清代学者开始发现这一问题,并尝试将“庙见”与“见庙”区分开。开启这项工作的是毛奇龄的《家礼辨说》。据说,毛氏幼时便已怀疑《家礼》亲迎之礼:
幼时观临人娶妇,至不谒庙,不拜舅姑,牵妇入于房,合卺而就枕席焉。以问塾师,塾师曰:“孺子焉知礼?礼不云乎‘不成妇者不庙见’,夫不先成妇而谓可以见舅姑、入祖庙,未之前闻。”予曰:“妇必寝而后成乎?”塾师不能答。(36)宋纁 :《婚礼辨正》,《四礼初稿》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434页。
在这个故事中,幼年毛奇龄竟能使饱读诗书的私塾先生一时语塞,当然不是因为考礼精详,而是因为他无意中触及了《家礼》礼文与礼义之间的断裂。在婚礼的整个过程中,男女双方的沟通都是通过主人、媒氏来主持、接洽的,但在至家、合卺、同牢等一系列礼仪中,主人与媒氏却都不在场。这不但有违礼重尊长的道理,还导致男女双方仓促会面的尴尬局面,不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礼成规,近似于“野合”。对于塾师给出的“从下做上”的标准答案,毛奇龄疑惑更甚:难道新妇需要通过合卺同房才能得到成妇的名分?后来,当毛奇龄向仲氏请教此事,得到完全不同的回答,因录其说为《昏礼辨正》,其文略曰:
自世不读书,不识《三礼》,不深辨夫子《春秋》,衹以宋学为指归。而宋人著书,一往多误。伊川程氏有三日庙见之语,而朱元晦作《家礼》即承其误,而著为礼文曰:“三日庙见,主人以妇见于祠堂。”且曰入门而不见舅姑,三日而始庙见者,以未成妇也。夫以曾子所问、夫子所言,“三月而庙见,成妇之义”,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庙见,不成妇不庙见。以三月为三日,以庙见为见庙,以子妇而为夫妇,以死舅姑为生舅姑,以不庙见不成妇为不成妇不庙见,以致五百年来自宋元至于今,自流沙至于日出,彼我梦梦,同入酒国。举生伦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会,而草草野合,涉于无赖。至请召宾客往来简帖,不曰“三日庙见”,则曰“儿媳某日行庙见礼”,抑又以凶丧不吉之辞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圣安在耶!(37)宋纁 :《婚礼辨正》,《四礼初稿》卷十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435页。
引文以檄文一般的措辞,列举了《家礼》“三日庙见”说的“五大罪证”:第一,《礼记·曾子问》有“三月而庙见”的明文,而将其改作“三日”,是为“以三月为三日”;第二,将本为舅姑亡故而设的庙见礼与婚俗中拜见祖先牌位的礼仪相混淆,是为“以庙见为见庙”;第三,成妇有夫妇与子妇之分,《家礼》以未成妇为不见舅姑的理由,是重视男女交媾的“夫妇”之道,轻视为人子、奉祭祀的“成妇”之道,是为“以子妇而为夫妇”;第四,舅姑在世而行庙见礼,则是以未死之人行既殁之礼,非常不吉祥,是为“以死舅姑为生舅姑”;第五,《曾子问》称“三月而庙见,成妇之义”,则是以三月庙见作为成妇的前提,而不是以是否成妇作为庙见的前提,是为“以不庙见不成妇为不成妇不庙见”。
因此,毛奇龄主张恢复舅姑殁而三月庙见的古礼,并依照《春秋》补入妇至见庙之礼,由主人主导新妇至家后行之。毛氏的观点批判《仪礼》而笃信《春秋》,对关键证据(如“先配而后祖”)的解读也存在偏差,遭到了当时一些礼学家的商榷与批判。不过,从家礼学角度看,毛氏的确提出了有礼仪实践价值的真问题。受《家礼辨说》影响,清代出现了一些试图分离“庙见”与“见庙”的家礼著作。如王复礼(生卒年不详)《家礼辨定》、林伯桐(1778—1847)《品官家仪考》等。
①今金华丛书本《家仪》非郑泳原本,而是后人郑崇岳(1550—1631)所补。《浦江县志》卷九《人物·政事》:“(郑崇岳)旋以计事不合告归。日集子弟讲习礼法,修饬祭器,及辑《宗谱》《圣恩录》《家仪》等书。”考《家仪》中有“二月十六日往庶子府君郑济墓处上坟”之制。按《郑氏祭簿》亦载此祭,并称:“庶子府君坟。……在前明首膺征辟……崇祯庚午(1630),告官理复久例,配享佥事府君。”(郑隆经等:《郑氏祭簿·祭期并规则》,郑家藏民国壬戌(1922)重刊本)考郑泳为明初人,柳贯曾为其作冠礼祝辞(柳贯著,柳遵杰点校:《柳贯诗文集》卷十三《郑泳加冠字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1页),而柳贯死于元至正二年(1342),郑泳之寿必不能至崇祯庚午(1630)。则郑泳原本《家仪》不可能载有庶子府君郑济之祭,乃是郑崇岳重刊《家仪》时补入。又考《家仪》补入此条时尚有“庶子府君入圣朝”之称,而《祭簿》则已改作“前明”,则该书定本时间当在明末,此后未再修订。
续表

六 礼亲 迎庙 见毛奇龄《家礼辨说》1623—1716纳吉可去,“请期”称“告期”。妇至告庙、见舅姑。三月庙见。李塨《学礼》1659—1733纳采、问名、纳吉、纳币、告期、亲迎。不用毛奇龄说,认同《家礼》。三月庙见。王心敬《四礼宁俭编》1656—1738问名、请期、纳币、亲迎。略同吕祖谦《家范》。“导女而入,先诣祖祠。”王复礼《家礼辨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具备。亲迎至女家、女家告庙、醮女、婿奠雁拜妇之父母、返家、婿妇谒家庙、同牢合卺、飨送者、明日夙兴妇见舅姑、醴妇、妇见尊长、妇馈舅姑、舅姑飨妇、三月庙见、婿见。三月庙见。“《家礼》改三月为三日,且不明言庙见之故,致习俗货货,遂以庙见为祀祖,大非。”《茗州吴氏家典》康熙五十二年(1713)具备。“以问名附纳采,而纳吉、纳币、请期,合为一事,亲迎各为一节。”略同《家礼》,补婿见妇之父母之庙见。略同《家礼》。张汝诚《家礼会通》雍正十二年(1734)问名、定盟、纳采、纳币、请期、亲迎。亲迎之日仪节同《家礼》,后异:三日早起庙见、见舅姑及诸亲、宴妇礼、妇请姑酢、旋车礼。三日庙见。曹庭栋《昏礼通考》乾隆十九年(1754)具备。以纳吉为定。认同《家礼》。认同《家礼》。《重修邱公家礼仪节》乾隆三十五年(1770)具备。略同《家礼仪节》,在卷首补入《六礼名义》申说其义。妇至前仪节略同,妇至之后仪式次序为:庙见、合卺、妇见舅姑、舅姑礼之、见尊长、同房、礼宾、明日婿见妇之父母、庙见、见尊长诸亲。“按《大明会典》天子纳后、亲王纳妃俱先谒庙,然后行合卺礼,而士庶人之礼独无之。愚意先拜祠堂为是。”武先慎《家礼集议》乾隆五十八年(1793)纳采、纳币、亲迎。“凭媒妁之言问所自出,两姓许可,送年齿生辰,然后纳聘,此问名并入纳采义也。卜吉定期,预告女家,旋以币帛品物致送,此纳吉、请期并入纳币义也。”驳毛奇龄,认可《家礼》,而在亲迎次日见舅姑、庙见,三日婿见妇之父母。 “遵《家礼》之义,参以宋说,合之邓论,应于妇至之明日见舅姑,尊长之在坐者亦见之,然后舅姑以妇见于祠堂。”林伯桐《品官家仪考》《士人家仪考》《人家冠昏丧祭考》道光二十四年(1844)纳采、纳币、请期、亲迎。《品官》:“纳采……乡俗谓之定礼。”《人家》:“纳采……乡俗谓之通庚。”有《妇至当先谒祖而后合卺考》《妇至三日可庙见考》。同《家礼》。
续表

六 礼亲 迎庙 见顾广誉《四礼榷疑》道光二十九年(1849)驳毛奇龄,从《家礼》。驳毛奇龄,从《家礼》。梁杰《家礼全集》光绪二十一年(1895)纳采、问名、纳币、请期、亲迎。“纳采内就以问名,纳币内就以请期。”沈某《家礼酌通》光绪十四年(1888)纳采、纳币、亲迎。同《家礼》。同《家礼》。
三、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
余英时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曾提出“内在理路”(innerlogic)的方法:“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38)余英时 :《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换言之,思想史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不但要探讨同一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争论及解决情况,还要关注后人在解决既有问题过程中引发的新问题。虽然“内在理路”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却对当前的家礼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当前对于明清家礼历史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种试图建立家礼与朱子学、阳明学、考据学等学术形态之间的关系,探讨新学术思想的出现对于家礼的影响,姑可称作“学术思想影响论”。持这种思路的学者认为,明清家礼的变迁受学术范式转变的影响,在阳明学兴起后有趋于简约的倾向,而在清代则演变为礼学考证。但是,家礼从俗从简是早在宋代便已出现的现象,并非阳明学者的专利;考礼是程朱便已开创的传统,亦非清儒所能自矜。从著作特点看,陆王一派学者不乏烦琐之作(如《陆氏家制》《南赣乡约》),程朱一派不无简约之风(如《家礼》删“六礼”为“三礼”);考据学者不无专断之辞(如毛奇龄《昏礼辨正》),义理学者不废考据之功(如丘濬《家礼仪节》)。对此,该假说都不能提供合乎逻辑的解释,从而难以为明清家礼的历史变迁提供有效说明。
另一种试图建立家礼与国家权力、社会之间的联系,探讨礼作为一种媒介沟通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作用,权可称作“外在影响假说”。这种观点认为家礼的变迁主要是国家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状况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外缘论自然无可厚非,却只是“对塔说相轮”,一旦深入到礼文变动及相关论争,便会显得缺乏解释力。例如,《大明会典》《大清通礼》中明确规定庶人婚礼三日庙见,为何不少明清家礼不顾国家礼典的明文规定,主张将庙见前置于新妇入门时?由上文可知,这是《家礼》仪文的固有缺陷导致的,明清家礼的异动并非对于政治权力、官方学术的简单否定与抵制,只不过是在努力解决这些难题而已。
笔者认为,家礼学在明清之嬗变的确存在某种内在逻辑。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承认朱熹《家礼》是一部“早年未定之本”,有许多见解未及订正、不够成熟。有趣的是,正是因为《家礼》的不完美,才引发后人在其身殁后产生补完《家礼》的巨大热情。这种研究热情从朱熹弟子黄榦、陈淳、杨复等人开启,经由元代朱子学者的地方化实践,在明代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学问。当《性理大全》中刻入《家礼》,《家礼》俨然与《近思录》等朱子学著作并列成为学者必读之书,在明代士人间广泛传播、讨论。这一过程与官方强力推行《家礼》实践的过程相协调,共同促成了家礼学的形成。到明代中期,《家礼》是庶民家中必备之书,是学者居家所行之礼,是士子考学必究之典,是官员当政化俗之具,俨然成为朱熹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同时,《家礼》在学术研究与礼仪实践中开始遭遇难题,并引发学者士大夫的反思。这些反思导致大量家礼新作的出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从《家礼·昏礼》的相关情况看,明清家礼学者对《家礼》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南宋到明代中前期,以杨复《家礼附录》、丘濬《家礼仪节》为代表,特点是在《家礼》基础上的补充古礼仪文,使之成为具备古义、详于施行的完本家礼。第二阶段是明代中晚期,以吕坤《四礼疑》、冯善《家礼集说》、宋纁《四礼初稿》等为代表,特点是质疑《家礼》礼文中自相矛盾、不合情理的内容,考证古礼、参酌己意做出修改。第三阶段从明末到清代,以毛奇龄《家礼辨说》、王复礼《家礼辨定》、曹庭栋《昏礼通考》等为代表,特点是质疑对《家礼》所以立制的理论、经典依据,揭示《家礼》对于古礼的误读与曲解,试图制定合乎古礼、安于人情、比于时俗的礼文。在这个不算短的时段内,学者对于《家礼》的认识从模糊走向清晰、由盲目转为自觉。当然,在清朝中期所有可能的问题穷尽后,家礼学也随之沉寂下来,道光之后的家礼著作已难觅及具备开创意义的思想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