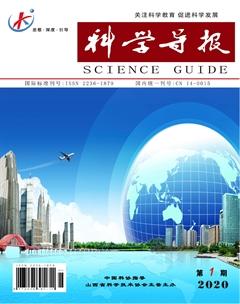云南少数民族风俗
窦泽杰
(一)摩梭走婚习俗的概况
我国的摩梭人作为一种民族下的独立人种而存在,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称纳日人,在我国其主要分布于四川与云南两省交界的泸沽湖地区。云南的摩梭人属主要居住于云南北部,属于纳西族,走婚习俗是摩梭人特有的一种事实婚姻状态。
纳西族摩梭人的婚姻形式比较复杂,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正常的婚姻关系,二是“阿肖同居”,三是“阿肖婚”。最为典型的是“阿肖婚”。这里所说的“阿肖婚”意思是“共宿的朋友”的意思。当地的摩梭人把这个形式称之为“走婚”,摩梭人一般在十九周岁以后,就会开始进行“走婚”,等到女方有了孩子后,便可以正式走婚了。传统的走婚表现在摩梭男子主动抢女方身上的一件东西,若摩梭女子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这便是流露出相爱之情,这就能说明彼此已经接受对方成为自己的“阿夏”。随后,摩梭族的男子便开始走访女子,在走访女子时必须带上先前找好的媒人或带上关系较亲密的朋友到女方家中。女方家中会提前备好酒菜,盛情款待男方。同时女方家长会通知其本村的亲族,表示自己的女儿已经有了“阿夏”。到入睡时,由女方母亲或姊妹将男子送到女子的花房。同时,摩梭男子在头三次走访女子时都要回避女子的舅舅、兄弟等。总而言之,这种民族婚姻可以总结为男不娶、女不嫁,男女双方不进行家庭的实质性组合,而是摩梭男子到女子家中居住,天亮后又回到自己家中,所生的子女由女方抚养,双方除这种关系外并没有经济上的联系,也不要承担义务,完全是一种“母系婚姻”。但这种走婚习俗并不是随意性的,男女双方从走婚开始就有着对应的义务,走婚的同时是绝对不允许走婚男女与多人同时保持走婚,一旦违反这一原则,便会受到民族内部的谴责。
摩梭人的这种走婚习俗,其最初的目的无非在于保证摩梭人的繁衍生息、理清两性伦理。同时,摩梭人通过这种习俗达到了理顺家庭私有财产关系和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目的。在这种民族状况下的走婚习俗中,作为女方的家族功能凸显出来。走婚的男子建立婚姻关系后,可以对其子女不承担任何的责任,他们的子女生活完全依托于女方的家庭。女方家庭承担了家庭中的子女抚养的全部责任。
(二)走婚习俗的法律冲突问题
依照纳西族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双方不存在形式上的婚姻,走婚制中婚姻和财产继承的内容几乎不涉及国家的婚姻法和继承法的实质内容,它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来约束摩梭人的相关行为,这套内容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没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在婚姻方面体现了极大的自由,财产方面也毫无争议的指出了属母系家庭所有。一般而言,其由女方家庭单独承担子女抚养义务,与男方并无抚养上的争议,同样,在女方家庭内成长的子女对男方(父亲)也无相应的赡养义务。同时子女对男方的财产也无相应的继承权。
这样的民族习俗很显然与会让我们联系到民法、婚姻法和继承法等一些具体的法律规定,很显然,走婚的习俗与实体法的规定是相冲突的,如在司法实务中法官遇见诸如此类的问题,则很难以实体法规定判断其事实,更难以作出判决,这就需要法官重视民族习俗这一非正式法源。
(三)走婚习俗的司法适用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纳西族的走婚习俗是在国家法之外维持的,其“走婚式”的婚姻关系也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管制的。因而可以将其归于民族习惯法范畴之内,然而我们所说的民族习惯法,其又不属于国家制定法,并不能作为法官司法审判的依据。从外国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的民族习惯法也都是通过法官自由裁量,由个案审判法官根据相关民族习惯法与现行法是否冲突进行判断。可以说该种实现途徑就是通过法官来适用法律的一种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现行法律存在漏洞或不足时,让民族习惯法基于其原生性和传统性等特征自然的作为司法审判的评价规范。但是,从基本分类而言,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确是直接对立的,国家法属于正式法源,可直接由法官将其作为司法审判的评价规范,而民族习惯法是非正式法源,只能借助于法官在诉讼中享有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适用,将其间接的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概括来说,民族习惯法并不是国家制定的成文实体法,其进入司法审判必然要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
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属于民族习惯的一种,但这种习俗却与婚姻家庭继承法等实体法规定相左,在此情况之下,法官完全可以依据其掌握的法理进行基本判断和事件调查,通过调查可以看出走婚习俗由来已久,且已经成为该地区普遍遵循的一种行为习惯。其能传承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属于少数民族无害的习俗,我国宪法规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因而法官可以据此进行说理,将该非正式法源引入裁判之中,使判决结果实现一种区域内的公正。当然法官也可通过报请程序,将此类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确认抑或是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立法权单独进行实体性立法的方式解决,但这些程序仅限于事后,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仍有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