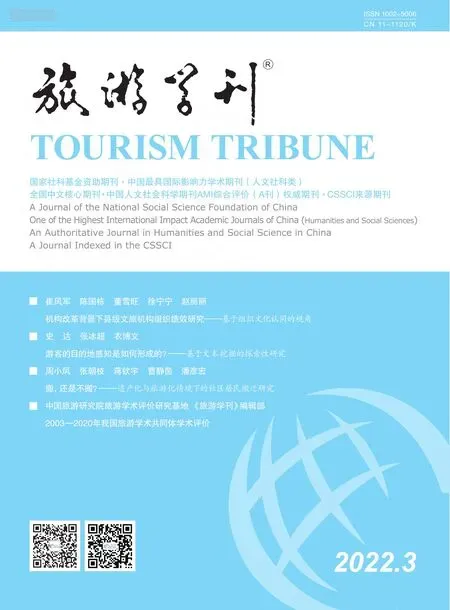旅游制度环境与国内旅游消费:制度嵌入性视角
刘亦雪 姚延波
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s, TSA)将旅游业界定为一系列为旅游者提供或多或少依赖旅游业的商品和服务,旅游业的规模由消费者(旅游者)的消费所决定(Frechtling, 1999, 2010; Smeral,2006)。旅游者可以自主决定其出游行为和消费行为,同时也要受到嵌入其中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制度嵌入性”是指消费者选择行为的制度约束(Nee和Ingram,1998;王宁,2008)。以国内旅游消费为例,意指旅游消费行为嵌入我国的旅游制度中。王宁将“制度嵌入性”视作消费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纲领,有效解释了“消费自主性”忽略的“消费脆弱性”话题。嵌入的旅游制度环境形塑了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旅游制度环境也为国内旅游消费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一、旅游消费助推旅游业发展和消费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的国内旅游市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09年至今国内游客人次增长速度均达10%以上,说明旅游已成为人民生活的常态和刚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反映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并提出发展壮大旅游产业以推动消费的稳定增长。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中可以看到国家关于消费意识形态的转变,从“生活水平话语”到“扩大消费话语”,国家赋予居民消费欲望以合法化并给予符号刺激(王宁, 2012)。消费也被喻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马车”,国内消费则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从国家宏观政策来看,发展旅游产业和加强旅游领域制度建设助推了国内旅游消费;从“消费自主性”来看,旅游消费因消费欲的符号刺激而迅速增长;从“消费嵌入性”来看,旅游者的消費行为同时也要受到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旅游消费促进了我国国内消费的增长和旅游业发展。何为旅游消费?世界旅游组织(WTO)将旅游消费界定为“由旅游者使用或为他们而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从旅游全过程来看,旅游者旅游活动前通过行程预订和支付进行消费,旅游活动中对食、住、行、游、购、娱等相关旅游产品和服务进行消费,旅游消费使旅游业对经济增长发挥强大的拉动作用,其经济乘数效应远高于其他行业。国内旅游消费也成为我国旅游消费的主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旅游总花费达5.13万亿元,旅游总收入5.97万亿元,国内旅游总花费占旅游总收入的86%,国内旅游消费成为推动消费的增长点。
二、制度嵌入性视角下的国内旅游消费
国家的“扩大消费话语”、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者的消费话语建构共同形成了消费欲的“符号刺激”,促进了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在国内旅游消费蓬勃发展过程中,也隐藏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旅游虚假广告、欺客宰客、强迫消费、非法“一日游”等市场顽疾,这均属旅游消费的脆弱性。旅游消费脆弱性是指旅游者因旅游消费风险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国内旅游消费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费脆弱性,由制度环境所造成(王宁, 2013)。正如王宁(2012)指出的“中国许多游客的体验:出游是为了开心,但常常免不了不开心。”由于旅游者出游前无法预见可能的消费风险,旅游被看作是一种高风险购买行为(Gitelson和Crompton,1983;Sirakaya和Woodside,2005),所以需要完善制度环境以降低消费风险。以“制度嵌入性”视角来看,旅游者的国内旅游消费行为亦受到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规范和约束;同时,国家监管部门、旅游经营者、旅游者等旅游消费相关主体也在推动着制度环境的优化调整。其中,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对制度环境的形成发挥着主导作用,典型如中共中央于2019年10月31日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共同架构了我国的旅游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础规则,是其他制度安排的基础(卢现祥, 2003)。Schultz(1968)将制度定义为一整套规则,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Binswanger和Ruttan,1979)。制度又由正式制度(政策、法律等)、非正式制度(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和实施机制构成(North,1990)。旅游制度在于减少旅游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旅游交易费用和消费的脆弱性以促进旅游消费。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要求旅游业完善旅游制度环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旅游需要。另外,消费升级驱动下,旅游者更注重目的地制度环境和优质的旅游体验,特别是替代性较强的目的地选择,典型如雪乡负面事件后,游客选择去其他省份或国家的冰雪旅游地。从消费实践来看,旅游者不仅关注旅行消费符号及其意义,更关注消费客体、物质性和具身体验(王宁, 2018)。自媒体时代,旅游者可将旅游消费的全过程和旅游体验的全细节分享于网络之中,这促使旅游者和经营者双边的单次旅游交易转化成多边的交易关系,进而影响未来的旅游消费选择。
三、完善旅游制度环境,促进国内旅游消费
良好的旅游制度环境可降低旅游消费风险,减少旅游消费的脆弱性。同时,制度环境也促成了目的地的市场环境,具体表现在旅游交易是否有序、消费过程是否规范、旅游产品价格和质量是否明确等方面,出于安全性和风险可控性的考虑,旅游者更倾向于选择消费体验可预期的目的地。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保护旅游者和营造良好旅游制度环境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为旅游消费提供制度保障(Grant,1996;March,2008;Zhang等,2009)。旅游者的体验性消费需求要求目的地通过制度供给进一步规范其市场环境,那么,如何优化我国的旅游制度环境以促进国内旅游消费?笔者认为可以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三方面加以考量。
(一)完善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方面,我国出台了《旅游法》《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旅行社服务通则》等旅游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体系等来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完善旅游制度环境。未来仍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旅游相关法律法规,关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马波, 2018)。典型如《旅游法》约束作用并没有有效发挥,部分条款仍需明晰,“比如‘不合理低价,按照《旅游法》第35条,有3個条件同时存在才能处罚,第一是低价,价格由物价部门来认可,而物价往往有最高限价,很少限低,不合理低价难界定;第二个是强迫消费,他们会说没有强迫只是建议,你要有强迫或诱导消费的证据;第三个‘获取回扣等不正当收益取证更难,他们可能在私下达成一定的奖励或返点,监管取证难”(文化和旅游部监管司访谈)。制度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如欧洲委员会于1992年颁布《欧共体包价旅游条例》,规定了包价旅游和相关旅游服务的市场运作规则;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欧盟对其进行了多次修订,并于2015年11月25日发布了最新修订的《欧盟包价旅游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旅游者和经营者的交易规则和包价旅游服务操作。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做法为我国旅游制度环境的完善提供了借鉴,未来需完善我国的正式制度,以合理明晰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为国内旅游消费保驾护航。
(二)培育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观、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与正式制度交互作用和促进。比如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游客之间在关系构建方面,是不是具有契约精神,是否依规履行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有些旅游企业仍存在短视思维,缺乏契约精神,消费者法律意识较淡薄,遇到事情不太愿意通过法律解决。深层剖析国内旅游消费中呈现出的低价游问题,一方面,旅游进入大众化时代,市场本身有低价游的需求,如笔者访谈的一位旅行社经理所述,“我做了十几年的旅行社,自己的亲戚旅游也会咨询我,我一看他报团的价格说你不能去啊,这个价格自费可能比较多,他们说我知道啊,旅游结束后也觉得挺好,都不通过我这边出团,觉得这边定价高”;另一方面,旅游企业采取低价模式去经营,把这种产品推销给游客,形成了利益输送的产业链。治理必须把利益的根源打掉,同时要培育非正式制度约束,以宣传和披露引导消费者的理性消费,以声誉机制和信用体系引导旅游企业规范经营,让非正式制度成为正式制度的细化和补充。
(三)健全制度实施机制
旅游制度的有效性除了需要完善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外,更需要健全的制度实施机制。没有配套的实施机制,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便形同虚设。典型如《旅游法》的实施机制不健全致使其并没有有效发挥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再比如出现旅游投诉,监管部门能否依法快速处理旅游者的有效投诉,旅游中频繁爆发的负面事件部分源于旅游投诉反馈渠道的不完善、旅游反馈处理机制和制度实施机制的不健全。国家作为制度实施机制的主体,一方面,要细化制度配套的实施细则,另一方面,要依法依规执行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
(第一作者系该院博士研究生、讲师,第二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9-12-25)
[责任编辑: 吴巧红;责任校对: 宋志伟]
1 王宁. 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产业转型升级[J].社会学研究,2014(4):24-48.
2 张朝枝. 文化与旅游何以融合: 基于身份认同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12): 162-166.
3 吴少峰,戴光全.迷笛音乐节中循环新部落的联结与交往特质[J].旅游学刊, 2019, 34(6): 7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