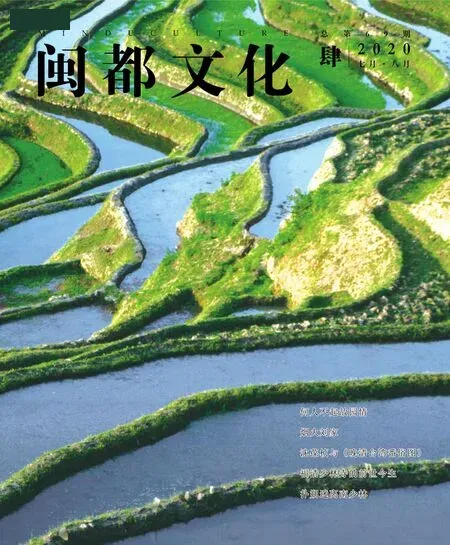清晨的闽江
鹿 野
清晨的闽江,其实已经不是闽江的清晨,它的清晨开始得比我们都要早,比整个城市都要早。
第一只飞过闽江的白鹭知道,当晨跑的年轻人、跳舞的大妈以及忙碌的上班族所组成的车流在江滨大道上奏响一曲交响乐的时候,闽江已经醒来多时了。
江中捕鱼的小船也知道。因为它已经沿着闽江的潮水,来回梭巡一圈,归了航。
妇人侧蹲在船舱内,用旧毛巾使劲地擦洗小船。一遍一遍,用力地擦。那些砖红色的木板被她擦洗得干净光滑,像新漆过的一样。接着,她开始清洗渔具、雨靴、雨衣。就着舷外的江水提起来,搡下去,提起来,搡下去,雨衣上的泥垢就被江水带走了。
并排停在旁边的几条船只,船身糊满了泥浆。油漆被浸蚀久了,已经剥落,木板表层都是裂缝。看来被主人放逐在这里,多日不用了。
清洗完渔具,妇人开始整理吃过早餐的碗盘。那一定是凌晨从家中带着的早餐,来不及坐在桌边慢慢吃;潮涨是不等人的。他们用两个绿色的搪瓷盆子装了,带到船上吃。就着来回移动的晨雾,一边吃一边挑一点喂给船头张望的白鹭。
男人把网一节一节地卷起来,捆扎好,一边查看着有无破损。他拉动船头的浮板,把自己渡上岸来。一只白色的油漆桶晃来荡去,里面装着今天一早的收获,几条黑鲫鱼,几条黄甲,还有几只并不肥大的江蟹,但因为是江中野生的,总能吸引一些厌弃人工养殖,对于自然生长有谜一般信念的老买主。
其实闽江边的渔民多数已经不能指望靠打鱼维持生计了。早在2000年初,政府就鼓励渔民上岸,有的安排到厂矿,有的给予失业补助。对岸就是这个城市最为繁华的商业区,CBD;超大体量的建筑群一到夜晚就会亮起炫目的灯光,那是最新科技操作下的灯光秀。这岸是他们的家。原先的窝棚早已拆除,他们都搬进了政府修建的安置房。这些闽江边的原住民,凭着对一条江的守候,已经拥有了令许多外地人羡慕的家底。随着近年来闽江沿岸楼盘的大涨,他们也早已不用为生计发愁。许多人因为拆迁都坐拥好几套房产,价值几百上千万。他们的子女也告别了古老的生存方式,上大学、考公务员,或者到企业工作。
但打了一辈子鱼的渔民还是舍不得水中的生活。摇摇晃晃的船上的舒坦,大概是走在平整宽阔的陆地上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江上的自由开阔大概也是拥挤的城市所不能给予的。
作为旁观者,我每天清晨途经闽江。每天清晨看着这对夫妇清点渔获,如同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但我始终不曾和他们有过一句交谈,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我在他们漠然的眼光中,继续我的散步,或者小跑。
沿着闽江跑。经过一座桥,两座桥,三座桥。
夏日初启,蓝花楹开放,闽江沿岸种了一溜的蓝花楹,在青绿色的浓荫中一树蓝紫色的花瓣高扬。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颜色的树呢?蓝色的花树。花瓣无声地掉落到地板上,一整片蓝色……有跑步的男士也忍不住停下来掏出手机对着拍,感叹着说好美啊。见我在看他,有点不好意思又腼腆地笑一下走了。
爱美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再跑远一点,跑到花海,跑到鼓山大桥下。各种时节各种花。成片成片的紫色的马鞭草,黄色的硫花菊。不是羞答答地开,是轰轰烈烈地开,排山倒海一般地开,是像海一样翻滚着浪花而来。
闽江水如同一条加粗的波浪线,把这个城市最美的诗句划了出来,那么醒目、耀眼。
于是你总盯着江水看,看久了,你会以为它在倒流。这令人恍惚的怀疑的时刻,你如同看到你自己。
泅水的人从下游逆流而上,双臂轮番挖向水下,像在拥抱什么,又像在打捞什么。身后波浪千重万重地跟随着,阳光一打,好像披了一件浩荡的金色披风,又像一个人牵引着千军万马。
雨季的闽江,江水浑黄、污杂。一些上游的残枝、水草顺着浑黄的江水漂下来。水直接淹到步道了。整个雨季,都是昏暗的。天空,闽江,全是浑浊的。即使这样,也有人下去游泳。多半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似乎一点不惧怕江水汹涌。他们从小在江边长大,入闽江,跟我们街道上行走一般自在。于是我们只能站在岸上,看他们戴着泳帽的圆乎乎的头像个皮球浮在汹涌的江面上,一点一点漂远。
落潮时的闽江干枯贫瘠,白鹭像捡拾残渣的流浪者聚集在干枯的河床上互相追逐,发出沙哑的叫声。那些停泊在江边的无主的船只像被遗弃多时。你以为它就会这么病下去了,丑下去了。不,它没有,自然界用一种无声的强大的力量修复它,水涨起来,一切又丰盈、光亮,不留痕迹。
人生不也是这样吗?一切都会随时间流逝。伤病和痛苦、贫穷和孤独,必然也包括美好的、令人留恋的情感。我们从未停止修复自己,完善自己。像一棵树、一朵花、一颗茶籽,会被闽江带到最适合的地方,然后,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