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心理咨询师的510通电话
林秋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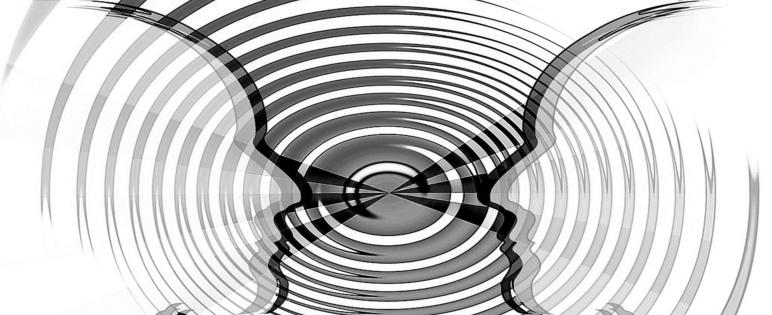
北大精神卫生研究所曾在2004年做过一项调查,发现SARS痊愈出院的病人3个月内抑郁状态和焦虑状态的检出率分别是16.4%和10.1%。严重传染性疾病与一系列精神疾病存在联系,根据国内外的研究,重大灾难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到20%,常见的症状包括:创伤后应激反应、抑郁反应、焦虑反应、躯体化反应等。
和SARS相似,新型冠状肺炎同样具有事发突然、传染性强、缺乏特效治疗药物等特点。强迫性的隔离、封闭的生存环境、高度刺激的信息更新给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损伤,它可能侵入的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病患及其家属,以及健康的普通人。
疫情发生后,各个省市陆续设立了心理援助热线。武汉宣布封城当天,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肖劲松教授找到心理咨询师杜洺君,第一时间开设了湖北心理热线。她成了湖北心协热線首批心理咨询师之一。
杜洺君从事心理培训多年,在2013年取得心理咨询师证,2014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开始用心理学来辅助自己的治疗和康复。在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她积累了大量肿瘤心理危机干预、医护人员心理健康辅导的案例和经验。
从1月23日至2月5日,湖北心理热线的团队接到了510通求助电话,累计提供心理危机干预1000次以上。其中95%是非医护人员发来的求助。有人每隔半小时就测量一次体温,有人因为“疑冠”将自己封闭在房间里……新冠带来的伤害,不仅在生理层面上发生作用,同时也在心上埋下了一颗雷。
疫情发生后,杜洺君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身体时常陷入深度疲惫的状态,但她始终用温柔、平缓的语气回答问题。她听到过不同的哭声和苦难,有时候也会跟着电话那头的人同频流泪,慢慢安抚对方,轻轻揉开他们心上的褶皱。
2月7日接受采访的最后,她哽咽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少了,我真的希望能够通过我一个小小的声音,去召唤所有人做些改变,更加去珍惜那一点点健康、一点点自由。”
以下是杜洺君的讲述。
1
李文亮医生去世了,这个事情是一个点,通过这个点可以看到我们整体的痛。
从疫情开始到2月5日,我们的热线一共接到了510通电话。
医护人员的电话打进来,最常表现的状态就是对于疫情的倦怠和无力,还有对于他们自身所处状况的焦虑和恐惧。
我接过一个呼吸科医生的电话,打来电话那天她已经连续上了9个小时的班,每天都在高强度工作,晚上得吃安定片才能睡着。
她每天要面对很多发热病人,有的病人,她需要将耳朵贴近他们的嘴边,飞沫很难防范。护目镜雾气很重,没办法写病历,只好摘掉。这些工作中的细节都让她非常焦虑。
医生们可能出现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现在都只能做预期的评估,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做的预警。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对接到武汉市各大医院的护理部。比较大的医院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心理热线,他们有内部的心理支持体系,我们遇到的一线医护人员的情况,目前大部分是相对稳定的。
实际上,我们接待的医护人员比例不到5%,他们根本没时间打电话。相比其他人群,他们的心理状态会比较滞后一些,可能到疫情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有精力去顾自己的心理状态。
那个时候介入其实也不会迟。所有的个体都会有底线和管理的(方式),都有心理上自我修复的机制,不一定都要借助外界的力量,自己就可以完成。
我认为大部分的医护人员会安然度过这个疫情,这个只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件事情。一些医护人员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们害怕,甚至受不了,但是这些话是瞬间的语言,所有人都会有的。它是一个表达,不代表他们的态度。他们哭完了,倾诉完了以后,第二天又很有毅力地上班了,我们不能根据他当下的情况断章取义地判断他整体的状态。
这是作为一个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我们不能轻视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要总刻意地找他们崩溃的瞬间,其实这些瞬间是很少的。更多时候,他们会要求自己如常地、比以往更坚强地去做他们的工作,我们应该给他们敬意。
2
最开始,求助的人90%是女性。女性沟通的能力强一些,也比男性更善于求助。男性可能更会隐藏自己,尤其不善于表达自己脆弱的部分。现在这个数据在变化,男性慢慢地多了起来,接近7比3的比例,关注的点也越来越趋同,都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并没有明显的分界。
有个年轻人,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给他在线做了一级干预之后,他的状态稳定了下来,已经能够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了。我们继续联动,把这个消息发到媒体和社区。社区向我们做了确认,得知这个情况属实,马上安排了人和车,把这个轻度感染的病人安排到了医院的床位。
除了医生、患者,感染者的家属也是这场疫情中的易感人群。他们是一直陪伴着患者的,因为这场疫情去世的人的家属,他们会比较严重一些。
一天早晨,一个女士打电话来,说她父母都病重,在两家不同的医院住,她要每天两头跑,给爸爸买好早饭,还要跑去另一家医院陪妈妈。她很害怕哪一次回来,爸爸就不在了。她是独生女,现在也请不到护工,压力和恐慌让她在电话里嚎啕大哭。我让她先吃点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她平静下来后,我把她转给了另一个咨询师,进行三级的持续跟踪。
我们有时候会和电话那头的咨询者一起流泪,那是一种同情和同理,是咨询师对他的一种感知。在这个状态下,咨询师是跟他同频的。心理咨询师有双重身份,我流的是他的眼泪。
我们一级干预有20多个心理咨询师,二级干预有202个人。我们要求做一级接听的咨询老师,咨询时长要有200个小时以上,年龄在40岁左右,要有丰富的经验。咨询师们是轮值的制度,目前还没到忙不过来的程度。人手是足够的,甚至是不饱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找到我们。
接到的电话,武汉和湖北省其他县市的占2/3,还有1/3来自全国其他省市。最北的有黑龙江,最南的有海南岛,我们都接到过电话。打完了以后,他们会说,抱歉,我们占用了你们湖北的资源,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支持。这让人很感动。
3
目前形势下,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趋向是“疑冠”(怀疑自己得了新冠)的人变多了。有的人怀疑自己生病了,会把自己隔离起来。当他处在单独的一个空间里面,孤单、恐惧和焦虑会达到高峰。这一类人打电话进来,我是非常感动的,这是基于爱和责任做出的选择,宁愿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也不愿意去影响到家人。
还有一个关于爱和责任的故事。我们接待过的最小的咨询者才12岁。电话刚接起来的时候,就听到旁边一个斥责声。他妈妈在旁边说,叫你不要打,你非要打。小孩子冲他妈妈喊,妈妈,我是帮你打的。妈妈没有吭声。他转过来对我说,我妈妈太焦虑了。我说,你需要我们给你什么支持?他想了想跟我讲,给我派个专家吧。
这个孩子就是想帮妈妈。他后来开了免提,全家人围在一起聊天,情绪得到了缓解。他妈妈的情况比较严重,也是比较常见的焦虑,我们都会存在。这时候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多做一些其他事情,对疫情的时间长度做好心理预期。有的人会不断地强迫性地刷新闻,可以把它理解为自己的责任感和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但不要因为刷新闻而影响自身的情绪,要控制那个度。
现在来求助的年龄层是中间高两头尖,30岁到50岁的人群占2/3。中间年龄层的求助者要承担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他们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个时候收支平衡被打破,肯定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现在的需求已经到了最底层,生命本身的压力才是第一位的,人们都已经被这场疫情推回到了最原始的点。
中年人通常会表达他们的责任和疫情的矛盾,他们其实隐隐地知道自己的付出,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哭,他们觉得自己在家人面前不可以表露真实的恐惧和内在。很多人熬到最后一刻才打电话过来,我们的老师告诉他,其实你可以哭的。这个时候,他才会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
我们会有聆听和回应,等他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再给他专业的支持,对当前的情况做一些分析,最后给予鼓励和肯定,强调他的责任感。这份信念的鼓舞,会支持他更久一点。这是整个工作的一个过程。聆听、回应、澄清,是我们干预的前三个步骤,在这之后还有评估和判断。澄清指的是澄清他们出现的情况是情绪状态还是生理状态。人在情绪激动状态中的讲述基本上没有什么顺序和逻辑,我们要为他解释出现的原因。
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每天反复量很多次体温,每半小时量一次,都在36、37度左右。我问他,你看你多次测量的体温,目前都控制在37度以下,对吗?这些是正常的。听到这些确认,他才会回过神来。
大家普遍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关于睡眠的改善。首先要确认,睡不着是心理还是生理的原因,是自身疾病还是疫情的原因,再对应地给予支持。
几天前,我们接到了一个老人的电话,他说总是睡不着。咨询师在线教他做了一个渐进式肌肉放松,第二天他又打了热线来说,你昨天给我讲了(肌肉放松)所以我睡得特别好,你再给我讲一讲,让我可以再睡着。
最近几天,健康的求助者少了一些。本身就有精神类疾病,比如患有抑郁和焦虑症的人,他们开始頻繁地求助了。有些患者以前吃过药好了,可是身体会记得这些感受和创伤,当与疫情相关的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基础疾病会被重新牵连出来,被激活。他们也成为了易感人群,应该得到关注。
到目前为止,我们平台还没有接到过自杀这样的高危案子,但是我们接到过别的平台的求助。
朋友圈里有人给我转来一个女孩的留言,说她焦虑到有自杀的想法。我们致电过去,女孩说,还好,没事了。当时她可能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很快挂断了这个电话。那种自杀的极端情绪是一时起来的。她接到电话之后,为什么说够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状态得到了陌生人的关注,她得到了这份关心就满足了。心理援助的一句话,也许是十分钟,但可能会改变一个人和一家人的命运。还会有一些热线覆盖不到的人群,这需要媒体和政府扩大宣传和援助的力度,让有心理需求的人及时地得到支持。但不要太依赖于心理援助,其他一些渠道也是可以去做到这些的。回家的路有千万条。
在心理援助这方面,一定要实事求是,切莫夸大了这个热线的作用。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伴说,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能做一点点的事情。跟我们能做的事情比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做什么,要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了这一点,那就不会感觉到无力。
4
6号晚上得知了李文亮医生的情况,我们编发了一个图文,关键词是活下来,因为对感染的人群来讲,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奢求了。
跟以往的危机干预相比,这次疫情发生得很急,所有事情发展的速度都太快了。同时它的范围很广,波及的社会性效应更深。
援助的困难其实不在心理工作者身上。如果说针对疫情本身的预警来得及时,事件本身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支持和发展变化的话,大部分人都能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情,不用心理工作者做太多的事情,需要援助的人群会缩到很小。
一些高危案例,比如对医生、武汉人产生怨恨,不仅仅是心理上出现的问题。这个事情的前端不是心理,而是事情本身,还是要回到最前端的事件。对于个体来讲,冲突、绝望和矛盾,从以前的远端到了他的眼前,平衡被打破了。
我们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解决这种怨恨,很难。能做的事情只是安抚、理解、同情。心理援助只能起到安抚的作用,稳定个体阶段性的心理变化,但是效果不会持续很久,我们无法预知平衡哪一次再次被打破。
这种个体不能耐受的痛苦,不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生命的启发,或者说是由心理的咨访关系推动他放下。这需要更大的力量,这背后藏着更宏大的社会问题。
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最终的走向都是:接受。
所有人都必须慢慢接受这件事情的发生,都去面对它给每一个个体、每个家庭乃至社会带来的影响。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他在这个瞬间理解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健康、什么是亲情。去寻找这个事件对他们每一个人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所在。我们都会痛,但面对这么多生命的痛,我们能做出一点什么来改善。
(第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在超市做采购。去超市之前,我和我妹妹一起给父母送了一些东西。我们把东西放在门口,他们拿进去,我们就下楼了,没有聊太多。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看到身边所有人的状态,我心中突然觉得很悲凉。那一刻,我站在那里流泪。
我看到他们捂得很严实,全副武装,在做各种各样能想得到的防护。比如把鞋套套在鞋子上,有的人穿上吃火锅的一次性围裙。所有去超市采购生活物资的人,都在拿自己拿得动的东西,往家里搬。年轻人也好,中老年人也好,都这样。因为不能开车,完全凭人力在路上拼命地搬运。
当时我觉得好心酸,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所有的生活都改变了。小区的大门被铁丝网封锁起来了,只留一个门供进出,量体温,做登记。你甚至很感恩小区旁边的卖菜的小店能开,但你买东西还是要靠呼喊,你要冲他喊你要什么菜,他再递过来给你。变化太大了。街上每个人看到对面有人来就绕开走了,不想和对方走在同一片空气当中。会心痛,心会很疼。我同时也很清楚,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在付出一个代价。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体现了一种群体性的失望。调和群体的情绪状态,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要有一个声音出来,恢复平衡,对他予以公正和公平的对待。
我希望6号这天能作为起点,能够有一个相对公平公允的声音来面对生命,来面對所有处在疫情中的民众。那么也许从这一天开始,我们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会往好的方向走,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拐点。
今天(2月7日)我跟所有伙伴说,我们不接受采访,要静默一天。为现实中这么多条生命的逝去,李医生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哽咽)
【来源】《人物》。
【阅读导引】一般而言,疫情本身因快速、波及传染、严重,对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下,除了带来躯体疾病外,一般人还可能会出现应激反应,如内心恐慌、焦虑、恐惧等。虽有人可通过自我调节等快速缓解;但若周围紧急事件持续发生,就可能使人产生心理危机,进一步形成心理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疫情期间,各地开展的心理援助是非常重要且有效的。特殊时期,隔着屏幕、电话,通过文字和语音来倾听、共情的心理援助,虽有一定的效果,但心理创伤是需要随时间、环境等慢慢恢复的,因此长期的关注也应当引起普遍重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负性情绪,有效调适心理健康水平呢?1.了解认识疫情性质和流行情况。2.接纳恐惧、焦虑等应激情绪。3.进行自我暗示、树立坚定信念。4.多交流、获得心理支持。5.建立积极的应对方式。6.寻求专业的心理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