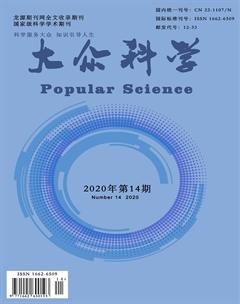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影响因素探析
郑洁颖 何婉庄 黎淑芹
摘 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方面改革的热点问题,是土地资源配置优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经济转型,意义十分深远。文章主要通过介绍佛山市南海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基本情况,然后根据南海建设用地入市的基本情况分析其入市的影响因素,并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的优化机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或意见。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影响因素;优化机制
一、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乡二者发展较好的同时,城乡差距却逐渐拉大。此外,土地市场的不断发育,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和农村用地的相关制度愈加完善,使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的必要性大大加强,以减少因城镇化与建设用地间的矛盾、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农村居民收入利益分配不当、农村产业及经济发展缓慢等带来的问题。为顺应时代发展给土地带来的改革潮流,国家制定并不断改善土地制度并得到发展,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也使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范入市一步步得到实现。在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印发关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试点工作的意见,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出 33 个县市区进行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其中包括广东南海、广西北流等。广东南海作为广东唯一一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试点,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本文将从广东南海的整体概况,从政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推导和制约因素,深入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影响因素,并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相关建议。
二、南海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基本情况
(一)南海区概况
佛山南海区位于广东省的中部,属于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南接佛山顺德区,环抱佛山禅城区,毗连广州市,靠近香港、澳门、深圳等地区,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土地价值较高。全区总面积为1073.8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91万[10]。南海区共有 2031 个经济社,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约 30 万亩,占全区建设用地总面积 38%。2019年,南海区GPA达3176.62亿元[11],连续6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排行榜第二名[12],综合实力较强。
(二)南海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发展过程
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载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南海区作为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腹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流转入市工作起步也比较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南海进行改革,逐步以经济社制代替生产队制;在90年代的“大抢建”后,南海的产业出现“量大、分散、低效”的情况,严重阻碍了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建设[1]。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求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2014年,南海区政府出台了《佛山市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施办法》,该办法的出台使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取得了较大的突破。2015年初,佛山南海区被授权为全国33个探索试点之一。
在一系列的背景下,南海区抓住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探索。
在被确定为试点地区后,南海区政府积极探索,先后出台了《入市管理试行办法》、《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与税费征收使用管理试行办法》,逐步构建起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体系。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政府结合先前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经验,学习其他试点地区的先进办法,从入市监管、抵押融资管理、产权登记管理、租赁住房管理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为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南海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现状
(1)南海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面积考察。
据网络数据调查和实地勘测,笔者对南海的用地面积进行摸查,结果显示: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面积约达304平方公里,其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面积约达171平方公里,约占集体建设用地总面积的56.25%[2]。
(2)南海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成果。
近几年,南海区抓住试点契机,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行了探索,并逐步构建起一套“1+N”的入市试点政策体系,全方位落实指导试点工作。
2016年初,南海首宗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政策执行的地块交易成交入市,标志着南海的改革试点工作进入了实操阶段。据统计,2016年12月止,南海区共完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42宗,面积约1670亩,总成交金额约36亿元。2017年8月止,共完成集体建设用地入市71宗,面积约2162亩,总成交金额超过58亿。2018年8月止,共完成集体建设用地入市88宗,面积约2471.7亩,总成交金额达70亿[13],交易的项目数量和成交金额位居33个试点地区的前列。由此可见,在试点政策体系的支持下,南海区集体性建设用地入市在穩步进行,项目数量不断攀升,所覆盖的集体土地面积也在逐渐扩大。
从实地访问调查结果可知,南海区的村民们纷纷享受到试点改革带来的红利,股份分红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极大的改善了生活质量。以大沥镇星港城项目为例,该地块所属经济社成员每年的集体土地股份分红已经超过40000元。
(3)南海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乱象。
早在2014年,南海区政府印发的相关文件中就规定:“通过流转方式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不得用于建设住宅或类似住宅的居住用房,也不得将地上已有的其他用途用房改为居住用房”。但随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入市改革逐步深化,许多开发项目却违反规定,出现“违规商改住”的乱市现象,即一些原本为商业服务性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项目,在竣工验收后,违规改建了公寓销售,扰乱了市场秩序,造成了大量不知情业主们的损失。出现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作为市场主体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因为开发商会根据市场需求而选择违规商改住,这是市场主体逐利行为,但是入市项目数量巨大,政府监管仍存在难处[14]。笔者认为,该现象反应出南海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存在着监管的漏洞,若不加强监管,就会有更多无辜的业主为这种乱象买单,造成更大的损失与更多企业以此失信。
三、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南海区的调查,本文主要将影响入市的因素分为诱导因素和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其中诱导因素的影响主要分析经济发展以及所处区位等的因素影响,而约束因素影响主要分析法律定位模糊、产权主体不明晰以及入市收益分配存在分歧的影响。
(一)诱导因素的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的持续发展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开始向经济水平高、基础设施配套较为完善的城镇或城市地区聚集。人口的聚集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必然会带来劳动力成本降低,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并推动服务业的发展,[3]不断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加对土地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在《人民日报》公布的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中,佛山市南海区再次强势上榜2019全国综合实力百強区,并连续第六年蝉联全国第二名。南海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使这里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与市场发育基础,吸引了众多投资、创业者,用地需求大大增加,而集体建设用地的灵活利用方式与相对较低出让或租赁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用地者的前期成本,使其更乐于选择使用集体建设用地。[4]
2、区位因素
首先,佛山市南海区位于广东省中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其东部地区与广州市中心城区相连,地理位置优越,而这优越的区位使其易于接受广州市的辐射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基础好,集体土地流转的数量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更为明显。[5]为了增强区域竞争力,2009年3月19日,广州市和佛山市签署了《广州市佛山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并颁布具体政策措施。而且南海区位于广佛交界地带,是广佛同城化的核心区域,在同城化的背景下可以创造更多优良的经济发展机遇,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源,促进该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不断推动南海的经济快速发展,增加对土地市场的需求,促进土地的交易。
其次,由于南海区临近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受到城市的辐射作用较强,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交通运输十分便利,因此其建设用地需求量大。
(二)约束因素的分析
1、法律定位上的模糊
2019年 8 月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新法”)颁布,在涉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制度中,删除了原法第43条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的规定。虽然新法从法律层面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消除了法律障碍,结束了多年来集体建设用地不能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的二元体制,但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在现行法律上依然定性模糊。《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客体是国有土地;新法的第六十三条与第六十六条都提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但这并不能代表可以将《物权法》中有关“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涵义应用于新法中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即使在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文件中,多处可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用语,但至今也没有现行法对其进行法律定性。
包志会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的现实障碍”的分析中[6]提到入市主体呈现多样化的原因在于农民集体在现行法律上定性模糊,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也没有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律定位模糊,一方面不能有效地优化配置农地资源,阻碍入市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例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发生争议时,法院在判决中不管是引用《物权法》中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还是引用新法中有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行的立法不仅没有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也没有设计出较为明朗的法律规则。[6]因此这也导致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进程十分缓慢,不能达到明显的效果,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力度还需加大。
2、产权主体不明晰
根据我国目前《土地管理法》的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据此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而“集体”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社会团体,而这种社会团体由于不健全的产权制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主体,加上权利的被限制,会导致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因其主权不明而具有较小的流动性。[3]
同时,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具体指出“集体”所指谁,在 《宪法》和 《土地管理法》 法律层面和各试点地区的入市实践中都不够明晰,甚至有些地区存在直接混淆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情况。因此产权主体不明晰会严重影响入市交易,农民的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3、收益分配存在分歧
自2015年南海被确定为33个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后,试点工作的开展给南海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尤其是伴随着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而带来的大额土地增值收益,使得南海农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快速的提高。而农村集体(经济社)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者,所以收益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的顺利开展。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收益分配,实质上就是对其增值收益[15]的利益分配。然而,通过调查可见,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实操过程中,由于涉及的利益分配主体较多,各方对于收益分配主体问题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社)和政府之间的收益分配矛盾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社)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者,毋庸置疑要享有收益分配的权利。而作为政府主体,正如刘燕铟在“政府—农民集体—土地使用者”的博弈分析[7]中提到地方政府在土地入市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保证政府在市场中能发挥好管理者职能的均衡状态,使得政府在管理工作中所耗费的成本得到经济补偿,所以政府参与到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的收益分配,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博弈分析中也提到,若政府参与收益分配的比例不合理,就会导致农民集体获得的收益过少,从而容易出现土地隐形交易行为的发生,扰乱试点改革的秩序。
综上,在土地收益分配的主体问题上,社会上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意见,如何在保证村民及村民集体的利益受到保障的同时处理好政府财政问题,制定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依旧是试点工作需要努力改进的方向。
四、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解决对策
(一)加强入市制度在法律上的建设
面对相关法律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不完善、不合理之处,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该加快完善入市制度的进度。国土资源部公开向公众收集《土地管理法》修改意见,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修改为“国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等方式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并签订书面合同”,这也成功创立了属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物权权能,强化了农民对于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权属。然而农村集体组织依旧没有完全具备独立法人的资格,因此集体组织尚未享有的经营权利应该要有详细的法规制定。[8]
同时,法规制度中的农民土地范围应该进一步明确。农村闲置宅基地、废弃地等整理节余出来的建设用地是否符合规划前提,在入市经营性建设用地范围之内,并无政策或法律界定相关概念。[9]因此,要使得入市过程中入市土地范围的明确,解决因土地范围带来的农村征地的冲突,相关概念一定要足够精确,才会使后续建设用地的开发、农民收益分配的合理带来契机,减少纷争。
(二)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产权制度
《土地管理法》中提及到的所有权人为“农民集体”,关于此概念,国家应该更明确地表述出“集体”一词的详细意义,落实到每一个集体组织的每一类人身上,确保每个人的自身利益都受到制度保障,避免引发所有者、使用者、政府多方共同矛盾。所有权主体和使用权主体要分清,才能使双方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减少纷争。南海政府也需给予相关的补助和支持,使所有权主体和使用权主体两者合作,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此外,应在试点地区首先实行一系列的推广措施及管理條例,让农民在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更加了解流程和相关法律,更加清楚地知道产权主体是何者,为农民能得到合适的、公平的收益打好基础,使得入市整个进程更加顺畅。
(三)健全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
收益分配制度的是否合理,决定农民收益是否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农村经济是否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因害怕收益分配有分歧而不敢进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乡村有不少,因此做好分配工作是重点,其核心在处理好国家财政、县乡镇府、农民集体组织成员、农民个人的收益分配比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根据参与利益分配者可将其划分为内部分配和外部分配。[3]
内部分配主要指农民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其主要包括土地所有者、土地使用者,重点是处理好双方的收益分配比例,农民集体组织成员制度的完善也必不可少,这也是分配依据之一。
外部分配主要指国家财政、县乡政府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县乡政府在入市过程中的参与,包括部门介入走访、多方面交谈、基础设施建设等,所以政府也是参与利益分配者之一。国家财政方面,可分配一部分收益,通过税收体制来体现,保证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体现了公平性和均衡性。
五、结语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我国在土地制度建设升级过程中的一大举措,它打破了我国原有的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制度。其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持,同时又是缓解城镇压力,使得城镇发展走向新形式的新起点。尽管在发展中有出现过一些约束问题,如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主体不明确、收益分配有分歧等,但是这会随着我国不断创新改革而逐渐得到解决,最终会提高我国农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陈海素.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困境——以广东省南海区为例[J].广东土地科学,2017,16(02):9-11.
[2]李松杰.以重点示范项目带动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以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为视角[J].广东经济,2017(05):20-23.
[3]刘冬凤.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湖州为例[D].浙江:财经大学.
[4]叶红玲.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新模式——广东南海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观察[J].中国土地,2018(07):4-9.
[5]李春江,贾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研究——以佛山市南海区为例[J].乡村科技,2019(24):41-43.
[6]包志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现实障碍和破解路径[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19(09):78+69.
[7]刘燕铟. 南海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收益分配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5.
[8]陈旻贤.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困境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11):49
[9]李清华.我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问题研究[J].科技博览,2018,13:197
[10]数据来源:http://www.nanhai.gov.cn 南海区人民政府官网
[11]数据来源:http://www.foshan.gov.cn/gzjg/stjj 佛山统计局官网
[12]数据来源:http://www.csmcity.com 中国中小城市网
[13]数据参考来源:搜狐新闻
[14]规范监管下暗生“灰色地带”佛山南海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溯源,来源:中国经营报
[15]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是指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产生的入市总收入扣除原先土地的取得成本和土地开发成本后的净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