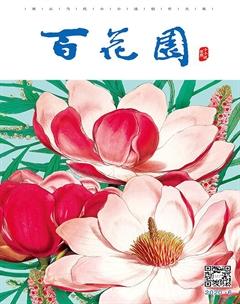是谁杀了伯仁
郑俊甫
人这辈子真是邪性,怕什么来什么。那天,一位好友喝醉了酒,附在我耳边悄声说:“你兄王敦,脑后生着反骨。”我心一颤,手中的杯子差点儿落地。好友擅长卜卦,大小事经了他的嘴,无不应验。
我一直想找王敦聊聊。这个堂兄啊,一刻也不让老王家省心,整天磨刀霍霍,忙着操演他的军马。我修了一封家书,言辞恳切,希望他能收敛收敛,尤其是在皇帝面前。信还没有送到,王敦就闹腾起来,以“清君侧”的名义,浩浩荡荡,兵临江东。
在京的王氏几百号人,一时间惶惶不可终日。大家无头苍蝇似的,满城乱飞,最后都飞进了我的府门。没办法,谁让王敦是我堂兄呢!还是撒尿和泥一起玩大的。大家都想听听我的意见,是卷起细软溜之大吉,还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当然都不能。皇帝于我有恩,于我们王氏有恩,出了这档子祸及九族的事情,我心有愧呀!于是,我带着一众族人,齐齐跪到宫门外,负荆请罪。
辰時,日上三竿。宫门外来来往往的人,见了我们,掩面而逃,好像我们身上带着瘟疫。以前这帮人不是这样,以前他们为了迈进我的府门,无不使尽钻营之能事。
此一时彼一时,我老老实实地垂着脑袋,等着皇帝心生怜意,能够给我一个表明心迹的机会,却始终等不到。皇帝像是忘了,宫门外还跪着乌泱泱一群人,个个如同油煎。
午时,身边“噔噔噔”有了杂乱的脚步声。斜睨一眼,是伯仁!我的好友周伯仁!我的心中顿然照进阳光。
我与伯仁自幼相识,情同手足。这么说吧,但凡我有一口肉吃,绝不会让他喝汤。当然,作为大晋的才子,官居尚书仆射,伯仁也不需要我的眷顾。
如果说,我对伯仁有什么看法,就是他太孤傲了。一次,与伯仁闲谈,我拍着他的肚子,戏谑道:“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的都是些什么?”伯仁一笑,轻飘飘地答道:“里面空空洞洞,不过像你这样的人,足可容纳数百个。”又一次,皇帝大宴群臣,酒酣歌热,兴之所至,皇帝说:“今日名臣共聚一堂,纵使尧舜之时也不过如此吧?”伯仁站起来反驳:“如今的世道怎么能跟尧舜盛世相比呢?”皇帝大怒,下诏将伯仁下狱。数日后,皇帝愤怒平息,才将他放出。大家前去探望,为他压惊,伯仁却轻描淡写地说:“就知道我死不了,没犯死罪嘛。”
你瞧瞧,这像什么话嘛!但是不管怎样,这么多年的情谊还是在的。况且,当年伯仁赴任荆州刺史,遇到了流寇,幸得王敦出手相救,才幸免于难。说起来,王氏于他,也算有再造之恩。如今,王家落到这步田地,他动动嘴皮,为我们求几句情,不为过吧?
我唤了一声伯仁。伯仁扭头扫了我一眼,视若无物,置若罔闻。我以为他没听见,提高嗓音又唤了一声:“伯仁,我王家几百口的性命就都靠你啦!”伯仁这次头都没回,昂首进了宫。
这家伙,为了避嫌,六亲不认。我心中愤然。
大概申时,不,也许已经是酉时。我揩汗的时候,斜日的余晖已经隐入宫墙。伯仁终于出来了,歪歪扭扭,五迷三道。这个酒鬼,平时贪贪杯也就罢了,这个时候,我一家老小命悬一线,他还有心思饮酒!我心里虽恨,身子依然匍匐向前,扯住了他的衣袖,像是扯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我得知道,皇帝到底打算怎样处置王家。
伯仁冲我翻了翻白眼,居然对身边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杀了王敦那帮浑蛋,好挣个天大的功名!”然后扬长而去。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
事情的发展像是一场戏。数日后,王敦大败朝廷大军,占领建康。入京后,王敦置瑟瑟发抖的皇帝于不顾,却开始笼络人才,意图重整朝纲。他跑过来问我:“伯仁声望极高,应当位列三司吧?”
我看了王敦一眼,即便他是一个胜利者,我依然觉得他是一员叛将,是王氏宗祠的一块污点。但现在说的是伯仁,伯仁呀,我的脑子里满是他走过我身边时目中无人的样子。我选择了沉默。
王敦不甘心,追着问道:“就算不入三司,也得做个仆射吧?”
我依然沉默。
王敦的眼里露出了凶光:“如果不能用,就只能杀了他。”
我装作没听见,抬头看天。仿佛天上写着伯仁的宿命。
伯仁最终被捕,押至城南门外处死。据说,临刑前,伯仁面色不变,举止自若。伯仁死后,家被查抄,作为大晋高官,家里仅有五瓮酒、数石米、几篓旧絮,而已。
我说过,事情的发展像是一场戏。我和王氏一族,因为在王敦之乱中坚定立场,维护帝室,不但断绝了这位堂兄的勃勃野心,还激起了民众的高昂斗志。王敦之乱很快平息,我又回到了熟悉的位置。我开始着手整理宫中奏折,厚厚的一摞里,意外地发现了伯仁的奏章。竟然是历数我的功绩和耿耿忠心,言辞恳切,殷勤备至。落款的时间,正是我跪在宫门外的那天深夜。我这才醒悟,在宫里和皇帝喝得醉醺醺的伯仁,醒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皇帝上表,替我这个所谓的好友鸣冤叫屈。
那天,我回到家,闭门谢客。我把几个儿子唤到跟前,一字一句地忏悔:“吾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呀!”
语罢,顿足捶胸,大放悲声。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