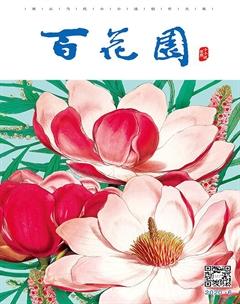阿 九
高亦佳

长生第一次见到阿九,是在一个刚下过雪的冬日清晨。当时阿九大约是十六岁吧。那天她来给长生的奶奶送花布,穿了一件大红的比肩褂和一条绣了花的黑裤子,裤脚绲着雪白的绒边,看上去暖和得很。他似乎还记得阿九梳了两条麻花辫子,发尾用红色的线绳绑了蝴蝶结。
阿九进屋之后便热络地和奶奶聊天,而长生则被奶奶打发去给他哥哥送一碗蒸鸡蛋。聊着聊着,奶奶就问阿九:“阿九啊,你妈妈给你说下人家了吗?”
阿九一惊,哈欠也被惊了回去,但因为瞌睡而蓄的眼泪却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愣了一下,回答道:“没有……哎呀,奶奶,您再说这个我可恼了。好好儿地送两块布来,怎么说起这个来了!”
奶奶笑而不语地点了点头,半晌后,又问:“你看你长生哥怎么样?”
阿九瞪了眼睛:“奶奶!你还说这个!”
奶奶憋不住笑了,道:“好好好,我们不说这个了。去吧,去吧,找你长生哥去,让他带你好好转一转。”
阿九红着脸应下,下了炕推门出去找长生了。
后来事实证明,长生实在是个禁不起漂亮姑娘诱惑的人。
当他们二人走在覆满白雪的红里坡上时,从没来过这儿的阿九远远瞥见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洞口。阿九顿时对那个洞口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伫立在雪地之上望着那個洞口。
突然,她从绲了白色绒边的袖子里伸出手来,轻轻地拉了拉长生的衣角,说道:“长生哥,那洞里是什么啊?咱们能去看看吗?”
岭北冬天冷,在山里躲着避寒冬眠的野兽也多。长生是这一带长大的人,在这崇山峻岭里活了十几年,他是知道这一点的。看着阿九恳求的眼神,他说:“好吧,就在洞口看看,咱们不进去,万一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睡着……”
阿九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
走在皑皑白雪中,他们二人仿佛偌大白色画布上两个缓缓移动的墨点,一滴是沉稳不语的墨黑,另一滴是燃烧着的朱砂。
那洞口离得有些远,一路上长生紧张得喉咙发紧,手心出汗。他从没和哪个姑娘有过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近到甚至能看清她额角的碎发、她胸襟上的绣花针脚还有红头绳的纹路。走到洞口时,长生往前迈了一步,却没料到雪是蓬松的。他一脚下去就踩进了坑里重心不稳,摇摇晃晃地摔倒了。阿九想去扶他,却也栽进了雪地里。
长生爬起来伸手去够阿九,紧促的呼吸之间流露出无限的焦急:“阿九……阿九,你还好吗?”
阿九慢吞吞地爬起来,蹒跚着向他走去:“没事儿,长生哥,我没摔着。你别动,我扶你起来。”
待到走在阳光下,长生才发现阿九走路一拐一拐的,应该是刚才那一摔崴到了脚。
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阿九回身看他,歪着头问:“怎么了,长生哥?怎么不走了?”
长生抓住她的左臂,说道:“崴脚了吧,我背你走吧。咱们先回家去。”
阿九犹豫了片刻,本想挣扎着走回去,但想到路程实在有些远,也就不再拒绝。
那天晚上,长生又背着阿九把她送回家。在夜路寂静到他以为她已经趴在他背上睡着了的时候,阿九突然贴着长生的脖颈问了一句:
“长生哥,你知道今天奶奶问了我什么吗?”
“嗯……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她问我有没有许下人家,我说没有。她就又问我觉得长生哥你怎么样。”阿九顿了一下,叹了口气继续说,“我嫌臊,没和她说。”
“啊,这样啊……”长生脚步没停,却有点儿失望。他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接下去,也不知道是不是该岔开话题说说别的。他听不出来阿九到底是不是中意他,也不知道阿九是怎么看他的。
胡思乱想间,长生已经快要走到阿九的村口了。
长生觉得,自己要是再不鼓起勇气问问她,就没机会了。于是他长吸了一口气,问道:“阿九,你到底觉得我怎么样呢?”
他忐忑着,心里飞速地盘算着各种可能性。他想了很多很多,甚至有些害臊地想着要是上她家提亲去该说些什么。
可身后却是一片寂静,只有颈边传来阵阵温热的呼吸。这呼吸声平稳得过分,听上去阿九应该是睡着了。
长生抬眼看了看黑魆魆的夜空,星星令人眼花缭乱地铺了满天。
他继续往前走,心想,幸好只有星星听到了。阿九要是听见了,多难为情啊!我很中意她,可她呢,看起来不像中意我的样子。
“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了。”长生顾自嘀咕了一句,加快了脚步。
把阿九送到家之后,阿九的母亲要留长生睡一晚,长生跺了跺脚,笑着摆摆手说:“不麻烦啦!”
阿九母亲也没再留,给他拿了两个烙饼,就目送他出了村口。
长生出村口之前,向阿九母亲挥了挥手,喊道:“姨,以后多让阿九来玩儿。”
那个裹着灰色布袄的村妇应了一声,就进了屋。
长生看着阿九家里那抹昏黄熄灭之后,转身回家。
回家的路上,长生两手揣进兜里,百无聊赖地踢着雪,他心说:“这么好的姑娘……阿九呀阿九,偏偏你是这么好的姑娘。”
他继续走着,似乎听到身后有人叫他名字。他回头望,却只有一片苍茫茫的天与地。
低了头去看,地上,长生的影子被拉得老长老长。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