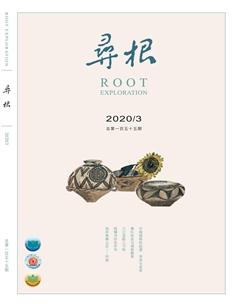闲雅识得十色笺
陈益
笺,最初是指写有注文的狭长竹片,系在原书简册上,仅用为标识。后来,慢慢演变为用于书写的小幅精美纸张,早在六朝时就通行了。唐代元和年间,寓居成都浣花溪的女诗人薛涛,精心创制出一种形制独特的笺纸,她在与诗人元稹以此题写诗酬,显得分外浪漫,被称为薛涛笺。“浣花笺纸桃花色”“红笺纸上撒花琼”等诗句,正是对它的形象描绘。
其实,蜀地的笺纸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色。此外,还有松花、流沙、彩霞、金粉等别色。《益部谈资》载:“薛涛井,旧名玉女津,在锦江南岸。水极清澈,石栏周环,久属蜀藩,为制笺处。有堂室数楹,令卒守之。每年定期命匠制紙用以为入京表疏,市无贸者。”《元费著纸谱》云:“今天下皆以木肤为纸,而蜀中乃尽用蔡伦法,有玉版、有贡余、有经屑、有表光等纸。玉版、贡余杂以旧布破履乱麻为之,唯经屑表光非乱麻不用。于是造纸者庙以祀蔡伦矣。”不难想见,十色笺纸的制作,在蜀地工艺十分讲究。后来还吸收了来自苏州的制笺艺术,称作“假苏版”。有所不同的是苏州笺纸多布纹,而“假苏版”多螺纹,纸骨柔薄。如果加厚,就能胜过苏纸。
到了明清时期,笺纸在江南一带被文人推崇。不仅有素笺,更流行印有人物、花鸟、山水图案的画笺。随着版画和木刻水印技艺的发展,笺纸被提升成一种艺术品,是属于文人的雅玩。天启年间刊行的《萝轩变古笺谱》和崇祯年间刊行的《十竹斋笺谱》,就是画笺的代表之作。
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不仅喜欢使用笺纸,还兴致勃勃地研究、传播创制方法。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屠隆在《考盘余事》卷二中,详尽地写下了“造葵笺法”“染宋笺色法”“造金银印花笺法”等章节。他说:“槐花半升,炒煎赤,冷水三碗煎汁。用银母粉一两、矾五钱,研细,先入盆内。将黄汁煎起,用绢滤过,方入盆中,搅匀拖纸,以淡为佳。文房用笺,外此敷色,皆不足备。”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创制出松花笺来。
颇有些市场经济意识的李渔,亲自设计创制了很多种笺纸,包括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笺纸上,专门刻印“笠翁新制”字样。不仅如此,他还标明每束笺纸的价格,四处销售。他说,自己之所以卖力地推销,是为了“售之坊间,得钱付梓人,仍剞劂之用。是此后生生不已”。与此同时,他公开宣布,不许他人翻梓。以今天的目光看,李渔将笺纸作为艺术品,也作为商品,不只十分注重流通,也很有版权意识。在这一点上,他站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清末文学家、经学家俞樾喜欢自制信笺,曾经制作曲园、右台仙馆、俞楼、五禽等多种笺纸为自己所用。自制信笺上,往往会有朱绘人物,人物或为坐姿,或为揖拜。并镌印“曲园”“曲园拜上”“如面后”等文字,充满文人雅趣。他的笺纸不但款式多,而且制作精致。最有名的“春在堂五禽笺”,笺纸上用红色篆字书写禽鸟名称并题字,五禽包括鹊、凤、燕、雁和鹤。写上“鹊”字的,上面题有“喜鹊随函到丝萝,故作鹊笺”;写上“燕”字的,则题有“紫燕西来,欲寄书,故作燕笺”,独具一格。
俞樾曾在扇面上题诗:“别馆山中草未滋,寓楼仍榜蒋公祠。何来福寿残砖字,得自宾朋雅集时。叠韵仍教依石鼓,制笺不必界乌丝。如今摹入齐纨扇,好与蒲葵一例持。”他设计笺纸和书写信札时的闲情雅致,悄然体现了出来。
古稀之年时,俞樾曾为自己设计、制作了二十种颇具个性特色的“墨戏”笺纸,为亲朋好友所称道。例如“一团和气”,取篆书形,“和气”二字围成圆形,标题为“一团和气”。图式说明为:“篆书‘和气二字,规而圆之,是谓‘一团和气。”“曲园长寿”,取草书式,“曲园”二字变体,肖人之形;“长寿”联书,末笔拉长,斜穿过“园”字拉下,取竹枝形,寓“携杖老人”之意。“曲园写竹”,篆草杂糅,如画竹石。左下方粗笔连写“曲园”二字,形似园中之石;右下为“写”字,“竹”字似两杆竹枝斜贯而上,字体呈竹石之貌,说明文字为“写此制笺,以报平安”。“曲园对月”,形肖老人依栏对月。“蓄道德能文章”,篆行草杂糅,犹如魁星像。“万卷书”,则仿佛架上积轴。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无纸化写作。懂得十色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结识的一位青年收藏家,近年来以一己之力,收集了一千多通名人信札,几乎都是书写在明清和民国时期的笺纸上。信札的上款人、下款人,既有学者、教授、作家、演员,也有党政官员、企业家、军人。每件信札不仅是文史研究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资料,也是探索笺纸艺术流变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