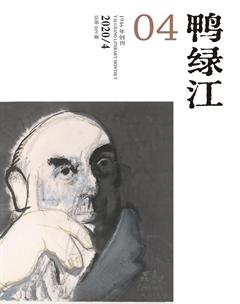他者镜鉴中的人情回响(评论)
1950年,朝鲜半岛硝烟弥漫,美国的介入更是让这场战争威胁到了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统一。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友邻情谊,同年7月,“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这一场高亢激越、充满着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战争至今仍是中朝两国深厚友谊的见证。
而在文学领域,作家们以敏锐的政治嗅觉与深彻的生活感悟迅速对这场战争进行了“与时偕行”的速写。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强影响力的报刊,比如《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都集中刊发了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在1950年至1953年间,东北本土期刊《东北文艺》(《鸭绿江》杂志前身)也发表了诸多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这其中包括韶华的《中国的客人》(1951年5月第三卷第四期)、柯欣的《列车在行进中》(1951年6月第三卷第五期)、鲁苓的《深厚的友谊》(1951年7月第三卷第六期)、殿宸书的《他们为了祖国》(1952年2月第五卷第一期)、李班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952年5月第五卷第四期)、韶华的《堵击》(1952年7月号30期)、胡捷的《光荣的任务》(1952年10号第33期)、韶华的《再见》(1953年1月号第36期)等等。这些“朝鲜叙事”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股“创作潮流”,以“十七年”文学的第一杆接力棒的姿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文学标本。
本期“新经典”栏目重新刊发蔡天心的《江边上》。这篇小说完成于1950年11月,这几乎与中国解放军出征朝鲜的日期同步。虽然在写作主体的亲身经历上有别于巴金、魏巍、路翎等亲赴朝鲜战地的写作者,但蔡天心以一种先验的自觉意识,在抗美援朝伊始便写下了这篇展示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因對美日敌军共同的仇恨而生发出“惺惺惜惺惺”之情的短篇小说。
50年代的“朝鲜叙事”中,大多数文学作品以抗美援朝战役为真实背景,以战地、战时、战事为写作素材,旨在突出中国志愿军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与中朝两国在战争中所建立起的亲密友谊,以此来鼓舞人心,宣扬爱国主义精神。因为受到战时文学所承载的现实功用束缚,“朝鲜叙事”在战争话语的体系中逐渐形成了相对比较固定的写作范式。在《江边上》中,作家脱离了现实的抗美援朝背景,将小说中的时空挪移到1932年,形塑了拯救“我”于危难之际的朝鲜父女的二人形象,在表现朝鲜人民的真诚与淳朴以外,从侧面揭示了侵略战争的残酷与抗战人民的坚强不屈,并借由朝鲜(人)的异国形象来映射本国(人)的人情真朴与不屈不挠的坚韧品格。
小说中,“我”率先出场于一个阴暗秋日的傍晚时分。依据故事的时间发展线索,小说可被分割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始于朝鲜姑娘凤子到学校找到“我”,向“我”说明来意:“我爸爸让我来给你送个信……今个下晚,日本人到学校来抓你,你得赶早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屯子,越快越好。”①而此时的“我”因作为一名革命者的天生“敏感”,对姑娘吞吞吐吐、含糊其辞的表述并不投以完全信任,直至姑娘说出“我”藏在房后大树窟窿里的五颗手榴弹的秘密,我对她产生了“一种温暖的亲切的感情”。姑娘向我提出,要带“我”去她家避一避,无处可躲的“我”便跟着姑娘走回了她的家。小说的第二部分,是“我”半信半疑地跟着姑娘从学校走到江边上的家,见到了姑娘的父亲,确认了这位及时给“我”送来情报的金大爷正是“我”认识的金仲山。“我”之前所有的疑虑随着与金大爷的对话都烟消云散了:“从他这几句简单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懂得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的态度是那样纯朴,那么沉着,对人那么亲切,说起话来那么有分寸,而讲起日本人,又那么充满仇恨。”金大爷与凤子姑娘用实际行动让“我”感到被奔涌的暖意包围着,并生发出对这两位朴素的朝鲜人民的留恋和景慕。伴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小说来到了第三部分,即高潮部分,朴永烈同志来到窝棚,向“我们”通风报信,金大爷叫凤子姑娘带我躲到柴火堆下面的地窖。当日本人搜到家中,向金大爷盘问“我”的去处时,他“一点也不怯懦”,用“理直气壮地强硬的声音”回应着日本人。即便当日本人对他高声斥责,拳打脚踢,他也是连一点哼声都没有。而地窖下的“我”无数次不落忍金大爷因“我”而受这番折磨,希望冲上去与日本人同归于尽。反倒是凤子姑娘极其冷静,父女俩与“我”在情绪上形成反差,这种反差更是加深着“我”的内疚感。当日军搜查盘问无果,走掉之后,“我”从地窖中出来,看到鼻青脸肿的金大爷,此时“我”的情感达到临近爆发的顶点。而金大爷却严肃地提出要“我”跟着朴永烈马上就离开的提议。在月色笼罩下的江舟上,小说走向了尾声部分,父女俩在江边的身影渐行渐远,而“我”内心的触动与敬意却越来越荡魂摄魄。
虚构是小说的权利。如果这只是一个在战争背景下,中国人民掩护地下革命工作者逃脱日军侦察的原景再现,或许使小说的“情理结构”过于流俗,也会使小说的阐释空间过于单一化。《江边上》的独异之处,是将小说中“我”的救命恩人设定成了朝鲜人的身份。救人者与被救者异国身份的建构将“我”与朝鲜父女之间的“人情”升华为中国与朝鲜两国之间的“国谊”,个体的命运与国族的前途、历史的中国与现时的朝鲜在同一叙事空间内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勾连。
二元对立式的人物立场,单线发展的故事情节,起承转合的完整叙事链条,这篇小说的叙事看起来几乎没有技巧,从开始“我”对凤子姑娘的将信将疑,到确认金大爷的身份,再到我对父女二人既感激又愧疚、既敬佩又不舍的情绪递进的过程,作家都是从“我”的心理活动层面来介入叙事的。学校外的院墙、天黑之后的三公里步行路程、地窖里、渔船上,四个地点成为小说中重要的叙事与抒情空间。每一个空间里的对话与“我”的心理活动,都在一步步加深“我”对父女俩的亲近与感激,尤其是当“我”与凤子姑娘一起躲在地窖中,一边听着日本人对金大爷的残害而无能为力,另一边,凤子却一直劝告、阻拦“我”,要“我”不要意气用事。父女俩与“我”无一不在经历着身心上巨大的煎熬,是父女俩出于对革命者的保护,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全“我”,使“我”在这次事件中感受到浓浓的人情与温暖的大爱。
然而,若仔细分析,所谓打动读者的“人情”其实源于中朝两国正在或者曾经身为被侵略者的“政治血缘”关系。这段攸关生死、感人至深的“人情”故事回响的背后,终究不能逃脱意识形态的捆绑效应,这段恩情还是被框定在了已经预设了的书写模式。朝鲜父女帮助“我”的根本原因是“我”是地下革命者的身份,是和他们一样的、站在日本侵略者对面的“统一战线同盟者”。小说中也数次借由金大爷之口表达出这个意思:“共产党不共产党现在都一样,共产党反对日本人,不是共产党的也要反对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都一样,反正在日本欺壓下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再例如结尾处,金大爷与“我”告别时说道:“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受日本鬼子压得活不下去,才豁出命来和他们拼!这不是我对你的恩德,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要记着我;路这么长,危险是很多的,你也许不会碰见我了,可是人民是不死的,你记住朝鲜人吧,我们朝鲜人现在和中国人一同受日本鬼子压迫,我们就共同来反对他,和他斗争,将来我们朝鲜人也要和中国人一同站起来。记住这个吧,记住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生死友谊。”由此可见,抗日语境已经成为了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重大主题,战争在作品中的呈现除了要表达它的深广性、人民与革命者的不屈,在1950年特殊的时间点上,作家也以高度的“自律性”将叙事指向了国家意志,及时主动地靠近和顺从了战时语境,以文学作品配合着现实斗争。
与此同时,这篇小说颠倒了我国与朝鲜人民的帮扶关系,与正在进行时的抗美援朝构成了一种互补式的呼应。1950年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因为中朝两国战争同盟的身份一致性,对于朝鲜人民形象的塑造其实也构成了某种镜像式的对照——作家将中国(人)“自我”的纯朴善良与刚正不阿的精神投射到朝鲜(人)的他者想象之中。正因为朝鲜父女对“我”不计生死的帮助建立在跨越国籍的基础上,才使得这份情谊更加动人。事实上,即使国籍不同,当面对着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反帝反殖的同一诉求会使“命运共同体”这一群体自觉地联盟,形成势不可挡的反抗力量,这也是作家给予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朝鲜人民以文学上的抚慰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蔡天心这一代的作家,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时代跨越,他们既是战争的见证者,又是亲历者,也是和平的创造者。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并深感和平年代来之不易,多重情感交织在一起,他们在新中国成立的战争书写中更多地融入了个体经验与价值立场。因此,1950年代的“朝鲜叙事”既有对峥嵘岁月的回顾与追思,也是作家们以无产阶级共和国主人的视角,将视线转向了正在同命相连的其他国族的罹难与抗争。这种人道主义立场的“人情”书写是人类性的写作,即面对非正义战争时,人性与人情是共通的,是没有种族、国籍与时代的隔膜的,所以救亡背景下的战争书写在1950年代已经开始出现了由鼓动、宣传转向缅怀、反思的萌芽,中国的“朝鲜叙事”也因中国与朝鲜的同仇敌忾、同气相求,在朝鲜的他者镜鉴中照见了注视者对战争、英雄、人性、生死等多个主题的复杂认知与期待。
上承解放区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秩序,下接“十七年”时期“文学一体化”的创作理路,处在历史转捩处的1950年代,其战争书写仍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纯粹的文学性之间斡旋。在1950年代中期,虽有《洼地上的“战役”》(1954年3月发表于《人民文学)等“朝鲜叙事”作品对个人的情感波澜没有弱化处理,但从其遭际的历史命运与文学批评的异声来看,“人情”的日常书写仍然被时代赋予的现实使命所局囿,甚至是压倒性地钳制,其艺术与审美价值也是在新时期之后才得以重衡。《江边上》表层意义上是在展现朝鲜人民的热心与英勇无畏,其实里层内置着主流话语权威规范化、组织化的诉求,因为小说中的朝鲜镜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话语载体,在主我与客我的转换中,它所映射的正是中国人民面对个人生死抉择、民族存亡考验时的时代精神风貌。由此,19世纪50年代的“朝鲜叙事”的这一特点也毫无疑问地纳入了“十七年”文学建立起的政治化主题的同构体系。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简介:
薛冰,辽宁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博士研究生。